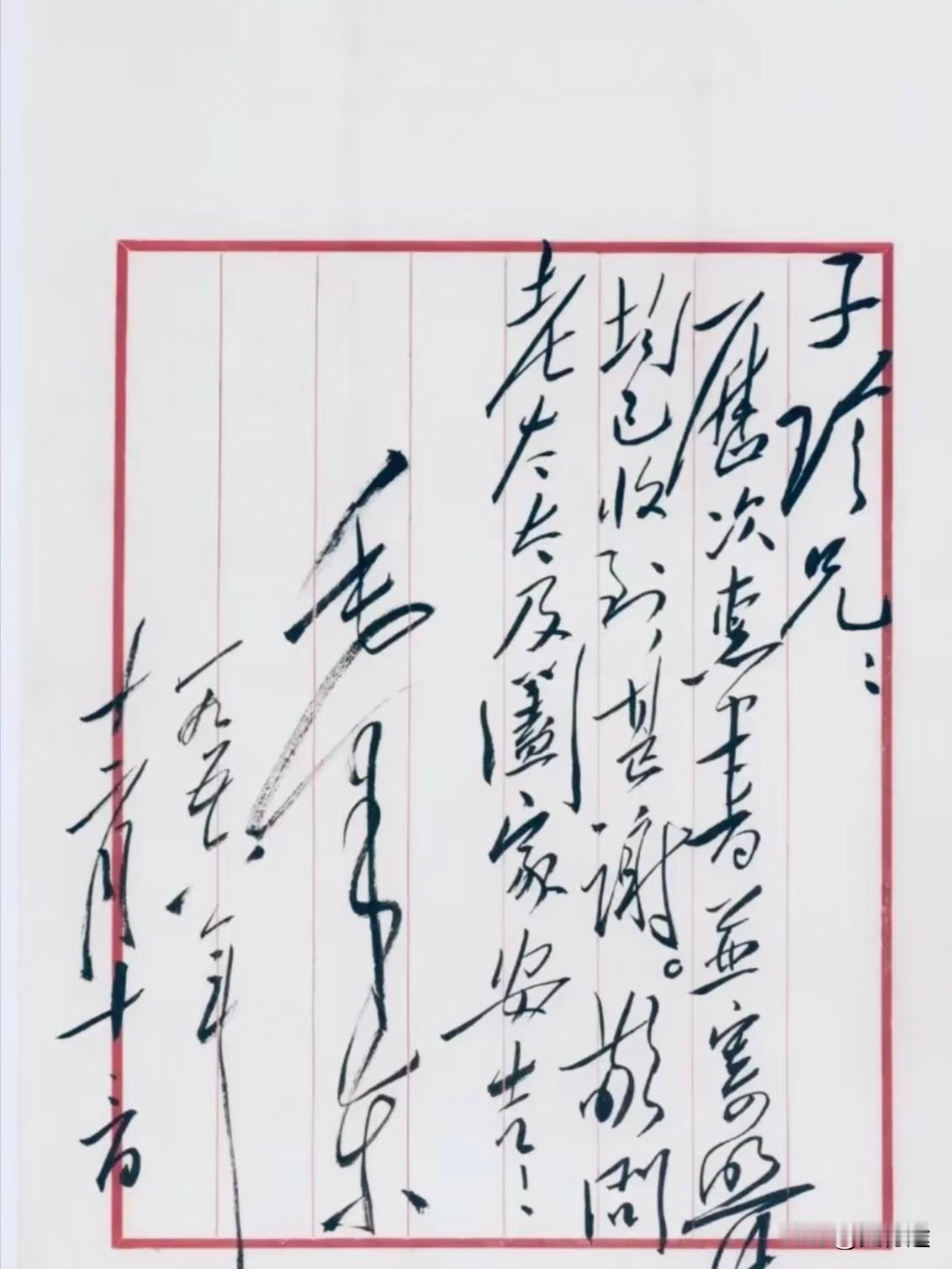毛主席写给妻子贺子珍的信! 说她命里跟信有缘,倒也不算夸张。 一九二七年,永新县天还没凉透,城里的风就先变了味。国民党右派拉着地主武装,突然对准这块地方开刀,夜里一阵乱枪,抓走了八十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牢房里塞得满满的。那会儿,贺子珍人在吉安,还是大家顺嘴叫的“桂圆”,十七岁已经是党员。消息一到,她和几个同志凑在昏黄的灯下商量,桌上摊着纸,墨迹一行一行铺开 那份“革命宣言”,就是她赶出来的。写谁被抓、谁开枪、谁在背后使坏,一条一条列得明明白白,还要派人跑省城,把这口气当面吐出来。嘴上不认输,手底下也没闲着,宁冈、安福、莲花几地的工农武装一一联络,话没说多少,意思很清楚:永新这口气不能白受。 七月二十六日,三县农民自卫军合在一起打回永新,牢门撞开,贺敏学在内的八十多人被救了出来。 街上刚透出一点喜气,江西、湖南两省六个团的敌军就压了过来。硬顶在城里,只有一个结局。 这时候,旧同学的面子成了救命的路。贺敏学和袁文才是同窗,井冈山那边的绿林好汉,本来跟“革命”这两个字还有点距离,一来二去也就坐在了一张桌边。为了把火种挪到更安全的地方,贺子珍和永新县委的同志,跟着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沿着山路往井冈山茅坪钻。 山里的风又潮又冷,人还年轻,脚却已经被磨得生疼。就是在那条路上,她成了井冈山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第一个女红军,“永新三贺”里最让人记住的那个。 再往后,秋收起义的队伍也上了山。毛泽东带着部队在这里扎下脚,枪声一阵紧一阵,火堆旁挤满了人。贺子珍混在战士里,军装穿得和别人一样,肩上的担子也不比谁轻。何长工回忆,提到她时语气里带着点佩服:“骑马打枪都熟,真带过兵,打过硬仗。” 外人爱从“夫妻”这两个字往里看花边,在山上这些人眼里,她就是战友。一块儿开会,一块儿挨饿,一块儿往前冲,毛主席对她最大的“表示”,不是甜言蜜语,是把她摆在可信任的位置上,事情推到她面前,不打折扣地让她挑。 照现在的说法,这也是一种“信”,只不过不在纸上,在安排里。 一九三五年春天,换了地方,还是那拨人。红军从贵阳往南走,干部休养连的女红军拖着一身疲惫,挪到了贵州盘县附近五里排。天色发灰,连长侯政指了指山那边,说过去歇一晚。队伍刚松下来一点,从山外传来一串飞机的轰鸣,嗡嗡地压着心口。 一架敌机压得特别低,机身几乎擦着山腰。指导员李坚真大声喊卧倒,地上的人却已经被敌机盯住。俯冲、扫射、投弹,乱作一团。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最难挪地方,有的刚抬起一头,就被爆炸声又扔回地上。 团政委钟赤兵躺在担架上,腿在遵义那边就负了伤,这会儿直挺挺动不了。他身边的警卫员已经倒在血泊里,人走了,枪还握在手里。 小沟里,有个身影原本藏得好好的。贺子珍抬头一看,心里有数:那副担架再不动,就真成靶子了。她把隐蔽当场丢开,直接从沟里窜出去。 她先是三下两下给钟赤兵重新包扎伤口,布条勒得很紧,动作干脆。接着抓起担架一头往隐蔽处拖,地面不平,担架在石头上摩擦出刺耳的响动。 刚挪出几步,敌机又俯冲下来,机枪扫了一溜火舌,炸弹从空中砸下。那一瞬间,她没时间多想,整个人扑在钟赤兵身上,用自己的背对着那片黑影。 爆炸晃得人耳朵嗡嗡响,土块、碎石、弹片一起飞过来。等烟尘稍微散一点,钟赤兵躺在担架上,已经够凶险的腿没有再添新伤,贺子珍整个人却倒在血地里不动弹,鲜血顺着头发和后背往下淌,把身下那块地弄得刺眼。 警卫员吴吉清赶到,手都在抖,把她背起又放上担架,再骑马去总卫生部硬生生把李芝医生请来。 李芝先给她打了止血针,再一点点翻找伤口。头部、上身、四肢,都被炸弹碎片“光顾”过,十七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像恶作剧一样躲在肉里面。药箱空荡荡,麻醉药根本没有,几个战士只好按住她的手脚,用夹子去夹那些比较浅的碎片。 金属和肉碰在一起,听着都疼。她额头上汗水直往下淌,眼眶湿润,到底没叫出声。深埋的弹片不敢动,只能留在那里,跟着她过余下的几十年。 昏昏沉沉几天,她总算醒了过来。睁眼第一句话不是问自己的伤,而是打听钟赤兵,人怎么样了。旁边的人告诉她没事,她那口气算是真放下来。 身体这回被彻底折腾垮了。行军路还长,她开口提出,把自己寄放在老百姓家里,不拖大家的腿。同志们死活不同意,轮班抬着她往前走。山坡陡得担架上不去,就有人蹲下来,把她背在身上,一步一步往上挪。 伤口结了痂,疼劲还在,她咬牙不肯再躺,非要自己走。脚下那条路,从贵州一直延到后面的雪山草地,她一步也没少。 这些年,外界提起她,总爱先说一句“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再加上“巾帼英雄”“红军女战士典范”一类的词。听着挺响,其实最硬的那部分,都闷在她身上:永新的牢门被撞开,吉安小屋里的那盏灯,茅坪山风里那身军装,五里排空袭留下的十七块弹片,还有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病房里慢慢暗下去的那一刻。 那天,她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