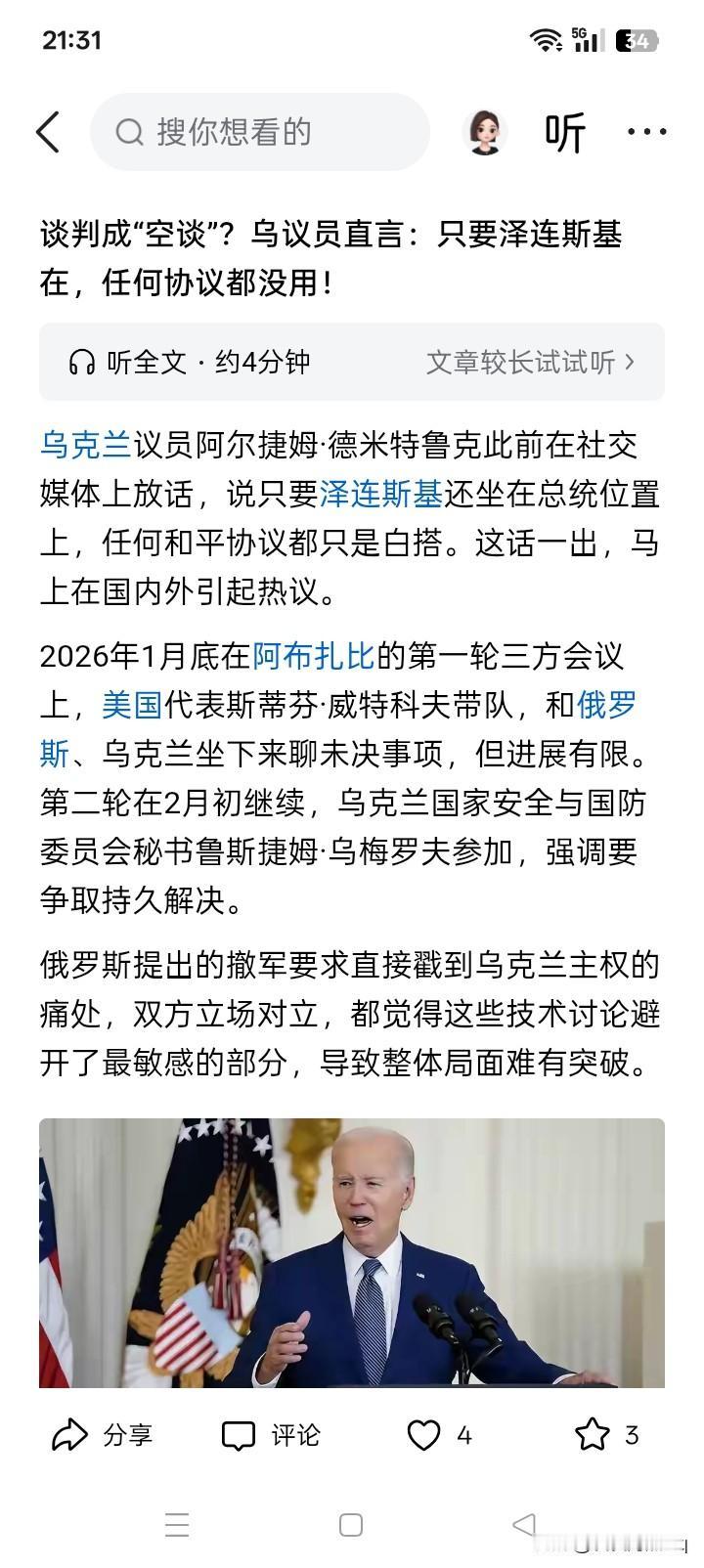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决定尝试一番。 1928年, 高伯龙出生在广西南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给他买过一整套《万有文库》和《小学生文库》, 儿童时代几乎都泡在书堆里, 心里早早种下“做科学家”的念头。 求学之路并不平顺, 父母四处辗转, 学校一换再换, 课程常常跟不上, 靠的是自己啃书、两次跳级, 小学毕业才10岁多一点。 抗战打乱了节奏, 高伯龙从课堂走向战场。战后再回学校, 1947年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 大学四年成绩一直靠前, 1951年毕业后被分到中科院应用物理所, 不久又被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讲课。 高伯龙原本想专职做科研, 几次申请调回研究所都没成, 索性认了一个理: 国家需要在哪儿, 就在哪儿扎根。 1970年代初, 美国已经在1960年做出激光陀螺, 中国在这一块几乎一片空白。 钱学森意识到, 谁掌握了这一技术, 谁就掌握了高精度制导的关键, 于是费尽周折弄回两页关于激光陀螺的手写笔记, 转交给国防科技大学。 那两页纸, 成了高伯龙此后一生的重心。 国防科大刚拿到资料时, 很多人只觉得眼前是块“高精尖顽石”。纸上只有最基本的原理、简单光路示意, 没有成体系的实验步骤, 更谈不上详细参数。 多数人选择观望, 高伯龙却主动接过, 组织几名年轻教师, 白天照常上课, 晚上把全部心思丢进实验室。 起步阶段谈不上什么“高端平台”。旧食堂被改成实验室, 器材大多是从废堆里翻来的材料。 为了做一个稳定的平台, 高伯龙亲自推着板车去工地借大理石, 为了节省经费, 在工地和学校之间往返了好多趟。真空设备买不起, 就把玻璃罐改造成简单的真空腔。 那两页英文手稿先被逐字翻译成中文, 一行一行推导, 手写稿很快堆成半人高。很多计算只能靠纸笔反复演算, 失败成了家常便饭, 故障和原因被一条条写进厚厚的本子里。 真正拦路的, 是高精度光学镀膜和超精密加工。国外靠成熟工业体系支撑, 中国当时连合格光学玻璃都紧缺。高伯龙带着团队用最笨的办法, 手工打磨、一次次镀膜、一次次检测。 高伯龙常常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十五六个小时, 连过年也不肯离开仪器, 角落里备着锅碗和几包面条, 饿了煮一碗接着干。一个年度下来, 团队累计加班时间超过1500小时。 1978年夏天, 第一台激光陀螺原理样机终于在简陋的平台上稳定亮出了那一束绿色激光。那一小截光路, 意味着中国在这个领域终于站到了起跑线上。 但原理样机离真正能用还差得远。接下来十几年, 高伯龙又带着学生啃检测仪器、啃信号稳定性, 解决了高精度光学检测这一卡脖子环节。 1994年11月, 中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通过专家鉴定, 国家终于拥有了可以装进装备里的“国产陀螺心脏”, 成为世界上第4个能独立研制这项技术的国家。 激光陀螺的落地应用, 不只是让导弹、战机、军舰有了稳定可靠的方向和速度信息, 还把工业测量的精度推到了微米甚至纳米级, 为后来的精密制造、自动化生产打下基础。今天人们谈起自动驾驶汽车、智能装备的姿态控制, 很多地方都有激光陀螺那一套原理在默默工作。 按常理说, 走到这一步, 高伯龙已经足以“功成身退”。 高伯龙却觉得, 做出样机只是第一步, 真正重要的是把这一套东西完整嵌进惯性系统, 让武器装备在实战环境中也能用得住、用得准。 国外有专家断言, 四频差动激光陀螺难以工程化, 上不了装备, 高伯龙偏偏不信。七十多岁的老人再次带队冲在前线, 把激光陀螺和整套惯导、瞄准系统绑在一起, 最终让中国成为当时唯一把这项新技术真正用在武器上的国家。 实验台上的高伯龙, 和生活里的高伯龙形成了鲜明反差。衣服多是几十块钱的旧货, 有件棉袄穿了三十年, 医护准备拿去洗洗, 高伯龙还担心洗坏。 有人问起这些年图个什么, 高伯龙只说, 自己小时候翻开那些书时, 就想为国家做点真正有用的东西, 后来遇到这两页手稿, 便再也放不下。 2017年, 高伯龙在长沙离世, 享年89岁。从1970年代接手那两页纸算起, 整整四十多年, 一个军工院校教师带着几个学生, 在旧食堂里搭出来的实验室, 把原本被视为高不可攀的技术一点点啃下来, 把中美在激光陀螺上的差距硬生生缩短了二十年。 这一生看上去只围着“激光陀螺”四个字打转, 却在雷达之外, 为中国立起了一枚看不见的“定海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