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193 年,刘邦的庶长子刘肥进京朝拜。在家宴中,吕后看不惯刘肥,笑嘻嘻地说:“刘肥,我是真稀罕你啊。要不你给你的妹妹鲁元当儿子吧?”刘肥端着酒樽的手顿在半空,脸上的笑意僵住。他知道吕后这话不是玩笑,鲁元公主是刘邦和吕后的亲生女儿,比自己还小几岁,让他这个兄长做妹妹的儿子,明摆着是羞辱,更是试探他有没有异心。他不敢直接拒绝,也不能真的答应,只能放下酒樽,低着头说,此事关乎伦理纲常,容他回去仔细思量。 公元前193年的长安,秋风刚卷走最后一片槐叶,刘邦的庶长子刘肥踩着落叶进了未央宫。 他是来朝拜的,作为长子却非嫡出,这身份像块浸了水的棉絮,压得他每步都沉。 家宴设在偏殿,铜灯的光暖黄,却照得案上的酒樽边缘泛着冷。 吕后坐在主位,凤钗上的珠翠随着她的笑轻轻晃,晃得刘肥眼皮发跳。 这是他入京后第一场家宴,本以为是寻常的宗亲相聚,可吕后开口时,空气里的酒气突然就凝住了。 “刘肥,”她声音软得像团棉花,“我是真稀罕你啊——要不你给你妹妹鲁元当儿子吧?” 鲁元公主就坐在旁边,比刘肥还小五岁,听见这话,手里的玉箸“嗒”地掉在案上,脸霎时白了。 刘肥端着酒樽的手顿在半空,琥珀色的酒液晃了晃,差点泼出来;脸上的笑还僵着,像被人拿浆糊粘住了似的。 他怎么会不懂?鲁元是吕后的心头肉,让他这个兄长做妹妹的儿子,哪是稀罕?分明是把“庶出”两个字揉碎了,撒在他脸上——更狠的是,这是在问:你敢不敢不认自己的身份?敢不敢有半点异心? 他不能怒,也不能笑,只能缓缓放下酒樽,杯底与案面碰撞的轻响,在寂静里像敲了声钟。 低着头,鬓角的汗滴在衣领上,洇出一小片深色:“太后,”他声音比案上的残羹还哑,“此事关乎伦理纲常,是天大的事,容臣……容臣回去仔细思量。” 有人说吕后此举是单纯的刻薄,可深宫里的话,哪有“单纯”二字? 刘肥的封地在齐,七十余城,是所有皇子里最富庶的;刘邦临终前虽没明说,可“长子”两个字,本身就是对嫡子刘盈的隐忧——吕后是在拿伦理当刀,既要削他的锐气,又要探他的底:你到底认不认我这个太后,认不认刘盈这个皇帝? 吕后的笑里藏着刀,是因为权力场上从没有“放心”二字;刘肥的低头,不是懦弱,是他清楚,此刻但凡说一个“不”字,明日长安城外的乱葬岗,就会多一具无名尸。 这种试探像根毒刺,扎进刘肥的骨缝里,往后许多年,他再不敢轻易入京,连封地的赋税都主动减半,只求吕后能忘了他这个“稀罕”的长子。 你说,那时的刘肥望着案上那樽没喝的酒,心里想的是母亲曹氏早逝时的模样,还是齐地七十城的百姓? 那顿饭终究是吃完了,刘肥揣着一身冷汗回了驿馆,连夜让人送去城阳郡的地图——把最富庶的城邑献给鲁元公主做汤沐邑,这才让吕后暂时松了手。 可这一让,也让后来的皇子们看清了:在皇权的棋盘上,庶出的血脉,从来都是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棋子。 若你也遇上进退两难的时刻,别急着硬碰,先想想自己真正要护住的是什么——是一时的脸面,还是身后的人? 铜灯的光渐渐暗下去,刘肥起身时,案上的酒樽还在,只是酒液早已凉透,像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在隐忍里落了地,却也结了层薄薄的冰。
项羽这辈子有多狂?创造三个世界第一,迄今无人打破。项羽从小就不走寻常路。叔父让他
【3评论】【5点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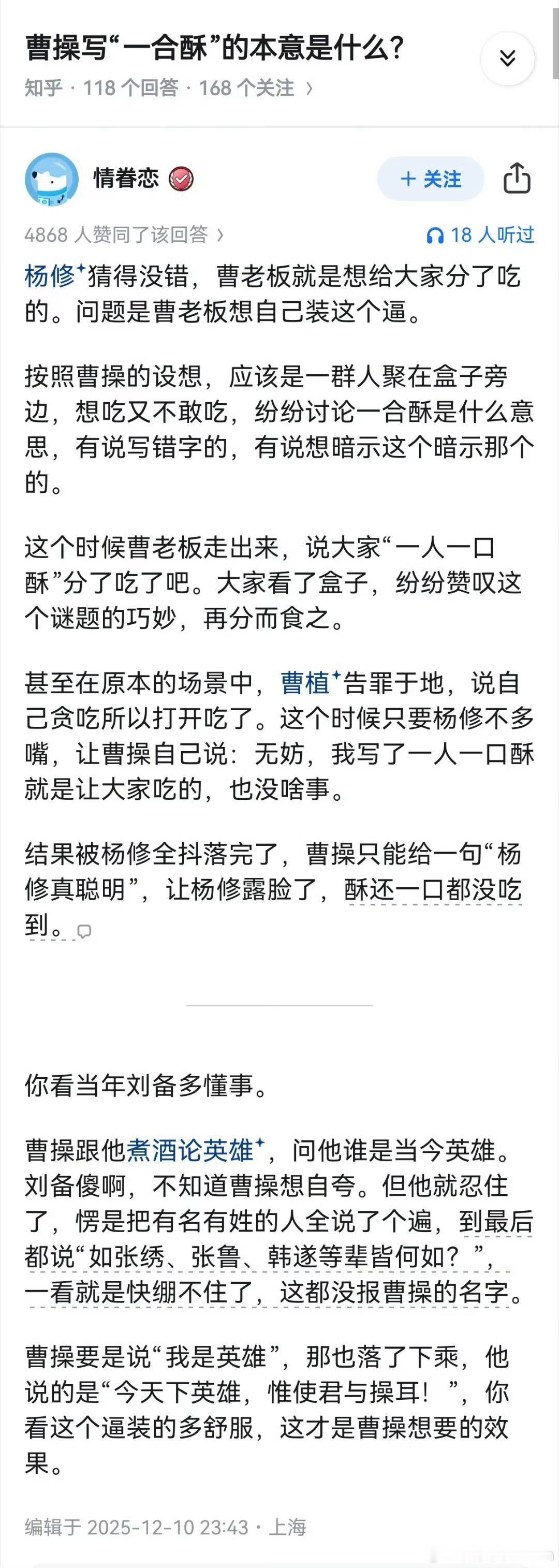

![刘备年轻时不怕失败,大不了从头再来。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年事已高没机会重来了[6]](http://image.uczzd.cn/1521207132244544198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