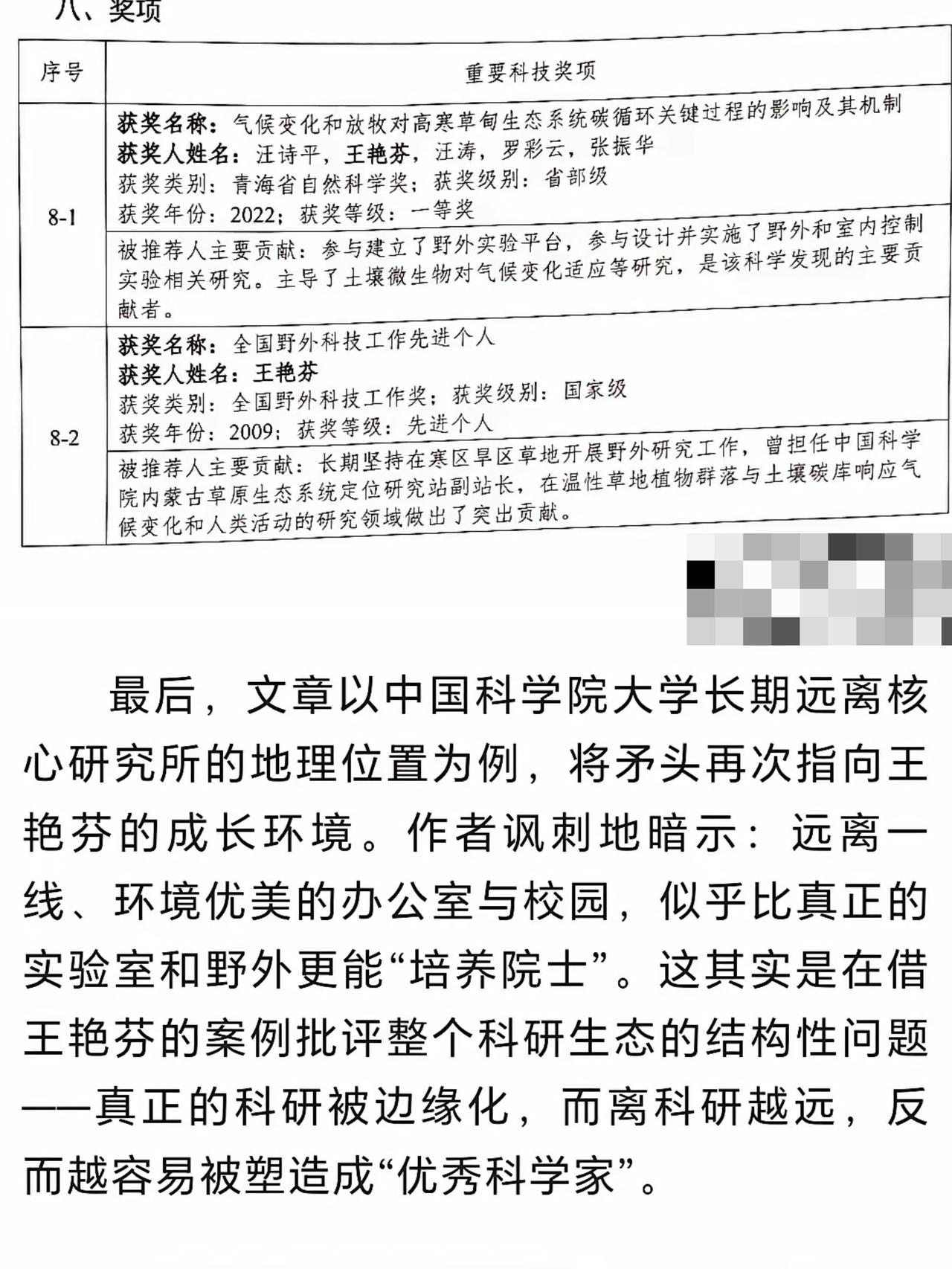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科技封锁的铁幕下,一项决定中国国防科技走向的关键技术正悄然萌芽。 激光陀螺这项被美国严密封锁的“国之重器”,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更是导弹、战机实现高精度导航的“心脏”。 当钱学森冒着巨大风险从美国带回这项技术的零星资料时,中国科研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是退缩于“无人区”的未知恐惧,还是迎难而上开启自主创新的破冰之旅成为当时摆在科研人员面前的艰难选择。 当时正值美苏冷战军备竞赛白热化阶段,美国实施《出口管理法》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高科技禁运,激光陀螺被列入“战略物资清单”,严禁向中国转让技术及相关设备,这种技术封锁让我们的科研之路难上加难。 钱学森利用加州理工学院时期与激光陀螺先驱RichardV.Pound的学术友谊,通过华裔学者辗转获取关键文献。 据《钱学森传》记载,这批资料包含23篇期刊论文、7份实验报告,其中《环形激光陀螺的误差分析》一文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参考。 国防科技大学的科研人员拿到这些资料时,却发现这就像给了一张藏宝图,却没有钥匙,还要自己造寻宝工具,很多人都望而却步。 39岁的高伯龙当时是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教师,本来想专注于教学工作,但后来发现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可能会影响国防安全。 在教研室动员会上,他沉默良久后说:“搞科研哪有不冒险的?钱学森先生都把‘火种’送来了,我们不能让它灭了。” 这句话让他从此踏上了长达20余年的激光陀螺攻坚路,也让中国在这一领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面对残缺的英文资料,团队成员轮流翻译,高伯龙逐页批注,仅《激光陀螺的锁区效应》一文就写下1.2万字笔记。 他发现美国资料刻意隐瞒了“闭锁阈值”的关键数据,遂提出“四频差动”理论模型,为后续实验奠定基础。 没有精密转台,他们用自行车轮改装机械转动装置;缺乏激光稳频电源,就用收音机零件组装控制系统;腔体加工精度要求0.1微米,团队用“研磨膏手工抛光加光学干涉检验”的土办法,使加工误差控制在0.3微米内,这些看似简陋的方法却解决了一个个技术难题。 1976年,首次整机组装后,陀螺漂移量达10度/小时,远超出0.01度/小时的设计标准。 有人建议放弃,高伯龙在实验室墙上贴出“绝不认输”四个大字,带领团队重新梳理137组实验数据,最终发现是腔体应力导致的偏振误差。 1979年,采用“熔融石英一体化腔体”技术,解决材料热变形问题,陀螺漂移量降至0.5度/小时,实现了真正的“零点突破”,这一突破让团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985年,中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鉴定,漂移精度达0.001度/小时,性能接近美国同期产品。 此后,这项技术先后装备于东风-31洲际导弹、歼-10战机、094核潜艇,使武器系统命中精度提升一个数量级。 同时,衍生出光纤陀螺、微机电陀螺等系列产品,应用于高铁导航、石油钻探等民用领域,2010年,相关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评审专家称这项成果使中国惯性导航技术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 高伯龙在科研领域一直坚持不署名、不领奖、不接受采访的“三不原则”,1996年退休后拒绝所有荣誉称号,坚持“成果属于团队”。 学生整理其遗物时发现,1982年的技术报告扉页写着:“个人是渺小的,唯有将自己融入国家需求,才能成就真正的事业。” 他创建的国防科大“惯性技术实验室”培养出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培德在内的56名专家,他首创的“问题导向式教学法”被写入《国防科大教学大纲》,影响至今。 如此看来,高伯龙用一生证明真正的科研从来不是追热点、赶时髦,而是在无人区里种庄稼,在荒漠中开河道。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科技自立自强的今天,这种“把冷板凳坐热”的精神,恰是破解“卡脖子”困境的密钥,更是中华民族实现科技强国梦的底气所在。 当我们在东风导弹的精准命中中、在国产航母的凌波斩浪里、在北斗卫星的浩瀚星空中感受国家力量时,不应忘记那些在实验室里与激光共舞的日与夜,正是这些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们铸就了国家的科技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