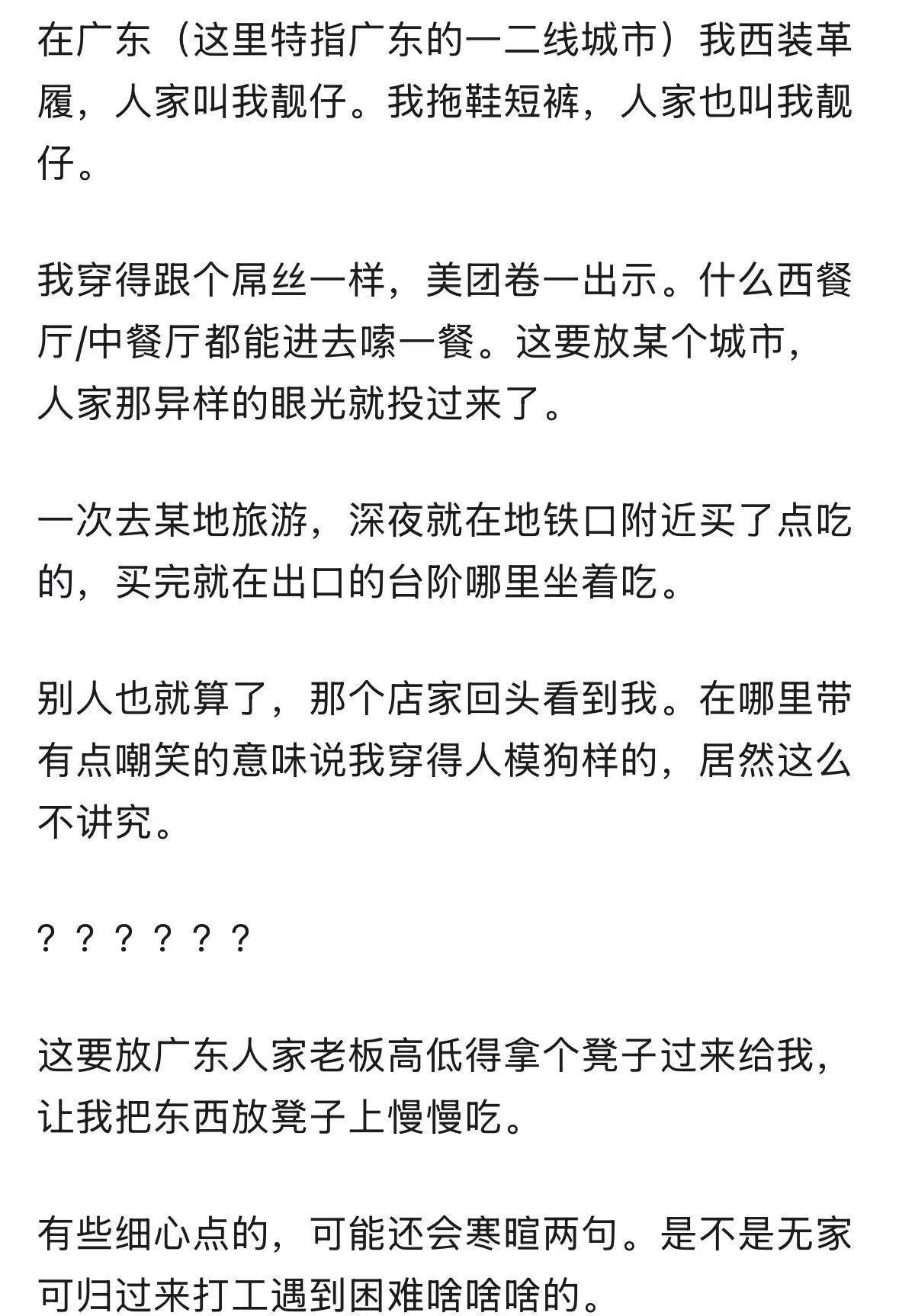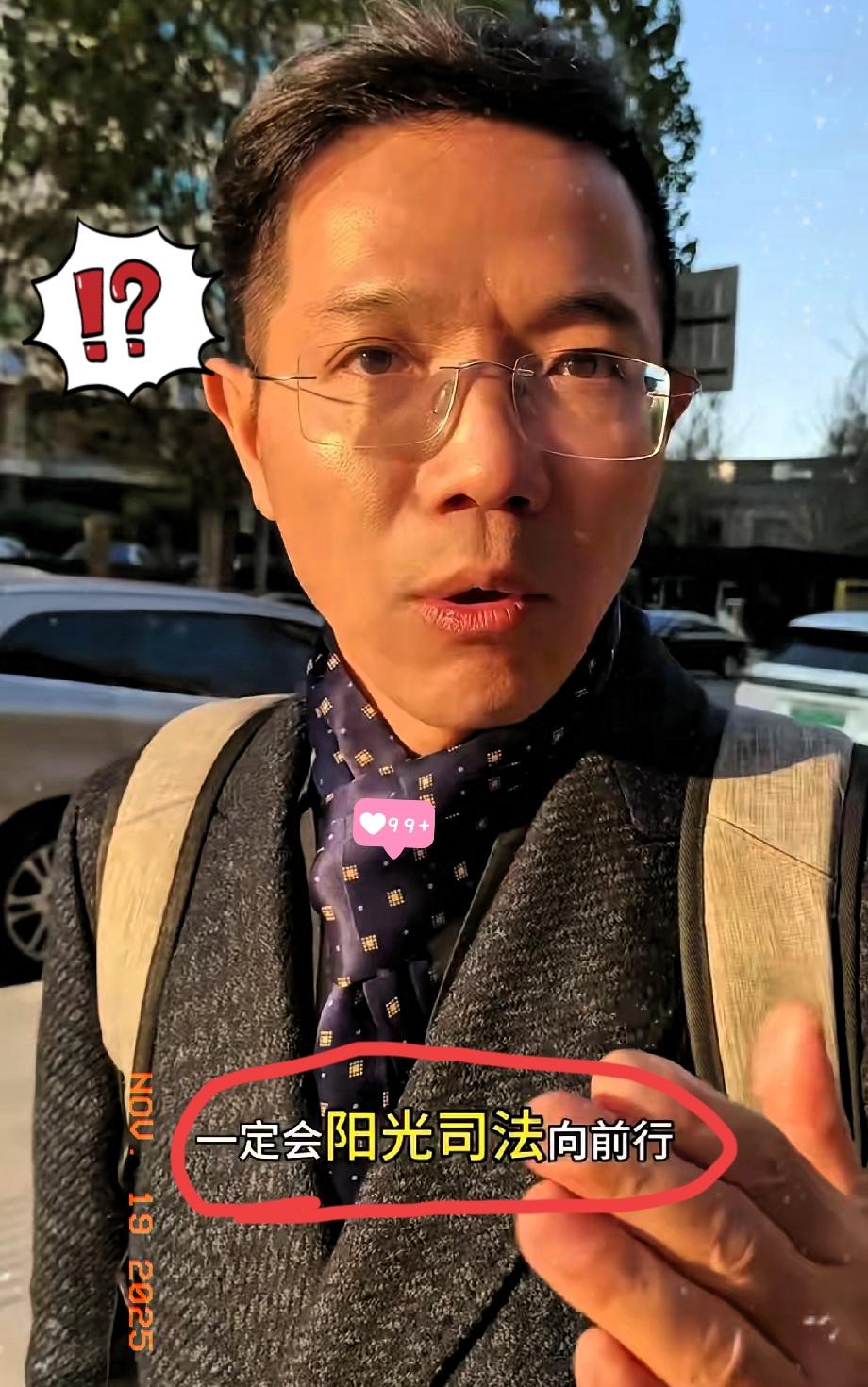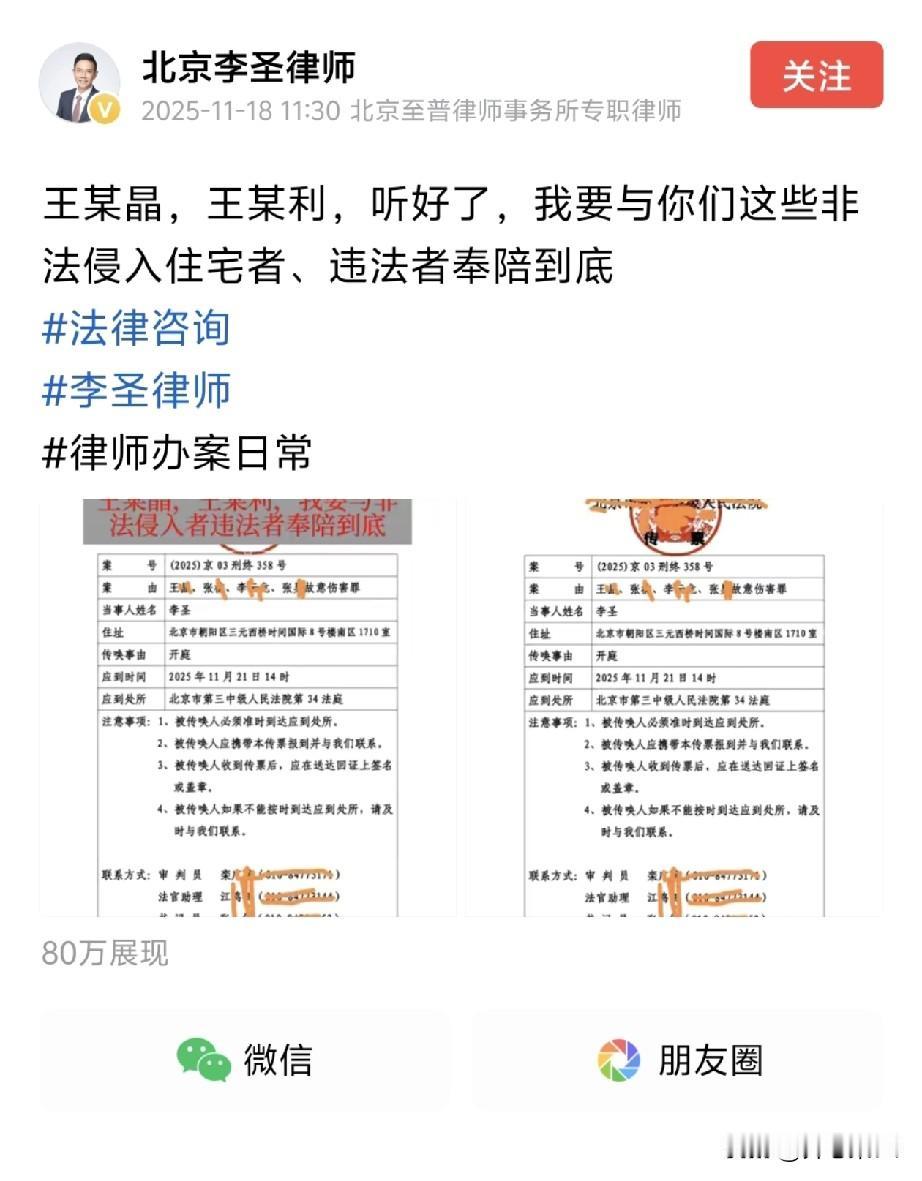2011年,广东一女子亲手溺死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然而在接受法院判决时,却有成千上万名群众为其求情,就连她的丈夫都表示她没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1998年之前,韩群凤的人生剧本拿得相当不错。自己在东莞一家银行当大堂经理,丈夫黄卓林是家媒体记者。夫妻俩工作体面,感情和睦。 1998年6月,喜上加喜,韩群凤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全家人都沉浸在幸福里。可这份幸福,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慢慢变了味。 到了孩子两岁,别的孩子牙牙学语、满地乱跑时,韩群凤的两个儿子却始终不会说话,站立不稳,甚至不受控制地流口水。 夫妻俩心里咯噔一下,抱着孩子冲进医院。诊断书像一道晴天霹雳,砸碎了所有幻想——先天性脑瘫。原因是早产导致的脑部缺氧。 那一夜,韩群凤夫妻俩彻夜无眠。 从那天起,“希望”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变得极其昂贵。 最初,韩群凤没认输。她咬着牙,要给孩子治病。 她先是在银行附近租了房,请了两个保姆。自己呢?白天上班,中午休息时间就发疯一样跑回家,给两个孩子喂饭,等他们睡下,再跑回银行。 听说有个镇上的按摩师傅技术好,她就每天下班带着两个孩子去做按摩。一个月光按摩费就得5000多。 这种疗法见效慢,花费高,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根本撑不住。 很快,韩群凤做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决定:辞职。 她放下了银行经理的身份,成了一个全职妈妈,一个24小时连轴转的“特护”。 丈夫黄卓林,一个文人,扛起了整个家所有的经济重担。夫妻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开始了一场长达13年、几乎看不到终点的战斗。 她带着孩子跑遍了广东乃至全国的大医院,得到的答复永远是“无法治愈”。 亲戚朋友都劝她:“再生一个吧,你们得有自己的生活。” 韩群凤拒绝了。她说:“我只想全心全意照顾好这两个孩子。” 在她倾尽心血的照料下,奇迹似乎发生过。两个孩子慢慢学会了喊“妈妈”,甚至能颤颤巍巍地走几步。 这声“妈妈”,对韩群凤来说,可能比什么都重要。这让她觉得,一切付出都值了。 但命运没有松手。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13岁了,他们的体重在长,个子在长,但病情没有根本好转。他们依旧无法自理,吃喝拉撒全靠韩群凤一个人。 13年,4700多个日夜。丈夫要挣钱养家,常常在外。大多数时候,是韩群凤一个人,守着两个残疾的孩子,困在一个压抑的房子里。 她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敏感,易怒。她会忍不住对孩子发脾气,发完脾气,又抱着两个儿子痛哭流涕。 邻居们都说,韩群凤太伟大了,太不容易了。 可这份“伟大”的背后,是一个女人精神世界的彻底垮塌。她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自己。她被“母亲”这个身份,活活钉死了。 2010年11月20日,韩群凤彻底崩了。 那天晚上,她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她用一种她认为的“解脱”方式,亲手结束了两个儿子的生命。 随后,她给丈夫黄卓林发了条短信:“我和孩子先睡了,不要打扰我们睡觉。” 她换上新睡衣,写好遗书,喝下了准备好的农药,躺在了两个儿子身边。 第二天,黄卓林回到家,推开门,看到了他一生无法承受的画面。他疯了一样打120,把母子三人送进医院。 抢救的结果是:韩群凤活了下来,两个孩子走了。 活下来的韩群凤,面对的不再是家庭,而是法律。她被警方带走,罪名是——故意杀人。 这个案子,在2011年6月开庭。法庭上发生的一切,比悲剧本身更震撼。 首先,是丈夫黄卓林的表态。 他作为受害者家属,却站起来替妻子求情。他对法官说:“这13年,她背负了太多。我太了解她的痛苦。我愿意原谅她,她没有错!” 紧接着,是邻居和亲友。 他们自发组织,写了10多页长的联名请愿信,上千人签名,请求法院对韩群凤“法外开恩”。 这些邻居,是亲眼见过韩群凤如何抱着比自己还高的儿子上下楼,如何日复一日给他们喂饭擦身的人。他们最懂那份绝望。 最关键的一幕,是韩群凤的律师夏良恒,请来了一位特殊的“证人”。 这位证人来自广州,她也是一位母亲,她同样有两个患有脑瘫的孩子。 她站在法庭上说:“我希望人们能从我身上,理解韩群凤的苦衷……社会对我们这些特殊群体的关爱远远不够。我希望社会能帮助我们,不要再让悲剧重演!” 这番话,让整个法庭陷入了沉默。 韩群凤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哪怕是母亲。这是法律的底线。 但她为什么这么做? 司法鉴定给了答案:韩群凤在案发时,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被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通俗点说,她当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已经因为常年的精神折磨而“明显削弱”了。 最终,法院综合了所有因素——她的犯罪事实、她的精神状态、丈夫的原谅、上千群众的求情——做出了一次极其艰难的判决。 韩群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这个判决,是法律能给出的最大“温度”。它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正视了一个母亲13年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