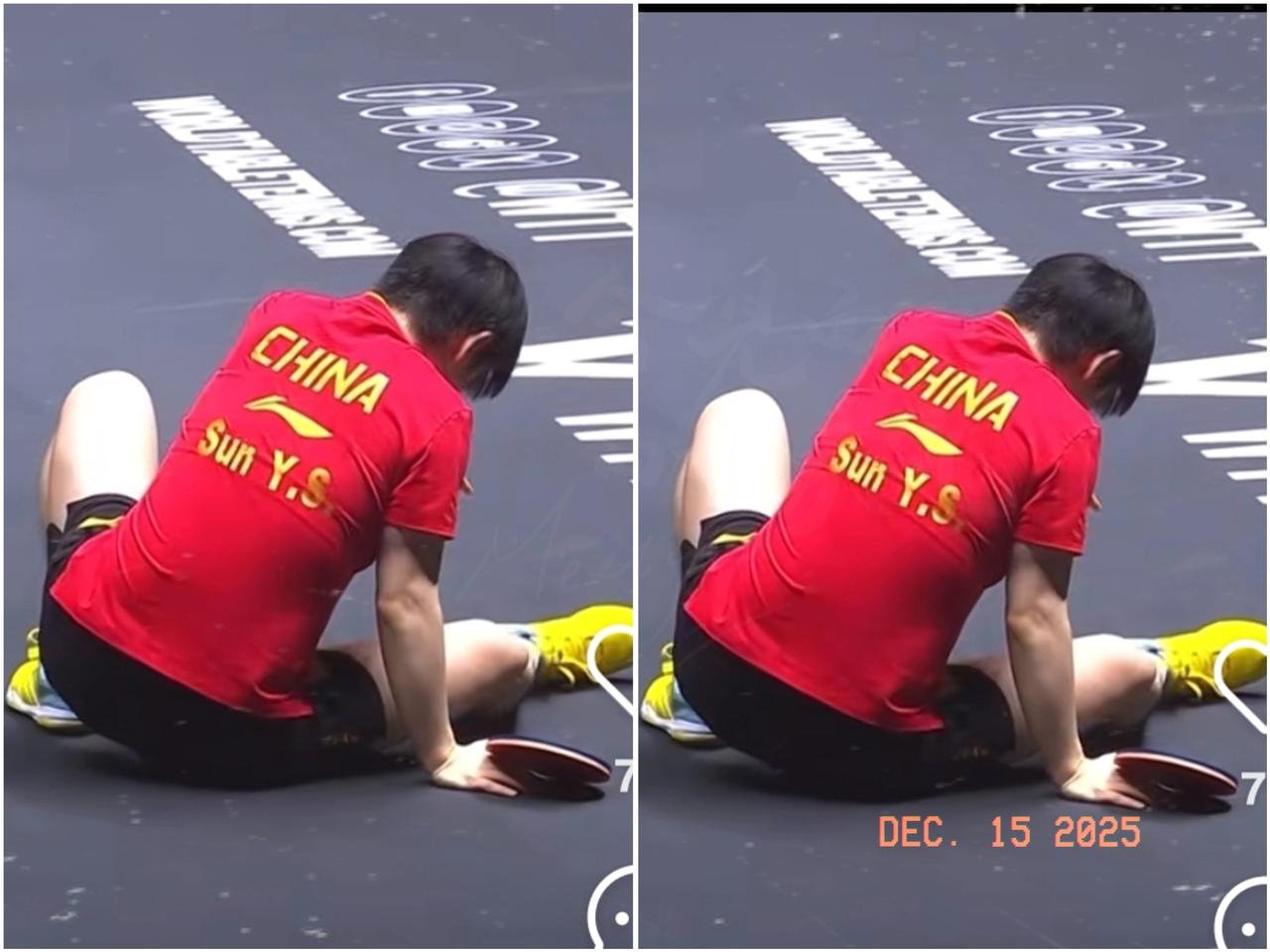我从得脑梗以后,十四年了,现在生活得很好,从没有复发过,但是,生活的确是太苦了。刚发病那年我才四十六岁,正是能扛事的年纪,早上起来准备去工地干活,刚走到门口就觉得左腿发沉,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 四十六岁那年的春天,我还攥着工地的工牌——塑料壳边角磨出毛边,印着“钢筋组老李”,早上五点半的天刚泛白,院子里的水泥地还凝着夜露。 正是能扛事的年纪,前一天刚和工友打赌,说这周要把三号楼的钢筋捆完,多赚两百给娃交学费。 刚迈过门槛,左腿突然往下坠,不是累的酸,是钝钝的沉,像被地里的草根死死拽着脚踝——低头看时,裤脚还好好垂着,可脚就是钉在原地。 我伸手去抓门框,松木的纹路硌得手心发疼,可身子还是斜斜地歪下去,工牌从口袋滑出来,“啪”地拍在水泥地上,塑料壳裂开条缝。 以前扛五十斤钢筋上三楼不喘气,现在连站都站不稳? 救护车的鸣笛声越来越近时,我盯着那道裂缝,突然想起工头说的“男人四十如狼,五十如虎”,我才四十六,怎么就成了这副样子。 十四年了,医生说我命大,梗在脑干边缘,没伤着要害;街坊见了总说“老李你福气,没复发就是最好的日子”。 可他们没见过我半夜摸黑去厕所,左腿在地上拖出“沙沙”的响,像拖着半袋漏了的沙子;没见过我想给孙子削个苹果,右手抖得刀在果皮上划出道道歪歪扭扭的线。 日子是挺好的,早上能自己煮碗粥,粥里卧个蛋;下午能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晒太阳,看对面楼的孩子背着书包跑。 只是那腿,总在我忘了它的时候提醒我——上台阶要先抬右腿,不然准得踉跄;冬天穿厚棉裤,左腿弯不过来,得让老伴帮着提。 有回孙子问:“爷爷,你走路怎么一瘸一拐呀?”我逗他:“爷爷在练武功呢,这叫‘独龙步’。”他咯咯笑,我却想起那年工地上,我追着他跑,能把他举过头顶转圈。 医生说复不复发看养护,我就每天扶着墙走二十圈,从客厅到院子,再从院子到客厅,栏杆被我磨得发亮;菜窖里的腌菜坛子,我够不着了,就让老伴把梯子架稳,我在下面递空坛子。 苦吗?真苦。 可那天晒着太阳,孙子把削好的苹果递到我手里——这次他没让我自己削,苹果皮连成长长的一条,像条红绳子。 我咬了一口,甜津津的汁水流到嘴角,左腿在地上轻轻蹭了蹭,好像没那么沉了。 工牌还在抽屉里,裂缝用胶带粘好了,照片上的“钢筋组老李”眼神愣冲冲的,像要把日子戳个窟窿。 现在的我,戳不动窟窿了,就慢慢凿吧,一锤一锤,凿出点甜来。
我从得脑梗以后,十四年了,现在生活得很好,从没有复发过,但是,生活的确是太苦了。
奇幻葡萄
2025-12-16 17:46:55
0
阅读: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