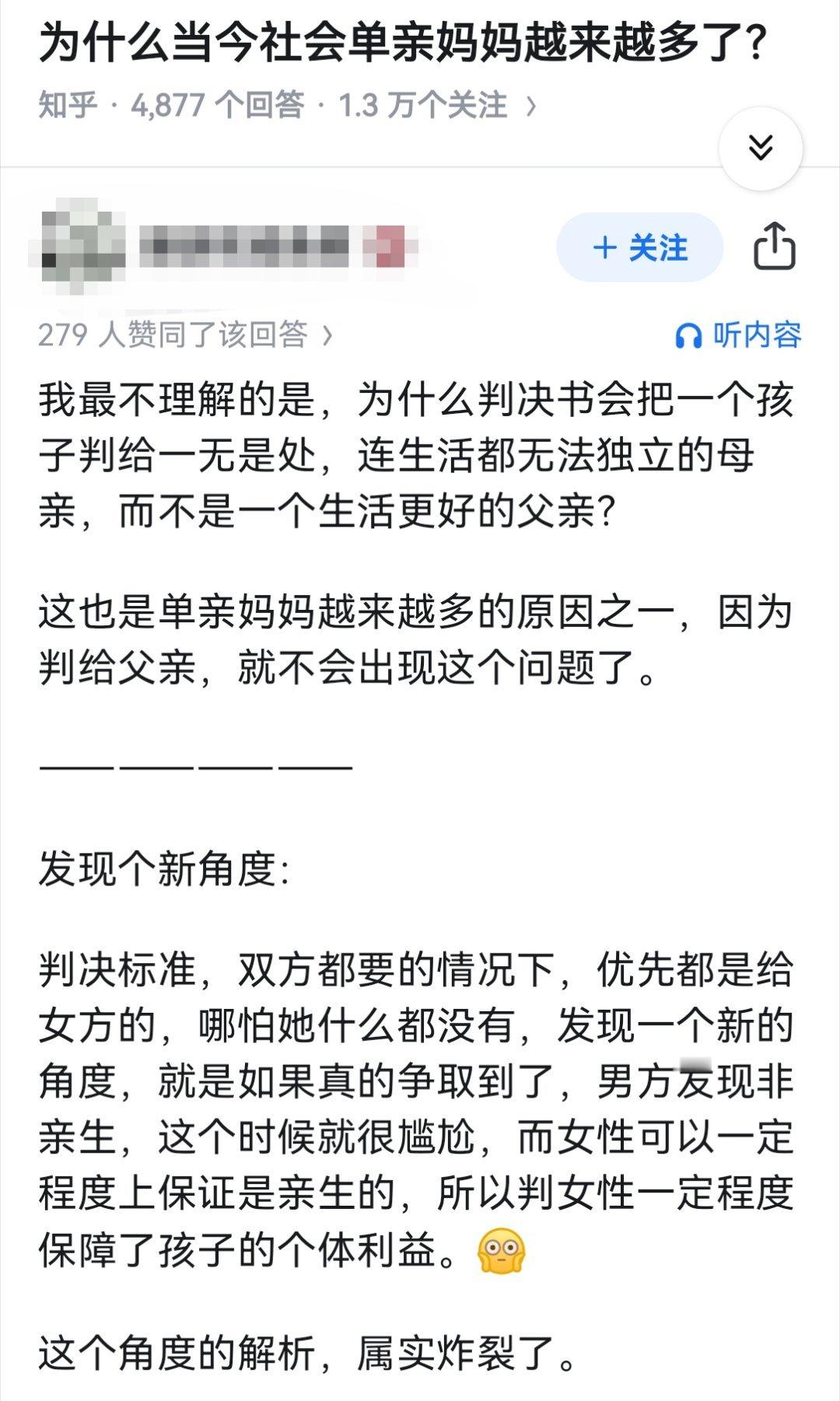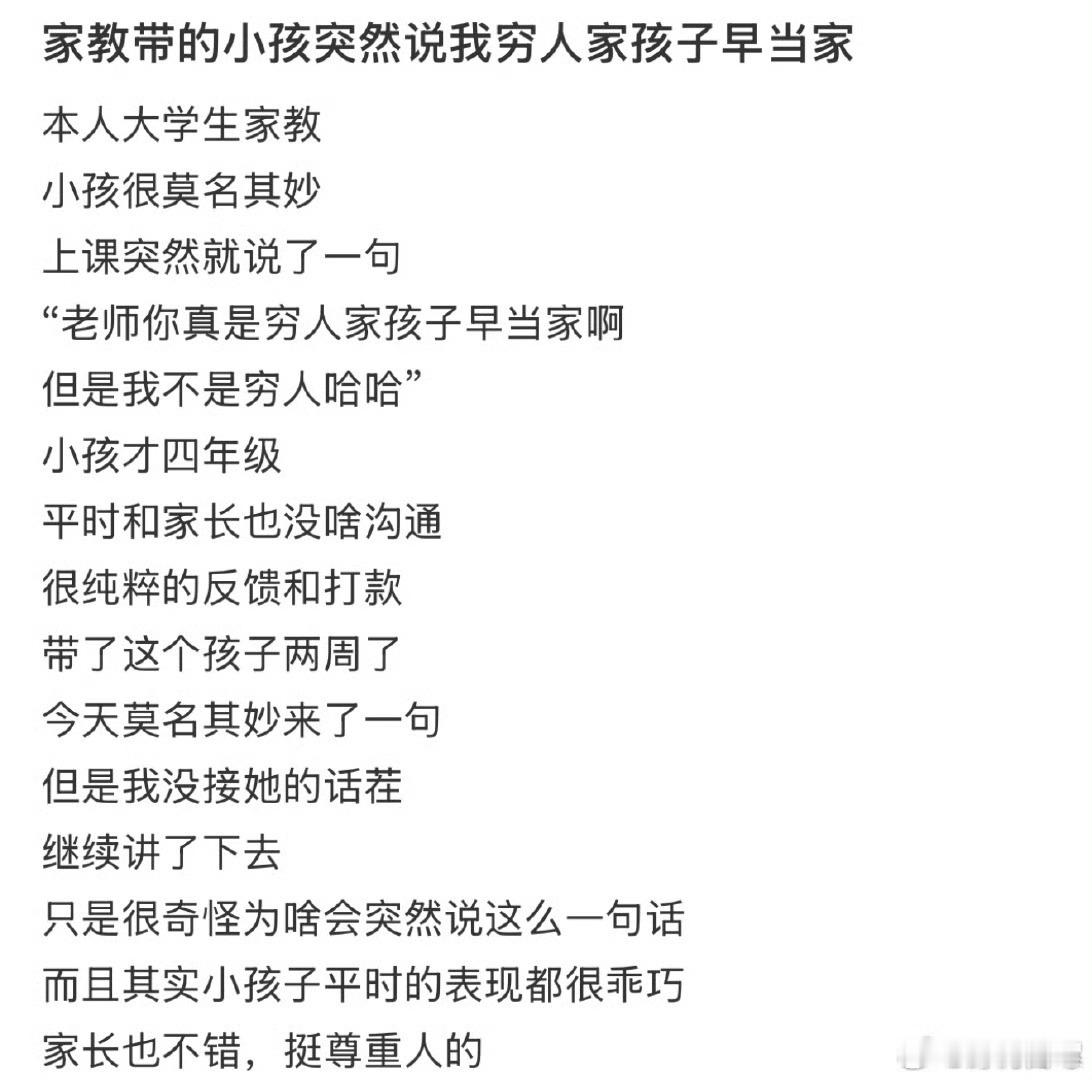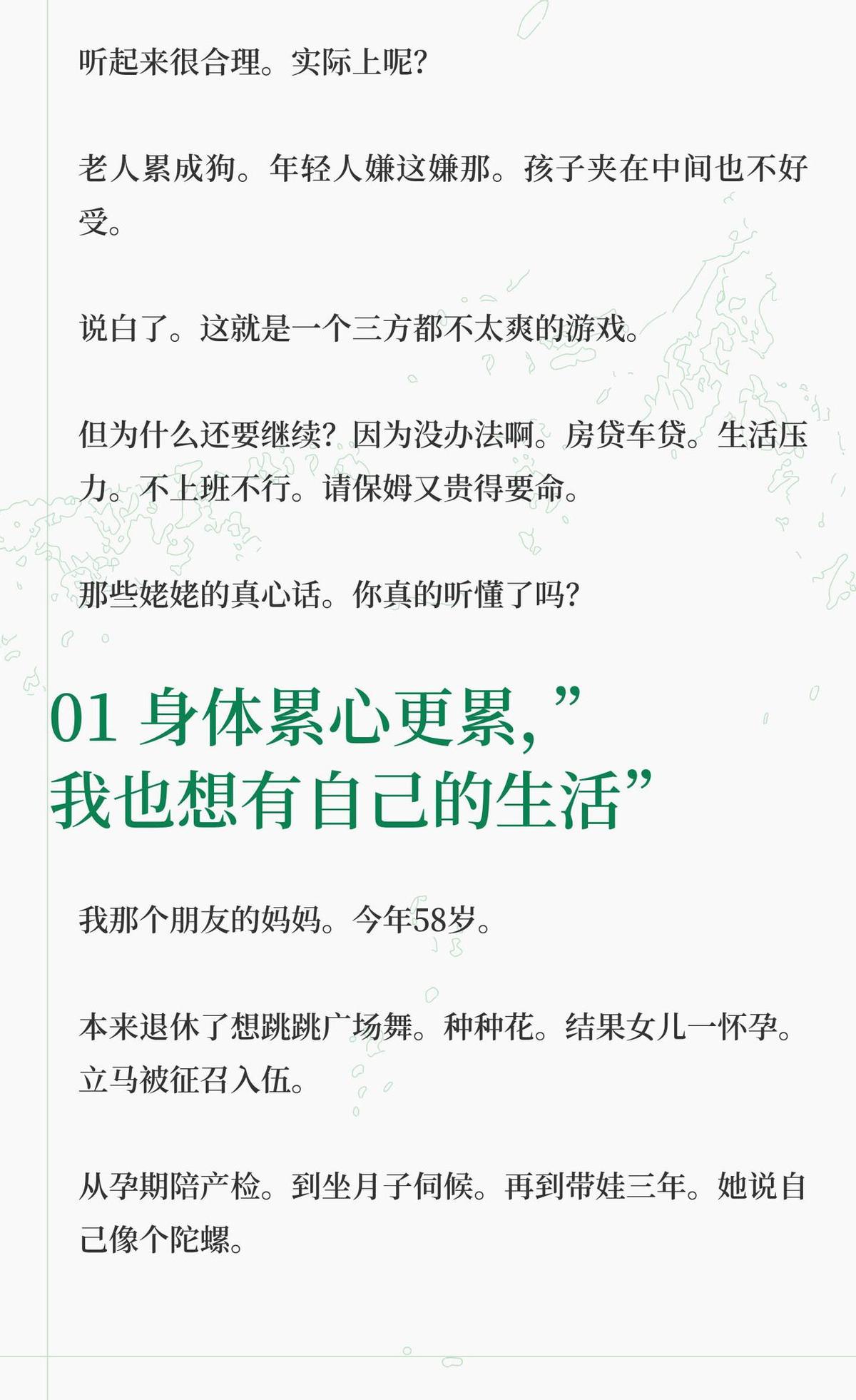孩子越恶毒的话,父母越要温柔接住。“你怎么不去死?”这是孩子对我说得最狠的话,而且是握着拳头、两眼冒火般吼我。我没有与她进一步发生纠缠与冲突,默默地走进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眼泪纵横。枕头很快洇出深色的湿痕,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像要钻进脑子里,我攥着被角的手不住发抖——那是我养了十六年的女儿,此刻却像只被惹急的小兽,用最锋利的爪牙对着我。 夏天的傍晚总是黏糊糊的,空调坏了三天,客厅里的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扬起的风都带着热气。 我端着切好的西瓜走进女儿房间,想聊聊她昨天没及格的数学卷,话刚到嘴边,她猛地把笔摔在桌上——“你怎么不去死?”声音像淬了冰,每个字都扎人。 她攥着拳头,指节泛白,眼睛里的火快烧出来了,我甚至能看见她后颈的青筋一跳一跳的,连带着桌上的玻璃杯都跟着晃了晃,水洒出一小圈,洇湿了数学卷的边角。 其实早上她就不对劲了,书包拉链没拉好,校服领口歪着,我问她是不是没睡好,她只含糊地“嗯”了一声。 现在想来,那大概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数学卷不过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我那句“没关系下次努力”,在她听来或许更像一句轻飘飘的嘲讽。 我没敢看她,转身进了自己房间,关门前瞥见她站在原地,肩膀微微抖着,像只被雨淋湿的小兽,爪子还在徒劳地挥舞。 躺在床上,眼泪比预想的来得快,枕头芯里的荞麦壳硌得后脑勺疼,窗外的蝉还在不知疲倦地叫,一声接一声,像在替她骂我——你怎么这么没用,连自己的孩子都哄不好。 我攥着被角的手越收越紧,指甲掐进掌心,脑子里乱糟糟的:那是我从襁褓里抱大的孩子啊,会奶声奶气喊“妈妈”的小不点儿,会把舍不得吃的糖塞我嘴里的小棉袄,怎么突然就长出了这么尖的刺?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咔嗒”一声轻响,接着是拖沓的脚步声,停在我门口。 我屏住呼吸,听见布料摩擦的窸窣声,然后是极轻的、带着哭腔的“妈”,像小猫用尾巴扫我的手背。 我没动,等她推开门,看见她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纸巾,眼睛红得像兔子,校服袖子还沾着刚才摔笔时蹭到的墨水印,“我不是故意的……”她的声音哽咽着,“数学考砸了,同桌还笑我笨,说我肯定考不上重点高中,我觉得自己好没用,你进来的时候,我就……就想把所有坏情绪都推给你,好像你疼了,我就不疼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她吼出的狠话不是淬向我的冰,而是她自己困在冰里时,慌乱中挥出的、想破冰的斧头——她不是想伤害我,是不知道怎么喊“救命”。 十六岁的孩子,心里装着比山还重的压力,却还没学会给情绪安上刹车,遇到委屈就只会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用最硬的刺对着最亲的人,以为这样就能保护自己。 她用最伤人的话刺向我,这是事实;可我知道,那不是她的本意,是少年人无处安放的焦虑和脆弱在作祟,像被踩了尾巴的猫,除了哈气炸毛,想不出别的办法。 我没有回嘴,没有摔门,只是给了她一个“暂时安全”的空间,让她能在情绪的海啸退去后,看见自己留在沙滩上的、其实是脆弱的贝壳——而不是我被刺伤后留下的血痕。 那天晚上,她趴在我床边哭了很久,说了很多学校的事,那些我从没听过的焦虑和委屈,像一颗颗小石子,被她攒了很久,终于敢摊开在我手心里。 后来她学会了说“妈,我今天心情不好,想自己待会儿”,而不是用狠话划开一道伤口;学会了在我递水时小声说“谢谢”,而不是别过脸假装不在乎。 其实孩子的狠话就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猛,但只要你撑着伞站在原地,不躲不骂,等雨停了,她会发现你还在,彩虹也会从她眼里慢慢爬出来。 半夜醒来,摸了摸枕头,湿痕已经凉透了,窗外的蝉终于歇了,月光从窗帘缝里溜进来,刚好照在女儿放在我床头柜上的那杯温水——杯子里的水没晃,稳稳的,像我们重新黏合起来的、带着裂痕却更结实的关系。
怎么判断一个孩子有没有数学天赋?
【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