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葬完母亲,我没再进屋和父亲打招呼,而是悄悄地走了。刚上车,父亲打来电话:你都不陪陪我吗?我冷冷地说:我为我妈感到高兴,她终于解脱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只有电流的滋滋声,我咬着牙挂了电话,发动车子时,手却控制不住地抖。 母亲的骨灰盒放进墓穴时,梧桐叶正往下掉,一片砸在我手背上,凉得像她临终前最后一次摸我的温度——那时候她已经说不出话,只捏着我的手指往父亲的方向扯,可我假装没看见。 刚把车开出墓园大门,手机就在副驾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的“爸”字像根刺。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三秒,按下接听键时,指节都在用力。 他的声音比昨天灵堂里还哑,带着点小心翼翼的颤:“你……这就走了?不进屋喝口热水吗?” 我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冷笑,像生锈的铁片摩擦:“喝什么?喝你以前总忘了给我妈热的那杯吗?” 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只有电流滋滋地响,像极了母亲夜里咳得喘不上气时,父亲在客厅来回踱步的脚步声。 那时候我总躲在门缝后看,看他背着手站在窗前,影子被月光拉得又细又长,像根快被压断的扁担。 “我为我妈感到高兴,”我咬着牙说,每个字都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她终于解脱了!” 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想起母亲下葬前,我整理她遗物,在床头柜最底层摸到一个铁盒子,里面全是父亲的体检报告——肝不好,腰不好,还有一张五年前的诊断书,写着“中度抑郁”。 我是不是太狠了?可他凭什么问我“陪不陪”?母亲躺病床上那三年,他有多少个晚上是在单位加班,回来时母亲的药早凉透了;我去医院送饭,看见她偷偷把药片藏在枕头下,说“你爸累,别让他知道我又不舒服”——这些他知道吗? 电话被我猛地挂断,车里死一般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微弱的风,吹起副驾上母亲的旧毛衣。 那是她亲手织的,枣红色,领口绣着小小的“安”字,她说希望我们都平平安安。 发动车子时,手怎么都稳不住,方向盘在掌心打滑,像母亲最后那段日子,我怎么也抓不住她逐渐变冷的手。 后视镜里,墓园的白墙越来越远,我好像看见一个佝偻的身影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什么东西,在风里晃啊晃——后来我才想起,那是母亲每天早上给父亲泡好的茶缸,搪瓷的,边儿上磕了个豁口,他用了二十多年。 原来有些话,没说出口的时候最疼;有些人,转身后才开始后悔。 现在我常常在路过药店时停下来,想买盒父亲常吃的降压药,却总在门口站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问一句“你还好吗”。 或许我该回去看看?可车已经开出去那么远了,远到连梧桐叶落在地上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江西,这位叫陈三多的网友,实在忍无可忍,曝光了监控!自家残疾的父亲,就坐在门口吃
【27评论】【6点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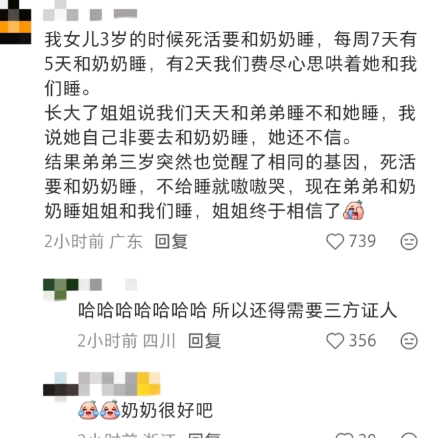




Q3Q
手抖还是先别开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