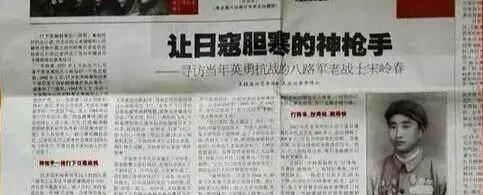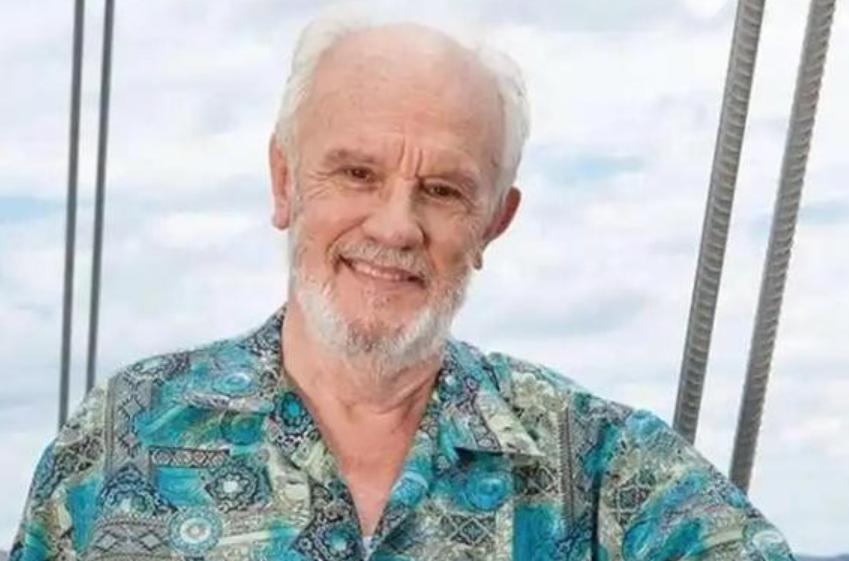1932年,澳大利亚爆发了一场人鸟大战,2万只巨鸟横扫澳洲,军队少校率领两名士兵,架起机枪迎敌,结果打光1万发子弹后,才射杀了12只。 它们就是鸸鹋。这鸟你可能在动物园见过,长得跟鸵鸟沾亲带故,身高能蹿到快两米,体重几十公斤,关键是,它跑得贼快,时速50公里。 这2万只大鸟,浩浩荡荡地从内陆迁徙而来,目标非常明确:农民们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和给牲口留的救命水。 更气人的是,它们还特别能糟蹋。吃饱喝足了,顺便把农民们好不容易拉起来的栅栏撞个稀巴烂。 这栅栏一倒,另一个“大爷”——兔子,也跟着钻进来开自助餐。农民们彻底崩溃了。 这帮农民里,不少是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他们见过大风大浪,但真没见过这阵仗。打吧?猎枪打一只,跑一群。吓唬?人家鸸鹋见识短,压根不知道啥叫怕。 绝望之下,老兵们想起了“娘家”。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澳大利亚政府:派军队来吧! 你猜怎么着?国防部长乔治皮尔斯爵士一拍大腿,同意了! 他的算盘打得挺响:第一,安抚民心,帮农民解决问题;第二,这鸸鹋肉据说不错,打来当军粮;第三,这也是个绝佳的“实弹演习”机会。于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人鸟大战”——“鸸鹋战争”,就这么“隆重”开幕了。 军方派出了皇家炮兵第七重炮连的精锐:GPW梅雷迪思少校,带着两名士兵。 武器是啥?两挺刘易斯轻机枪和一万发子弹。 梅雷迪思少校信心满满。他觉着,这不就是一场盛大的狩猎派对吗? 1932年11月2日,坎皮恩地区。 侦察兵报告:发现“敌军”主力,大约1000只鸸鹋正在一片开阔地集结。 梅雷迪思少校眼前一亮:好机会!他立刻下令,在水坝附近设下埋伏圈,就等这群“大笨鸟”自投罗网。 鸸鹋群晃晃悠悠地过来了。 “开火!” 两挺刘易斯机枪同时喷出火舌,密集的弹雨扫向鸟群。少校仿佛已经看到了成片鸸鹋倒下的壮观景象。 然而,接下来的发展,彻底超出了人类的认知。 鸸鹋们在中弹的瞬间,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倒下。它们只是晃了晃,然后……跑了。 它们不但跑了,还跑得极有战术素养。领头的“指挥官”一声令下,整个鸟群“哗”地一下化整为零,分成无数个小队,朝着四面八方疯狂逃窜。 机枪手傻眼了。刘易斯机枪打固定靶和集团冲锋是厉害,可打这种高速移动的、分散的“游击队”,瞬间抓瞎。子弹“突突突”地打出去,大部分都打在了空地上。 更要命的是,鸸鹋的羽毛非常厚实,皮糙肉厚。梅雷迪思少校在战后报告里震惊地写道:“它们的生命力跟祖鲁人一样顽强”,“它们能像坦克一样顶着机枪前进”。 第一场伏击战打完,一清点战果。军方消耗了数千发子弹,最终确认击毙的鸸鹋……12只。 是的,你没看错。一万发子弹,12只,这就是标题里那个令人绝望的数字来源。 梅雷迪思少校不服。他认为,是战术出了问题。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机动化作战。 他们找来一辆卡车,把一挺机枪架在车斗里,准备开着车追着鸸鹋打。这回,看你们往哪跑! 结果,现实又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农田里根本跑不起来。而鸸鹋,作为大自然的“越野健将”,在自己的主场上健步如飞。 于是,澳洲的荒原上出现了极其滑稽的一幕:一辆破卡车在后面疯狂颠簸,车斗里的机枪手被晃得七荤八素,根本无法瞄准。而前面几百米,一群鸸鹋迈着大长腿,闲庭信步般地领跑,时不时还回头看两眼。 到12月10日,军方弹药快打光了,梅雷迪思少校和他的士兵们也筋疲力尽。 国防部要求上报战果。梅雷迪思少校在极度尴尬中提交了报告: 总计消耗子弹9860发。 确认击毙鸸鹋986只。我们就算按最乐观的官方数字,9860发子弹打死986只。平均10发子弹,才干掉一只鸟。 全球的报纸都在看笑话。“澳大利亚军队被鸟打败了”成了国际头条。 梅雷迪思少校和他的部队,灰溜溜地撤军了。 “鸸鹋战争”以人类的完败而告终。 这场荒诞“战争”的背后,其实藏着几个特别扎心的真相: 技术的傲慢: 人类总以为,自己掌握了高科技,就能征服一切。但大自然用2万只鸸鹋告诉我们:在生态系统面前,你的“降维打击”可能只是个笑话。 “锤子”思维的陷阱: 当你手里有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你却用它来解决生态问题。用对付德国人的办法来对付鸸鹋,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诞。 大自然的“游击战”: 鸸鹋赢,不是因为它们猛,而是因为它们“不讲武德”。它们没有指挥部,没有后勤线,打了就跑,完全不按人类的战争逻辑出牌。它们用最原始的本能——适应性,碾压了人类的战术。 那么,鸸鹋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很简单,悬赏。 政府放弃了正规军,转而鼓励农民和专业猎人自己动手。事实证明,那些了解鸸鹋习性、端着老式步枪、极富耐心的本地猎人,效率比机枪高得多。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赏金猎人系统性地捕杀了成千上万只鸸鹋。这远比那场大张旗鼓的“战争”要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