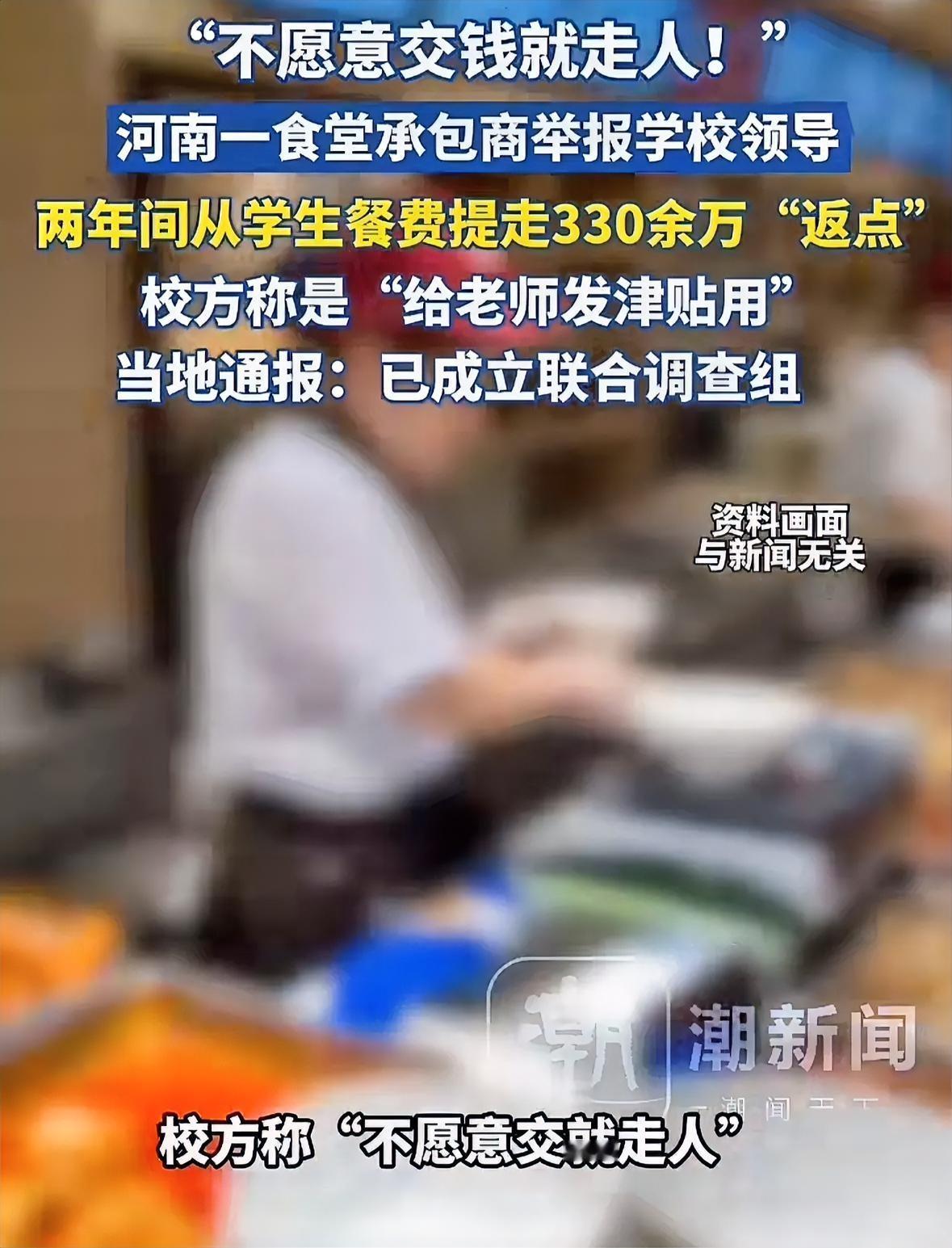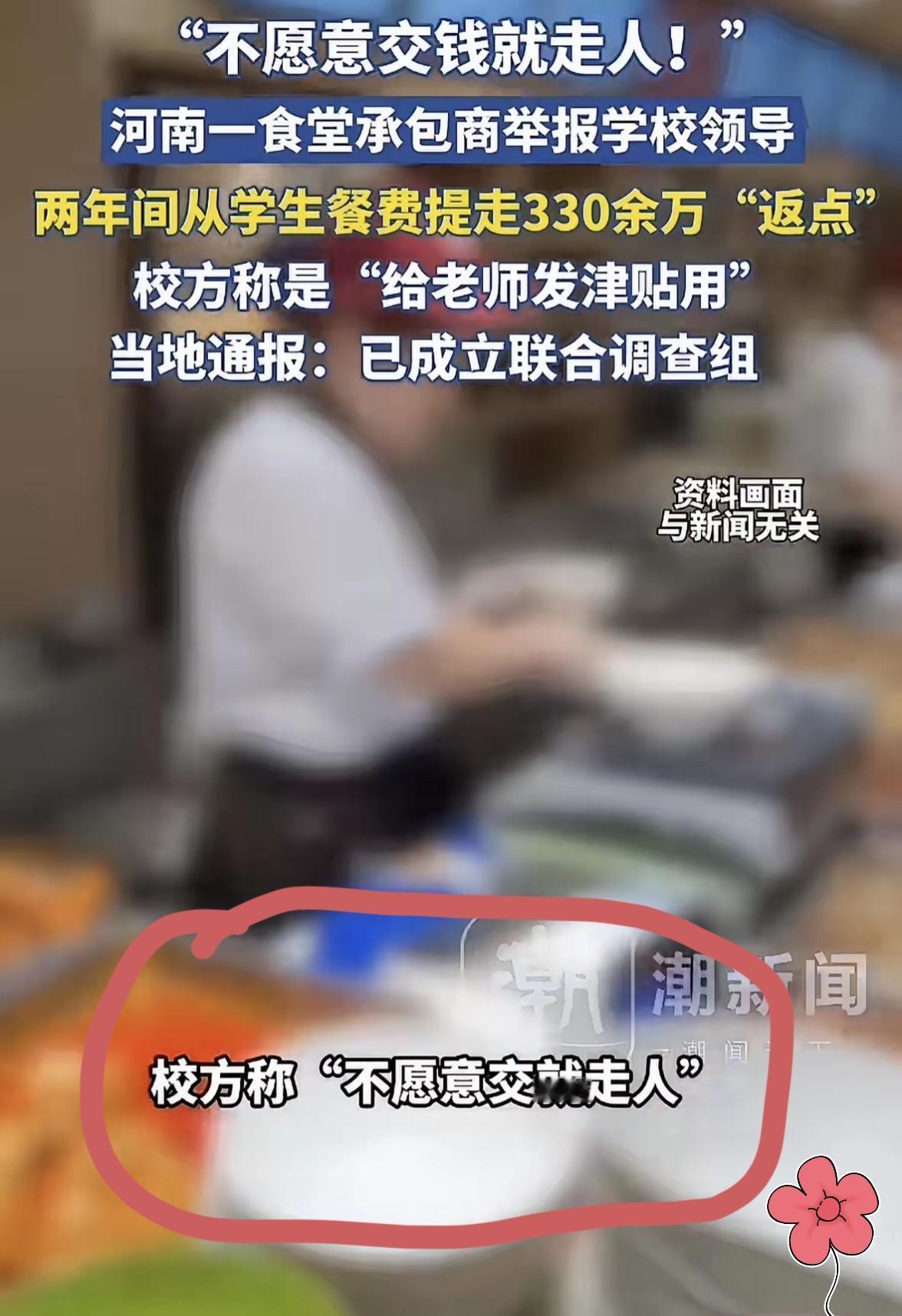四年了,终于在同学聚会上,碰到了当年借走我 3000 元不还的女生。包厢里闹哄哄的,班长正举着杯子挨桌敬酒,我刚跟当年同桌碰了杯,转身想拿饮料,就瞥见了角落里的她。穿了件浅灰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低马尾, 毕业四年,同学聚会的请帖在手机里躺了三天,最后还是来了——总觉得有些事没翻篇,比如当年那个借走我三千块的女生。 包厢里冷气开得足,混着火锅的牛油香和果盘的甜气,闹哄哄的声浪裹着班长的敬酒词撞过来,我刚跟同桌碰完杯,转身去拿桌上的酸梅汤,眼角余光就扫到了角落。 她就缩在最里面的卡座,浅灰连衣裙的袖口沾了点果盘里的西瓜汁,右手捏着杯子,指节泛白,低马尾垂在肩上,发梢有点毛躁——还是当年那副紧张时会攥紧杯子的样子。 我端着杯子的手顿了顿,她好像察觉到了,猛地抬头,眼神撞过来又飞快垂下,耳根慢慢红了。 这时候副班长喊我过去跟老班喝酒,我应着,却忍不住回头看她,她正低头用吸管戳杯子里的冰块,一下,又一下,像在数着什么。 酒过三巡,包厢里更吵了,我去洗手间回来,刚拐过走廊拐角,就看见她站在消防通道门口,背对着我,肩膀轻轻抖。 听见脚步声,她转过身,手里捏着个旧钱包,拉链磨得发白,“那个……”她声音发紧,“当年借你的钱,我一直想还,可毕业前我妈突然住院,家里凑医药费,我打工的工资全填进去了,后来换了手机号,就……” 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被走廊的风声吞了,她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我找过你QQ,你早就不用了,微信也换了头像,我……” 原来我记了四年的“赖账”,在她那里是四年的“没机会解释”——我们都困在自己的视角里,把对方想成了故事里的反面角色,却忘了当年她也是那个会帮我抄笔记、下雨时把伞往我这边歪的女生啊。 那三千块钱像根刺,扎在我心里四年,让我不敢轻易相信“失联的解释”;可对她来说,那三千块和没说出口的道歉,或许比刺更重——毕竟,谁愿意欠着别人的情,连同学聚会都要缩在角落呢? 你说,人是不是总这样?对没解释的事,宁愿往最坏的地方想,也不肯留一点“或许她有苦衷”的余地? 她从钱包里数出三千块,递过来时手还在抖,我没接,笑着拍了拍她胳膊,“早忘了,再说当年你帮我补数学笔记,值不止三千。” 她愣了愣,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浅灰连衣裙的袖口上,晕开一小片湿痕,跟刚才沾的西瓜汁混在一起,倒像朵不太规则的花。 散场时她走在我后面,低马尾随着脚步轻轻晃,路过火锅店门口的路灯,发梢的毛躁被灯光照得像撒了层碎金——原来有些重逢,不是为了讨债,是为了把当年没说完的“再见”,换成一句“没事了”。 现在想想,如果那天我没转身去拿饮料,如果她没缩在角落,如果我们都再勇敢一点,是不是四年前的夏天,就不会留下这个小小的疙瘩? 其实啊,遇到解不开的结,别急着给人贴标签,等一等,或许时间会把答案送到眼前——就像这杯没喝完的酸梅汤,放久了才发现,底下沉的不是杂质,是没化开的糖。
四年了,终于在同学聚会上,碰到了当年借走我3000元不还的女生。包厢里闹哄哄
小杰水滴
2025-12-28 18:28:09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