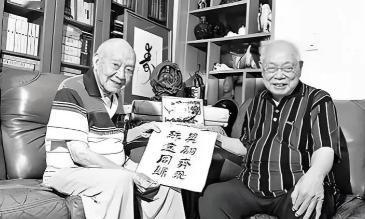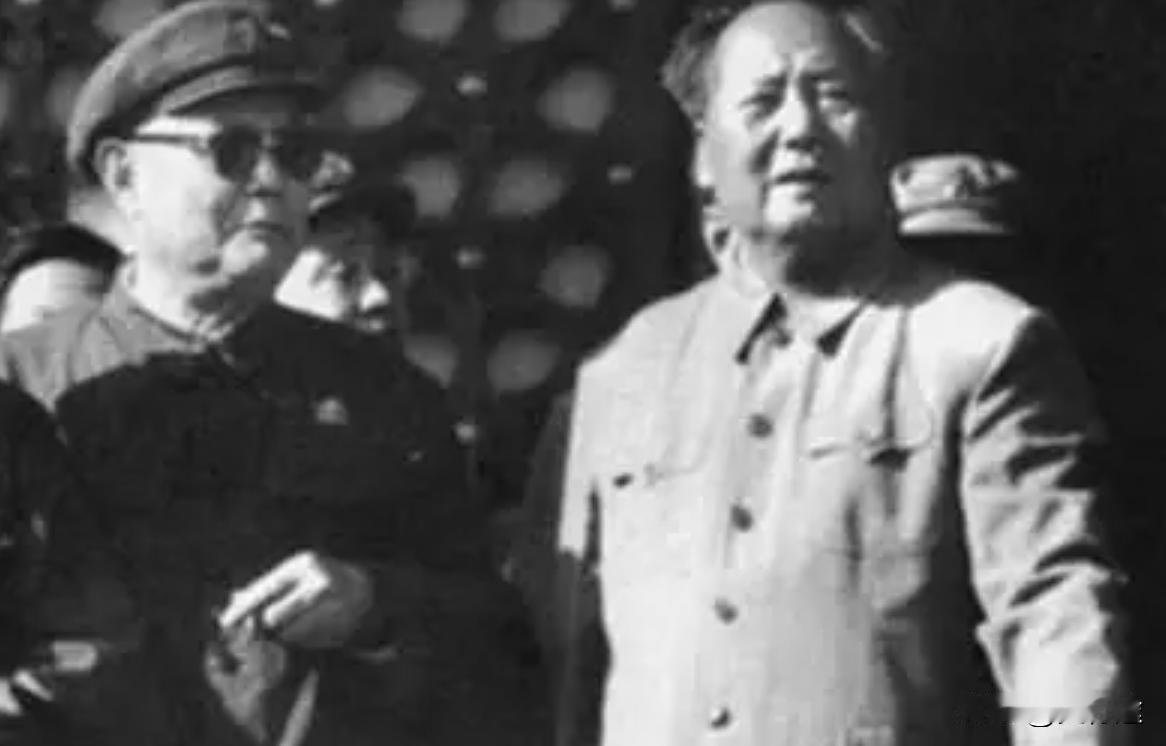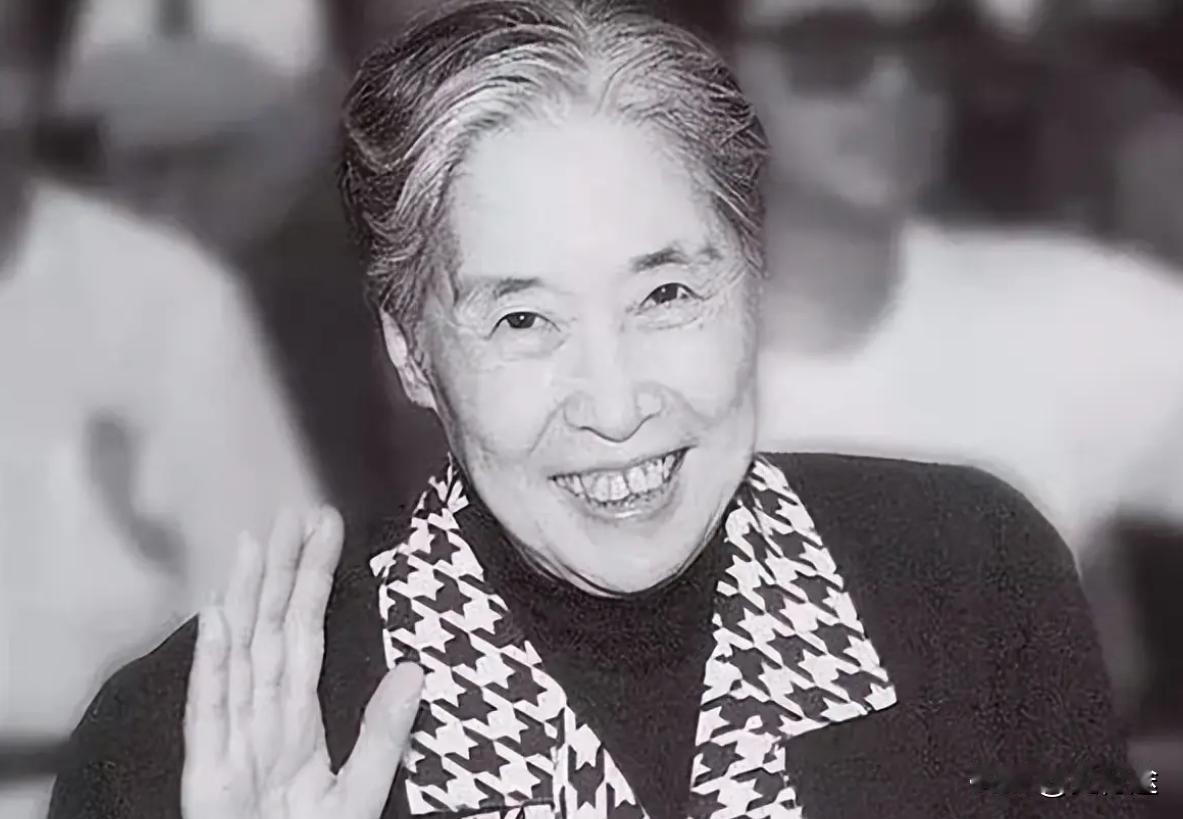1969年,知青张梅香被公社副主任黄书良叫到办公室。从身后抱住了张梅香,嘴里念叨着:“可想死我了。”作势就要亲下去。张梅香奋力挣扎无果,就在她绝望之际,没想到一个动作竟救了她。 在那个年代,很多城市青年响应号召去了农村,张梅香就是其中一个。她从北京来到陕北的郭家塬村,本来以为能适应新生活,谁知道刚到就碰上各种难处。身体不适应高原气候,吃的东西也跟城里大不一样,粗粮咽下去都费劲。村支书郭修成安排她住自家窑洞,这让她多少有点依靠。郭明亮是支书的儿子,人不爱多说话,但干活特别卖力。他帮张梅香挑水、教她怎么割麦,这些小事让她慢慢站稳脚跟。公社副主任黄书良管着村里的事务,对张梅香留意已久,但表面上没露声色。知青下乡本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动员了上千万年轻人,张梅香的经历也算典型。她初来乍到时,农活上手慢,常常被晒得皮肤发红,但她咬牙坚持下来。 知青生活本来就苦,张梅香还得面对额外麻烦。黄书良找借口把她叫到办公室,本意不轨。她反抗无效,但关键时刻一个举动让她逃脱。事后黄书良没罢休,利用职位给她派重活,扣工分,挡住回城路子。这种情况在当时知青中不算少见,很多女知青遇到类似刁难。郭明亮在这时候站出来,帮她分担负担,两人就这样互相扶持。陕北的黄土高原上,知青们每天面对的都是体力劳动,张梅香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黄书良的举动暴露了他的品行,但村里人也没办法多管。郭明亮帮张梅香的那些事,让她觉得农村不全都是苦。 张梅香和郭明亮的相处越来越密切,两人通过劳动建立起信任。郭明亮帮她生火、捆麦捆,这些日常帮忙拉近了距离。知青下乡政策下,很多城市青年和当地农民有了交集,张梅香的例子就是这样。她从不熟悉农活到能独立干活,花了不少时间。黄书良的针对让她工作量加大,但她没退缩。郭明亮总在暗中支持,比如替她完成部分任务。陕北的村子条件简陋,窑洞里住着几个人,生活节奏慢而单调。张梅香适应过程也反映了当时知青的普遍状态,国家动员他们去农村锻炼,但实际遇到的难题不少。 事件发生后,张梅香的生活节奏没变,但压力增加了。黄书良扣她的工分,理由总是劳动不积极,这让她积分少拿不少。知青的工分直接影响口粮,她日子过得更紧。郭明亮咬牙帮她扛下重担,两人就这样熬过几年。陕北的农村劳动强度大,张梅香从城里姑娘变成能干农活的人。黄书良的举动没得到追究,但他继续使绊子。郭明亮的支持成了张梅香的支柱,两人感情在这些年里逐步加深。知青政策持续了多年,张梅香的坚持也算常见。 八年时间过去,张梅香和郭明亮的关系几乎定下来。1977年高考恢复,这对知青来说是个转机。张梅香抓住机会复习,最终考上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手时,她决定回城,但没忘郭明亮。离别时把手表给他,当作承诺。知青回城是当时的大趋势,很多人在高考后离开农村。张梅香的决定也符合政策变化。郭明亮留在村里,面对村人的议论越来越多。陕北的乡村生活没变,但他开始减少回信。 在大学里,张梅香定期写信给郭明亮,分享学习情况。郭明亮起初还回复,但压力渐大。村里长辈介绍他认识寡妇李嫂,她带两个孩子,生活现实。郭明亮寄出分手信,以为这样对双方好。张梅香收到信后,立刻停学业赶回陕北。她找到郭明亮,坚持带他去北京。两人办手续后一同返回,并在那里成婚。知青和农民的结合在当时不算多见,但张梅香的举动体现了她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