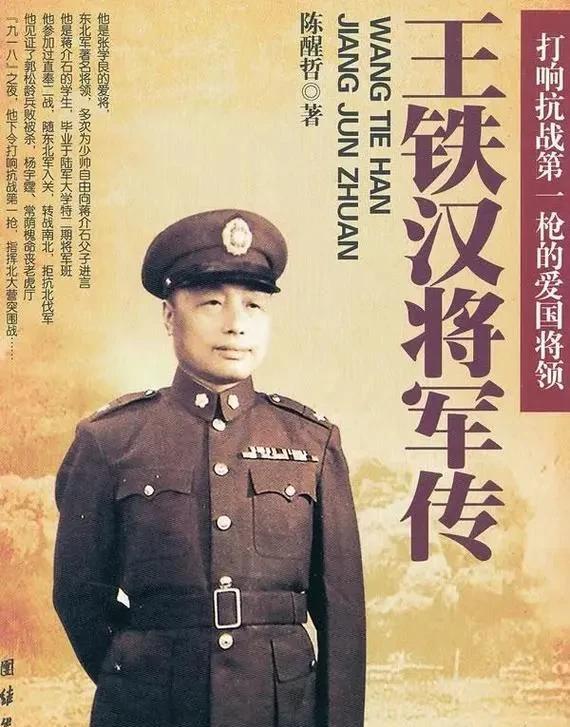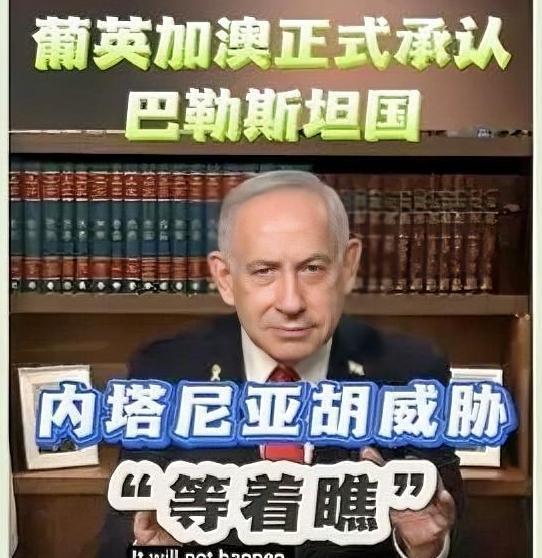1992年,84岁军统特务头子毛森,临终前,抓住儿子的手,说:“我只有一个憋了40年的愿望,想回家乡看一眼!” 这句话让儿子心里一震,他愣了很久,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父亲的身份他太清楚了,血债累累,名声狼藉,如今却在生命尽头吐出这样的心愿,儿子既有怜悯,也有抗拒,他明白这是父亲最后的牵挂。 曾经,毛森主持的审讯留下无数血迹,他签下的处决名单让无数家庭破碎,他的冷酷与铁腕使他成为军统体系里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1949年局势逆转,解放军步步逼近,毛森仓皇逃离上海,先到厦门,再转赴台湾。起初他想依靠旧日的功勋重新站稳脚跟,可随着情报系统的清洗和权力更迭,他逐渐被边缘化。 走私黄金、虚报军情等旧账被揭出,他彻底失去信任,最终,他选择借机会离开台湾,漂泊到美国,从此成为海外的流亡者。 在旧金山,他会翻阅旧报纸寻找一切关于中国的消息,他明白自己回不去了,可心思却始终停留在故土,他的生活简单到枯燥,每天在小屋里写信、算账、寄钱。 他把退休金的一部分,按月寄回浙江老家,他用化名写信,说愿意捐助教育,对于外人,他没有提起过内心的愧疚,但在信里,他反复提到“希望孩子们能读书”。 这是他赎罪的方式,也是他在流亡生活里唯一能抓住的价值,虽然外表冷漠,毛森对家乡的思念却随着岁月愈发浓烈。 他常常对儿子说起廿八都镇,说起桥头的水声,说起孩童时母亲的呼唤,这些画面在他脑中反复浮现。 他甚至收藏了一本《浙江通志》,反复翻看,指着地图上的江山位置,对儿子讲那里的山和水。 在美国的几十年,他见过各种华人社团,也被人冷眼看待,他的过去让人不齿,可他自己更清楚自己的一生不可能抹去那些血债,唯有家乡始终牵着他。 1992年,他的病情恶化,医生断言时日无多,就在此时,浙江方面得知他多年寄款资助教育,决定允许他回乡探望,这是他盼望已久的机会。 当飞机降落杭州,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到接机处,迎面是一条横幅:“浙江省人民政府欢迎您。”他眼泪夺眶而出,多年漂泊,他第一次以一个游子的身份回到故土。 在江山县廿八都镇,乡亲们围拢过来,毛森坚持用拐杖支撑,颤抖着走向祖屋,他在众人注视下写下“谢谢亲爱的乡亲们”,这一刻,他似乎把所有的力量都倾注在笔尖。 随后,他参观了新落成的小学,教学楼门楣上写着“思源”二字,这是他捐助的心愿,他久久抚摸,久久凝视,仿佛看见了那些曾经被自己伤害的学生,那些失去生命的年轻人。 他说,这是他的赎罪,也是留给家乡孩子的补偿,毛森的归乡引起极大轰动,有人感叹他在晚年愿意资助教育,认为这是浪子回头;也有人愤怒,指责他当年的血债再多善举也不能抵消。 乡亲们的态度复杂,有人愿意接纳他留下的钱,有人拒绝原谅他留下的罪,学校落成的消息登上当地报纸,人们议论纷纷。 无论褒贬,他的名字再次被记起,这一次不再只是恐惧的代名词,也与“教育”“赎罪”挂上了联系,归乡几日后,他返回美国。 三个月后,在旧金山的家中,他安静离世,整理遗物时,儿子发现一张泛黄的字条,上面写着:“把我的骨灰撒在须江公园的桂花树下,从那里能看到家乡的山。” 最终,他的骨灰被送回祖地,安放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毛森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争议,他曾是冷酷无情的特务头子,亲手制造过无数惨案。 他也在晚年寄钱建校,试图为家乡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他的人生是沉重的,他的归乡是迟到的,他的赎罪也是有限的。 对世人而言,他的经历提醒人们:再高的权力,也敌不过时间与良心的拷问;再深的罪行,也会在生命尽头被记起,他的一生既是历史的黑暗注脚,也是人性复杂的写照。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主要信源:毛森(1908~1992).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