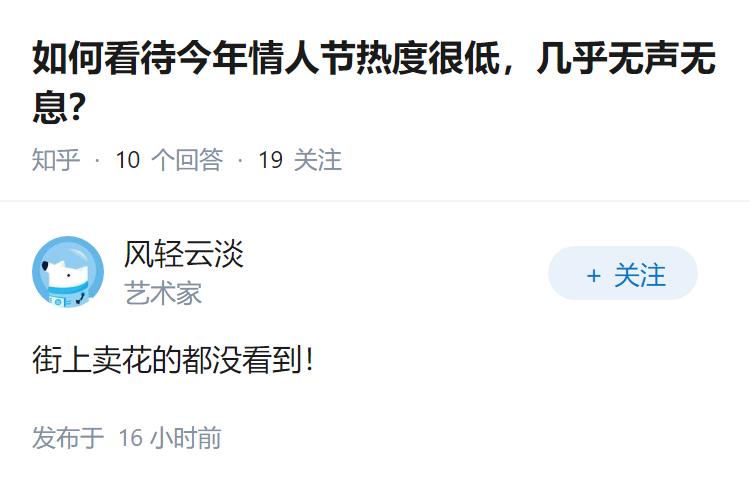钱学森唯一儿子钱永刚的峥嵘岁月 二〇〇八年那会儿,钱永健拿了诺贝尔化学奖,电视一播,亲友的电话就往钱家那边扎。 有人感叹:要是当年老钱一家不回国,永刚现在说不定也不是在机房里写程序。 时间往回拧,要拧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那时候的钱学森,在美国前途亮堂,科研平台顶尖,家里一儿一女,大儿子钱永刚,一九四八年出生,两年后妹妹钱永真来了,小家看着体面安稳。 心却不在加州,在万里之外的新中国。 念头一拧,麻烦跟着来。美国当局死活不让走,关起来反复审,人被折腾得一个月瘦了三十来斤。多年攒下的书和笔记,差不多八百公斤,被海关一扣了事。另一边,新中国咬牙,把在朝鲜战场俘获的十一名美军飞行员放回去,换他回家。 等到全家踏上回国的船,甲板上的风吹得人睁不开眼。钱学森夫妻俩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七岁的钱永刚却一脸懵,只知道要和幼儿园的老师同学说再见。 船一靠岸,他才知道什么叫换了天地。 物资紧巴巴,牛奶面包成了稀罕物,嘴里那点“小资口味”得收起来。 语言也是道坎,从小蹦出来的是英文,突然要换成顺溜的中文,张嘴前心里得先过一遍。家里气氛更紧,父亲一头扎进国防和导弹工程,见孩子的时间屈指可数。 适应这件事,只能自己扛。课上听不懂,就课后多抄几遍;吃不惯,就学着和同学一起在食堂门口排队等一锅大米饭。久而久之,成绩爬上来了,老师点名夸,同学喊他“学霸”。 书包越来越沉,心里的主意倒是越来越稳:以后要学理工,在图纸和数据堆里给国家干点实事。 形势一变,路说断就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角一响,高考戛然而止。 原本准备直奔大学的学生,被迫把书往抽屉里一塞走人。对钱永刚来说,这一下不只是“缓一缓”,是彻底按下暂停键。 看着儿子心里打鼓,钱学森说得很直白:报效祖国,不一定非要戴着“科学家”的帽子,穿上军装照样顶用。路就这么指出来了。钱永刚去部队报了名,一待就是九年。 九年里,他戴着军帽,干的是技术活,却从没想过找父亲开口走捷径。反倒因为“钱学森儿子”这五个字,有些提拔机会被格外小心地绕开。后来调去科技部门,工作好了一点,他也没多讲,只当是该吃的苦、该走的弯。 一九七七年,消息传到连队,说国家恢复高考。 他向领导打报告时,只说想试一试。对方干脆,考上就放你去念,考不上就接着在部队干活。 话定了,他把压在箱底多年的课本翻出来,晚上对着昏黄的灯一点点啃题。十年没系统读书,底子还在,再加上平时搞技术,脑子没完全荒。 考试成绩出来,他以全系第三名考进国防科技大学,成了校园里年纪偏大的那一拨新生。这一年,他三十岁。 三十岁在很多人眼里,是往上爬的年纪,他却背着书包坐进教室,和一群小他不少的同学一起上高数、学程序。心里明白,自己已经绕了大圈,不敢有半点松劲。 四年熬下来,所有科目都是优,拿到计算机专业学士学位时,那口气总算慢慢吐出去。 学位在手,脚步没停。看着国外计算机技术一日千里,他清楚,只在国内闷头钻是不够的。一九八六年,又做了个挺“折腾”的决定:三十八岁,自费去加州理工学院读硕士。 这所学校,对钱家别有意味。 差不多年纪的时候,钱学森已经在那儿当教授,管着喷气推进中心。 履历一摆,压力不压人也难。钱永刚却不愿让自己陷在比较里,把自己当普通留学生看待,上课、做实验、改项目,一样样往前推。 两年过去,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拿到手,老师们看在眼里,几家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接连抛来橄榄枝。 要不要留下,多数人会算一算账。他心里那杆秤早就立着,没打多少弯。 出来是来学东西的,东西学到手,路得往回走。 回到国内,他钻进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里,做过不少重点项目。很多成果悄悄落地,改变着行业的底层运行。高校来请人,请他去讲课、带学生,一会儿在机房对着代码,一会儿在讲台上拆解系统。 把他重新拉回公众视野的,是那场诺贝尔奖。堂弟站在聚光灯下时,不少人替他算起“如果”的账:要是当年不回国,要是当年留在美国,是不是又一个大奖得主。有人干脆当面问出口。 钱永刚听完,只笑了一下,提起钱家的老话:利在一身不能谋,利在天下必谋之。对他来说,生活条件好不好,名头响不响亮,从来排不到最前面。更看重的,是一路走来,有没有对得起这句家训,对得起这片土地。 父亲那一代,把一生交给导弹和航天;儿子这一代,把青春和中年系在计算机和系统工程上。起步晚不晚、奖项多不多,在外人眼里是比较,在他们家,只是顺着那句话往下接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