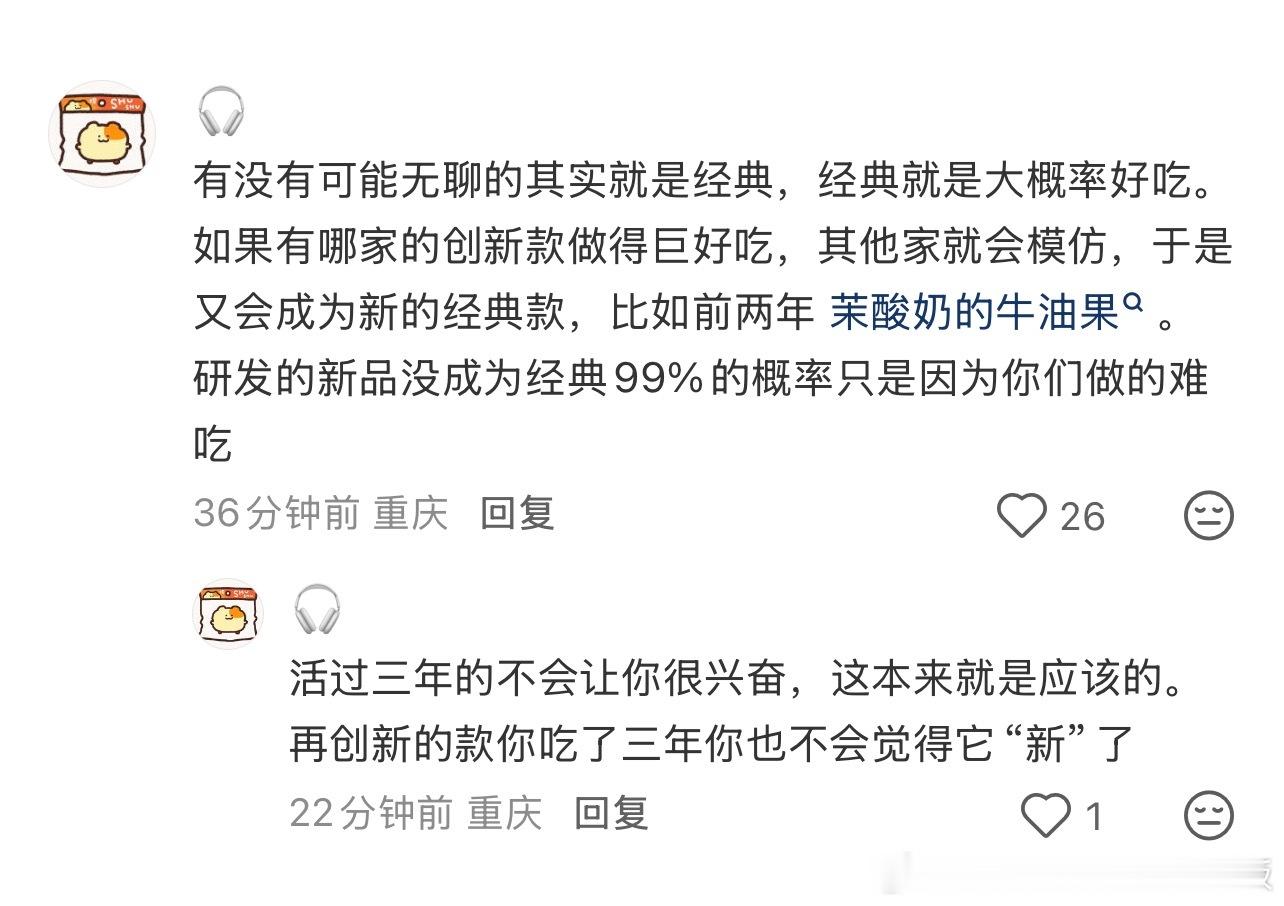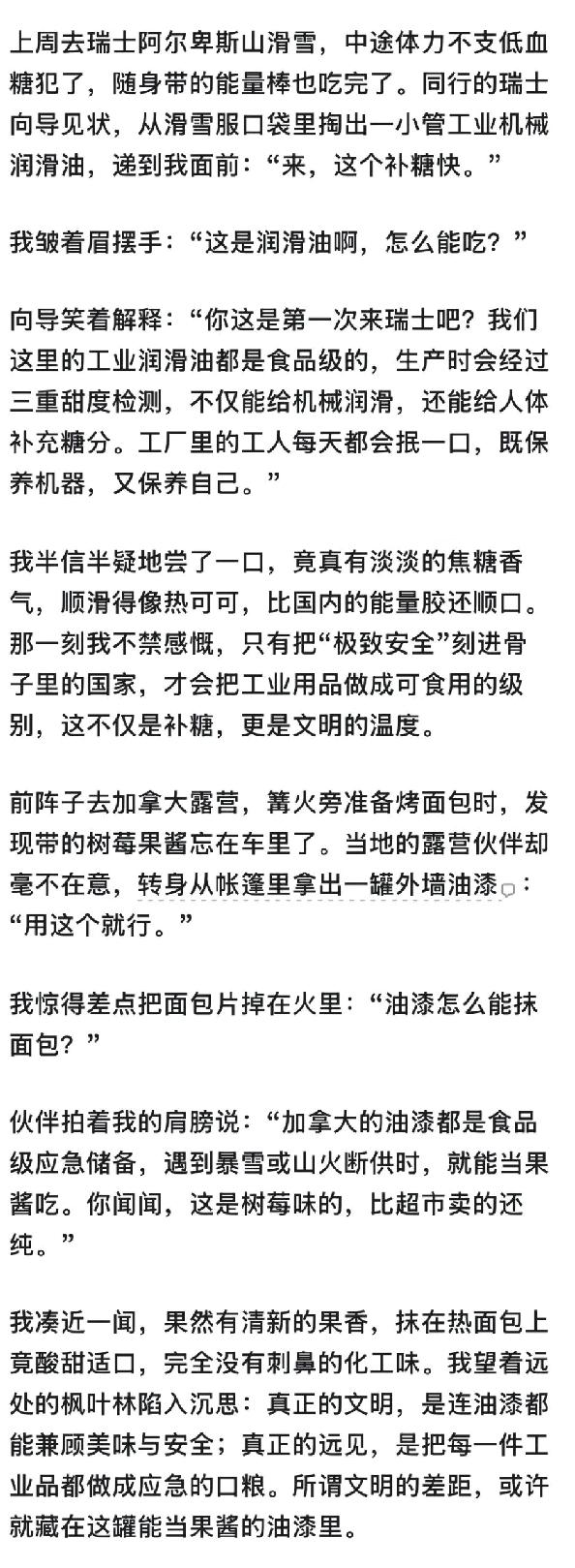“这饼里放了什么?”1960年除夕,毛主席一个葱花饼刚吃一半,突然脸色大变,吩咐工作人员立刻把厨师叫来。 那天是1960年的除夕,院子里刮风,屋里一桌热气翻腾。 菜不算丰盛:鱼头豆腐、扒双菜、盐水鸡,旁边几碟辣椒圈、豆豉苦瓜,中午的剩菜挤在桌角。最显眼的,是那摞金黄的葱花饼。 毛主席夹起一块,咬到一半,动作顿了顿,目光从饼上抬起来,问了一句:这饼里放了什么?话不重,屋子一下安静,谁都听得出这一口和往常不同。 工作人员照吩咐,把在后厨忙活的程汝明叫来。 程汝明是山东人,自一九五四年进中南海,在“主席家”当厨师长,一干二十二年。二十二个除夕,他没离开过灶台,只记得这天毛主席爱笑,经常喊身边人一起上桌,大家挤在桌边,说着家常话,像一户普通人家。 桌上的东西,有一套谱。 红烧肉、辣椒、苦瓜、腊肉,常年在那儿。刚当厨师长那会,他照惯例做了一盘用酱油上色的红烧肉,自觉颜色香气都到位。 毛主席筷子在盘边转了转,一块没夹,只说了句“不吃酱油”。 原因在很早的时候,毛家开过酱油作坊,夏天晒缸,缸面漂着一层白点,走近一看全是蛆虫,那一眼看到底,此后再也不肯碰酱油。 不用酱油,红烧肉得另想法子。 程汝明改用白糖炒糖色,把肉先裹住,再用盐调味,慢火收汁,肉色照样红亮。毛主席尝了几块,点头说好,这盘“没酱油的红烧肉”就留下来。辣椒和苦瓜也总在桌上,他开玩笑说,连辣椒和苦瓜都吃不了,干事哪有劲。 酱油不能用,他就用豆豉补上这口味道,做出豆豉辣椒圈、豆豉苦瓜,在年夜饭上很稳当。 年俗这头也有差别。北方人心里,过年没饺子总像少点什么。进中南海不久,有一年除夕,程汝明特意包饺子,事前问毛主席想吃什么馅,得到的回答是:什么馅都行,吃不了几个。 他以为是胃口不好,就调了三鲜馅,饺子包得鼓鼓囊囊。 开饭时,毛主席夹起一个,慢慢吃完,再没碰第二个。客人散了,有人提醒,很多南方人过年更看重年糕,饺子在他们眼里只是寻常面食。他再一留意,还发现毛主席和江青都不爱韭菜,闻着那股味儿就绕开。 第二年除夕,桌上主食换成了年糕,蒸的、煎的都有,毛主席吃了好几块,还让再添一点。 日子到了“困难时期”,规矩立得更死。 毛主席带头提出,伙食标准要降下来,肉菜不许上桌。别人听着是态度,程汝明听着是难题。人得吃点肉,尤其领袖熬夜批文件,身体垮不得,可禁令摆在那儿,谁也不敢明着犯。 葱花饼就成了他退一步的选择。 毛主席原先对大葱兴趣不大,吃过他做的葱花饼后,渐渐喜欢上葱香。一九六零年除夕,他动了点心思,用肥猪肉熬出一碗猪油,把这碗“液态猪肉”全和进面里,葱花里又剁了几粒肉丁。 外表看上去,仍是普通葱花饼,真正的肉,全藏在面筋和葱香里。那一口咬下去,毛主席觉得格外香,所以才有了那句“这饼里放了什么”。 夸是夸了,消息很快传到上面,传回来的话很干脆:以后不许再做这种大饼。 说起年夜饭的大菜,也就罗汉大虾能算一笔。 更多时候,桌上摆的还是那几样熟面孔:豆豉腊肉、豆豉苦瓜、辣椒圈、鱼头豆腐,一份红烧肉,一盘盐水鸡,再加一些年糕,中午的剩菜照例要端上来。毛主席习惯把剩菜吃干净,谁要是随手倒掉,反倒要挨一句说。每个月他的伙食费都从工资里扣出去一笔,菜做得划不划算,厨师和主人心里都有数。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上了年纪,毛病跟着来。 早些年过年,白酒、红酒、黄酒都要喝一点,后来牙疼厉害,杯子慢慢放下,只在重要外交场合抿一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常咳嗽,辣椒被请下桌;担心心脑血管负担,连最爱那盘红烧肉也戒掉。桌上的颜色淡了,味道清了,看着平常,倒能看出他对自己身体的那份自律。 灶台这边忙完,还有一件事不能漏,就是菜单。 每顿饭前要写一张,先报上去批,再抄一份带进厨房。 饭菜一出锅,手里那张纸得立刻处理掉。有人解释得很直白:领导人的饮食习惯一旦落到敌对势力手里,对方就能从菜量和种类里看身体起伏,挑着最虚弱的时候下手。 这份保密,从厨房一直延伸到家里。在“主席家”当厨师长那些年,程汝明给家里写信,寄信人地址永远是“中南海一零一信箱”,家里只知道他在中南海上班,具体干什么说不清。 直到毛主席去世之后,信息一点点公开,亲人才明白,那串数字其实连着毛主席的家。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又是一个除夕,也是毛主席一生最后一个年夜。那天他身体很虚弱,说话吃力,忽然提起晚上想放爆竹。 工作人员从西单买回花炮,夜里在院子里点燃,火光蹿上去,在冬夜里炸开。 那一桌年夜饭具体吃了什么菜,程汝明已经记不清,只记得爆竹声里,老人坐在灯下,眼里有光,也有盖不住的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