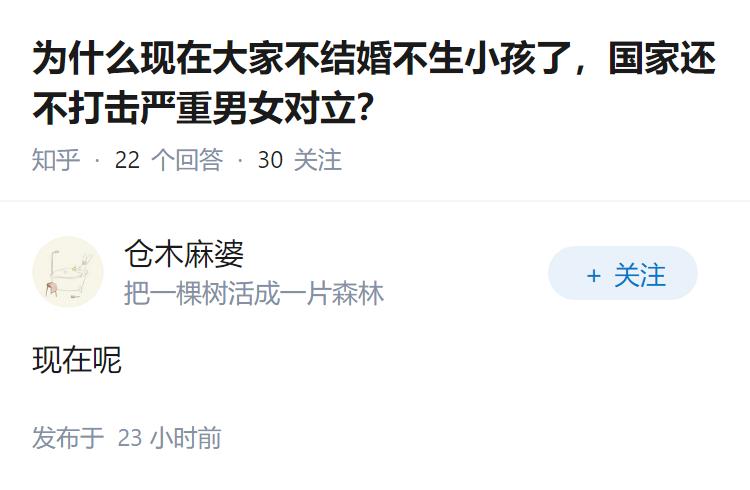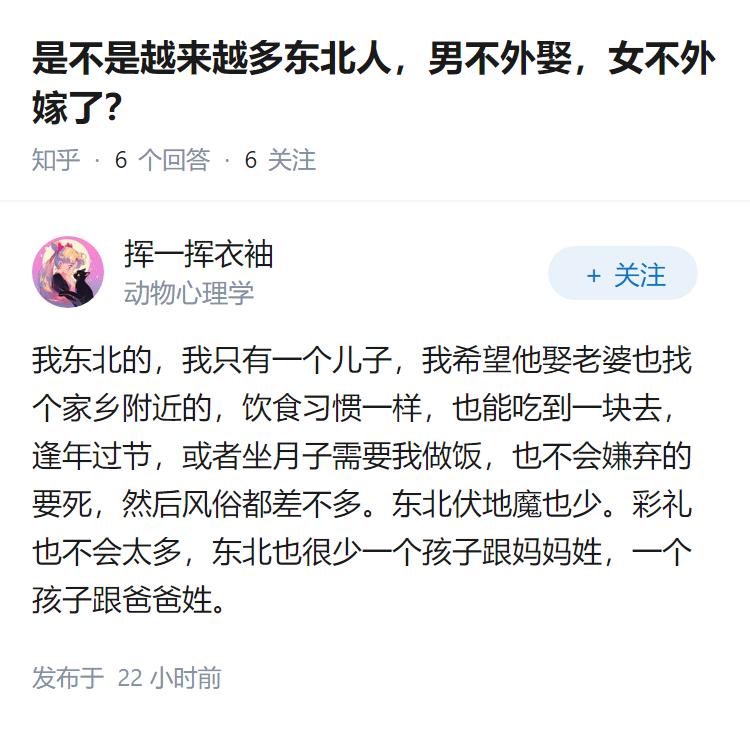陈二虎听完父亲哭诉,脸上看不出波澜。 只说先让他住着。不急。 他从行李里取出一把带鞘腰刀。 暗色鲨鱼皮鞘,有些地方磨得发亮。 刀随意斜倚在自家老墙根下,正对着西院张旺霸家新开的小窗。 刀柄朝外。 张旺霸的儿子扒着窗缝看。 刀柄缠布上,有洗不干净的黑红点子。 张旺霸认出来了。 去年府城来客佩过类似的刀,师爷当时腿肚子都在抖。 他托人去打听。 回来的人说,陈二虎在锦衣亲军里待过,是指挥使手下办过差的。 第五天清晨。 张旺霸领着全家跪在陈府门前。 磕头磕到额上见了血痕。 白花花的银子捧在手里,求人收下。 陈二虎走出来。 只取了约莫三分之一,说这是修墙和抵租的钱。 剩下的,命他三日内拆了墙恢复原样,再退还给这些年盘剥的乡邻。 那把绣春刀还靠在墙根。 没出鞘,也没挪过地方。 真正的威慑从来不是挥出去的刀刃。 是让对方自己看见刀柄上的旧血迹,然后整夜整夜地算——这一刀如果落下来,该是什么价码。 你总想靠解释和对抗来解决问题。 却忘了让人膝盖发软的,从来不是你的拳头,而是他关上门后,自己脑子里那场停不下来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