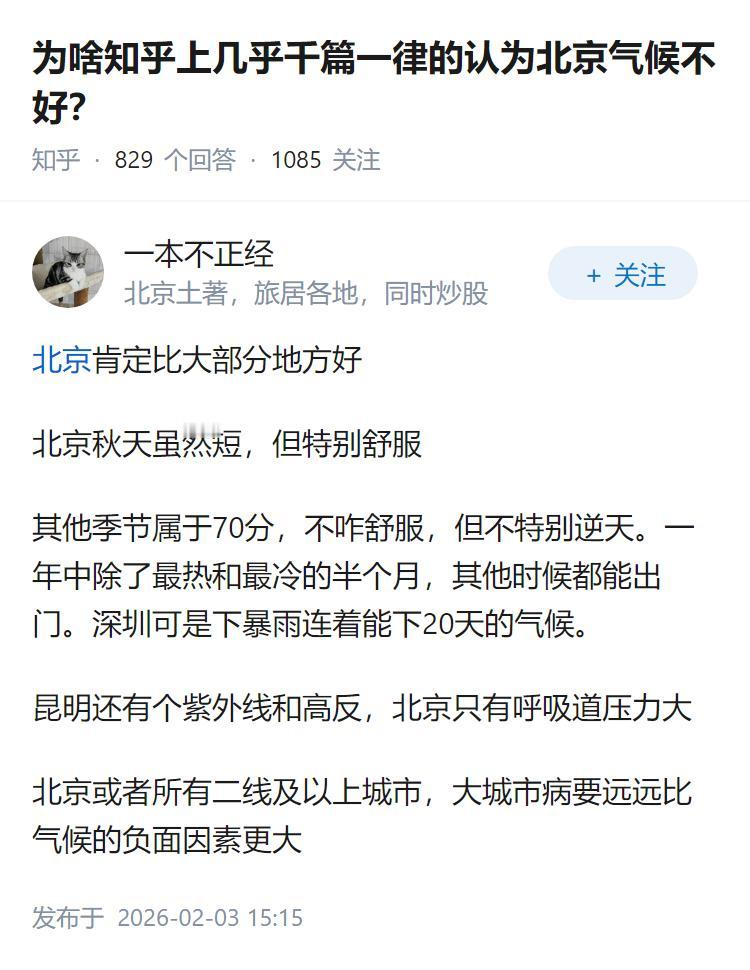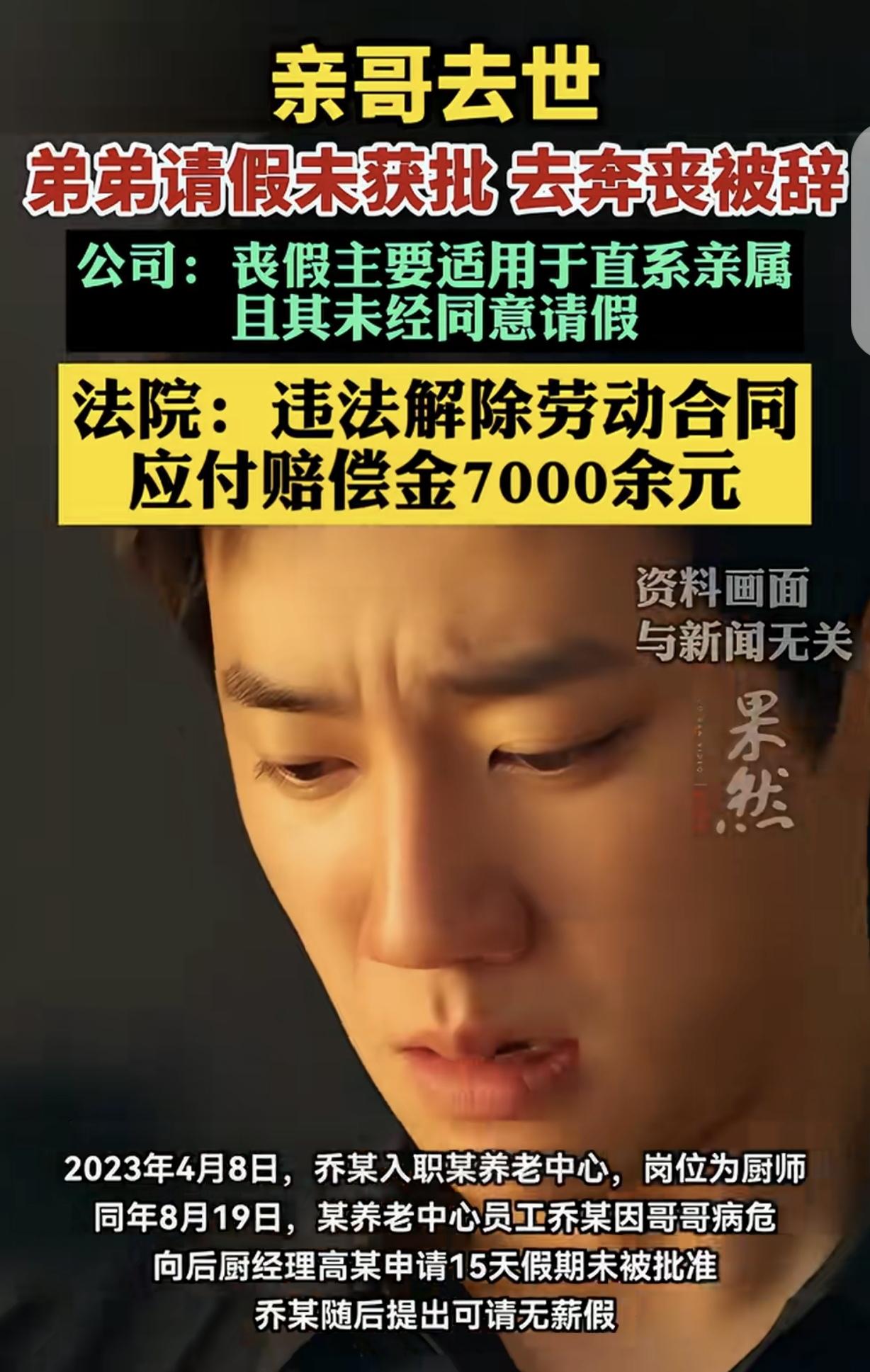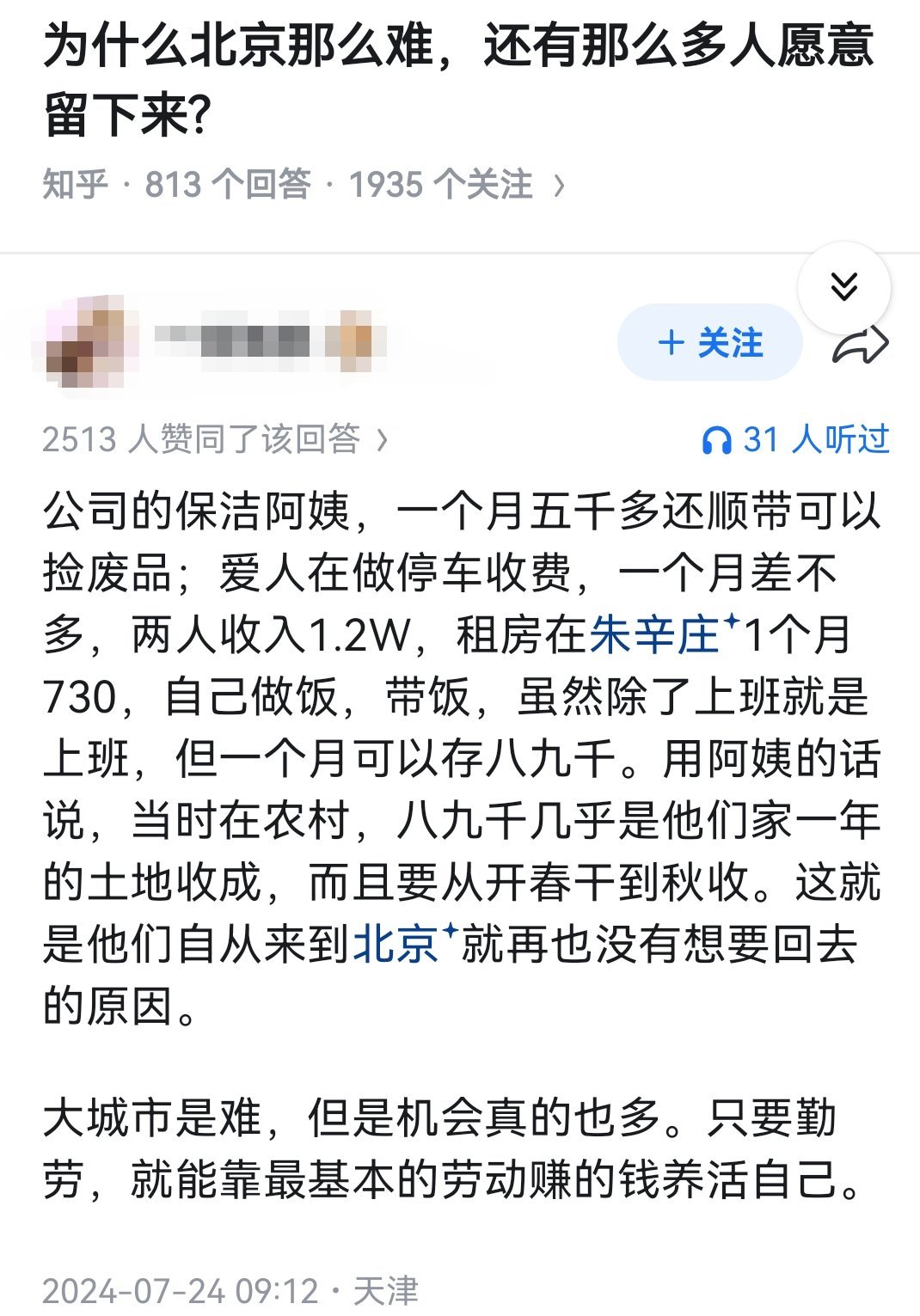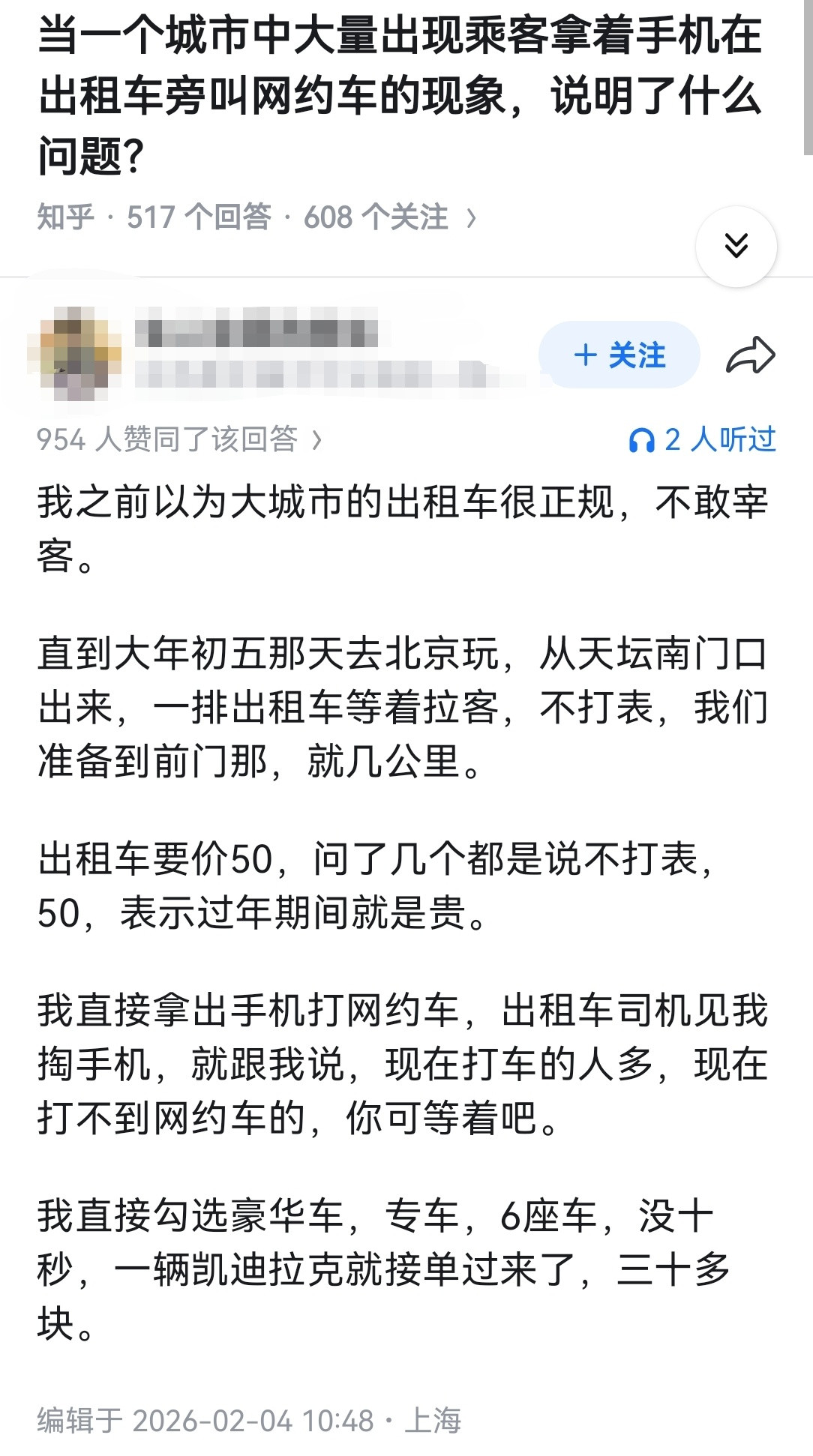1992年,19岁的段奕宏孤身去北京考试。在火车上时,人贩子盯上他,趁他下车前抓住他不让走。 1992年的北京火车站,空气里大概混杂着煤烟、汗酸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躁动,在那个人潮汹涌的站台上,一只成年男性的手,像铁钳一样死死扣住了一个少年的手腕,少年叫段龙,也就是后来的段奕宏。 那年他十九岁,口袋里装着在伊犁果脯厂做苦工换来的钞票,脑子里全是关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幻梦,对方不是什么星探,是个人贩子,这大概是段奕宏人生中最接近深渊的一秒钟,那个自称“商人”的中年男人,撕下了在火车上温情脉脉的面具,不再提什么“采购商品”。 而是要把这只从新疆飞来的雏鹰,生拉硬拽进某个不知名的黑工厂,如果不是那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喊声一声炸雷般的“段龙”吓得歹徒松了手,今天的华语影坛恐怕会少一位影帝,而当年的社会版面,或许只是多了一行关于失踪人口的冰冷铅字。 90年代初,那是个野蛮生长的年份,1993年的中俄列车大劫案就在转角,荣昌甚至爆出过团伙拐卖案,连那个叫彭洪菊的人贩头子最后都被同伙卖了,在那种治安真空地带,一个单身远行的西北少年,就是猎物。 段奕宏在火车上的嗅觉救了他,当那个男人过分热情地递来食物,絮絮叨叨地套近乎时,一种本能的寒意让段奕宏哪怕扛着行李也要换车厢,这种对危险的病态敏感,后来成了他表演里最迷人的特质。 你看他在《烈日灼心》或《暴雪将至》里的眼神,那种神经质的紧绷,或许早在那个惊魂未定的站台上就埋下了引信,逃过一劫的段奕宏,并没有迎来鲜花,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性暴击”。 从新疆伊犁到北京,三千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远没有阶层的鸿沟难跨越,为了攒路费,他在家乡的果脯厂当过工人,那是个什么地方,高温蒸汽熏着,每天像机器一样重复劳作,累得直不起腰。 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工人,父亲退休,母亲操持家务,他们眼里的好日子是“找个班上,娶个本地媳妇”去北京演戏,那是痴人说梦,但段奕宏就是这股犟脾气,母亲哭着给他收拾行李,他硬是头也不回地走了三次,前两次考试,中戏的大门对他紧闭。 理由残酷而直接:形象不够好,口音太重,这简直是对基因的羞辱,没人知道他在第二次落榜后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在当地找了个老话剧演员,死磕基本功,像个苦行僧一样练发音、练形体,等到第三次终于以高分撞开中戏大门时,他以为自己赢了。 结果,大学生活成了另一座炼狱,在90年代中期的中戏校园,段奕宏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周围是衣着光鲜的城市同学,嘴里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谈论着他听不懂的时尚,而他,穿着旧衣服,一张嘴就是一股“羊肉串味儿”。 “外星人”这是同学给他的绰号,这种由于地域和阶层带来的自卑,像一把钝刀子在割他的肉,他想过退学,想过逃回伊犁,但他最后选择了一种近乎自虐的报复方式:练。 既然别人看不起我的口音,我就对着墙练,对着镜子练,直到舌头麻木,既然别人嫌我土,我就把基本功练到谁都不敢忽视,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陶虹是唯一的光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年的陶虹是班长,是那种阳光得让人不敢直视的女孩。 而段奕宏,是躲在阴影里的自卑男,起初陶虹也笑过他的口音,但很快,这个聪明的姑娘看懂了段奕宏骨子里的那股劲儿,那是大二的除夕,别的同学都回家了,段奕宏为了省路费留在学校,陶虹知道了,二话不说把他拽回自己家吃年夜饭。 那顿饺子,段奕宏记了三十多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陶虹一家人的接纳,不仅填饱了他的胃,更缝合了他破碎的自尊,这种情谊甚至延续到了毕业后,陶虹成名早,每次聚餐都抢着买单,从不让窘迫的段奕宏难堪。 这种不对等的施予,如果没有极高的情商和善良,很容易变味,但陶虹把它处理成了最自然的战友情。信息来源:澎湃新闻;一言难尽段奕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