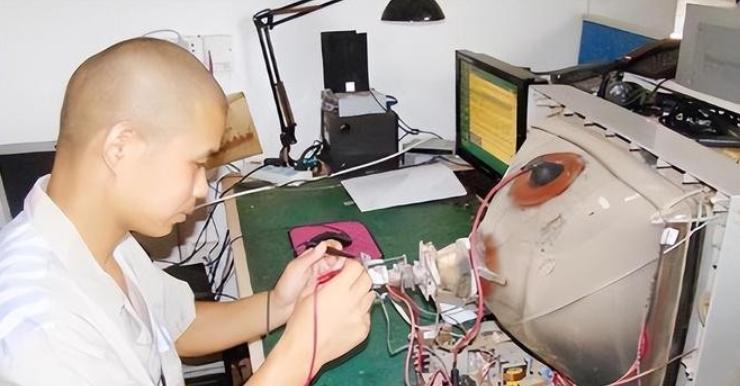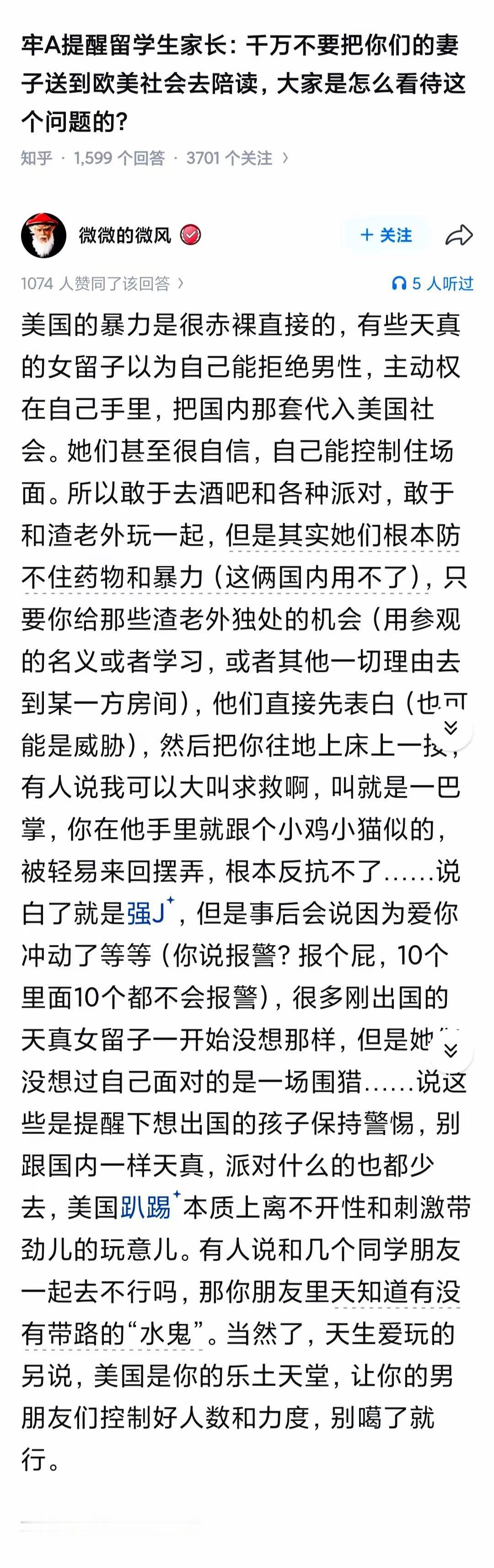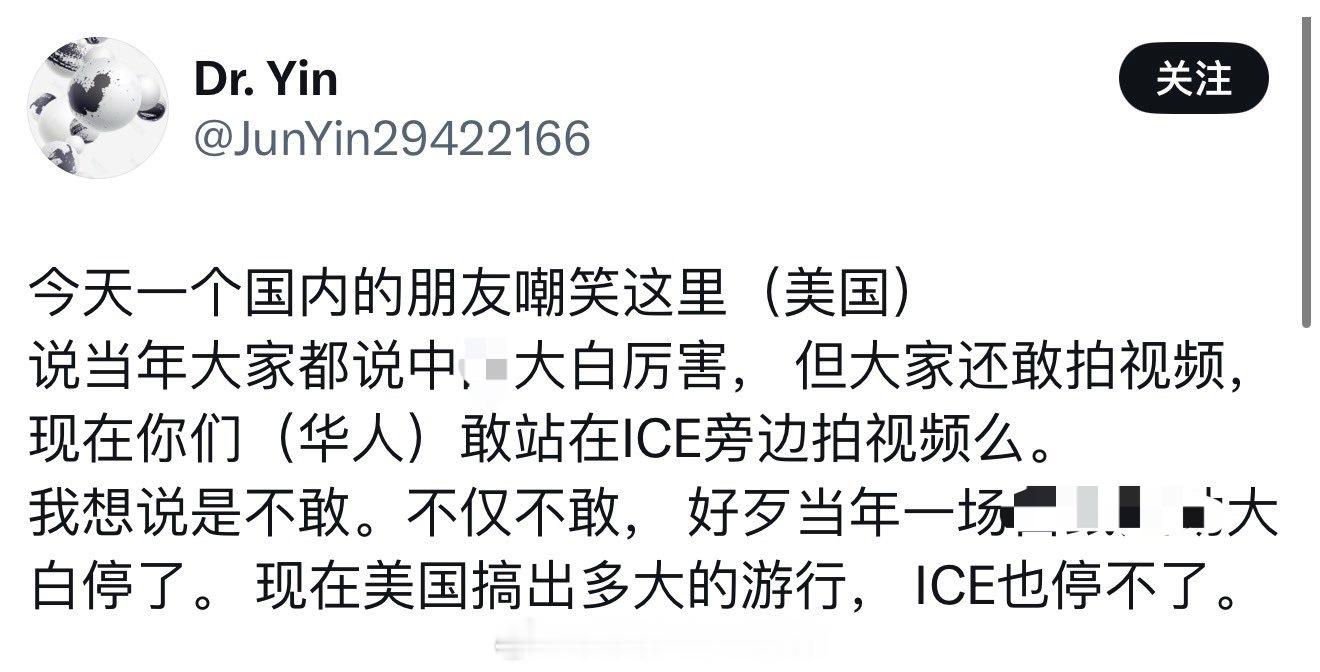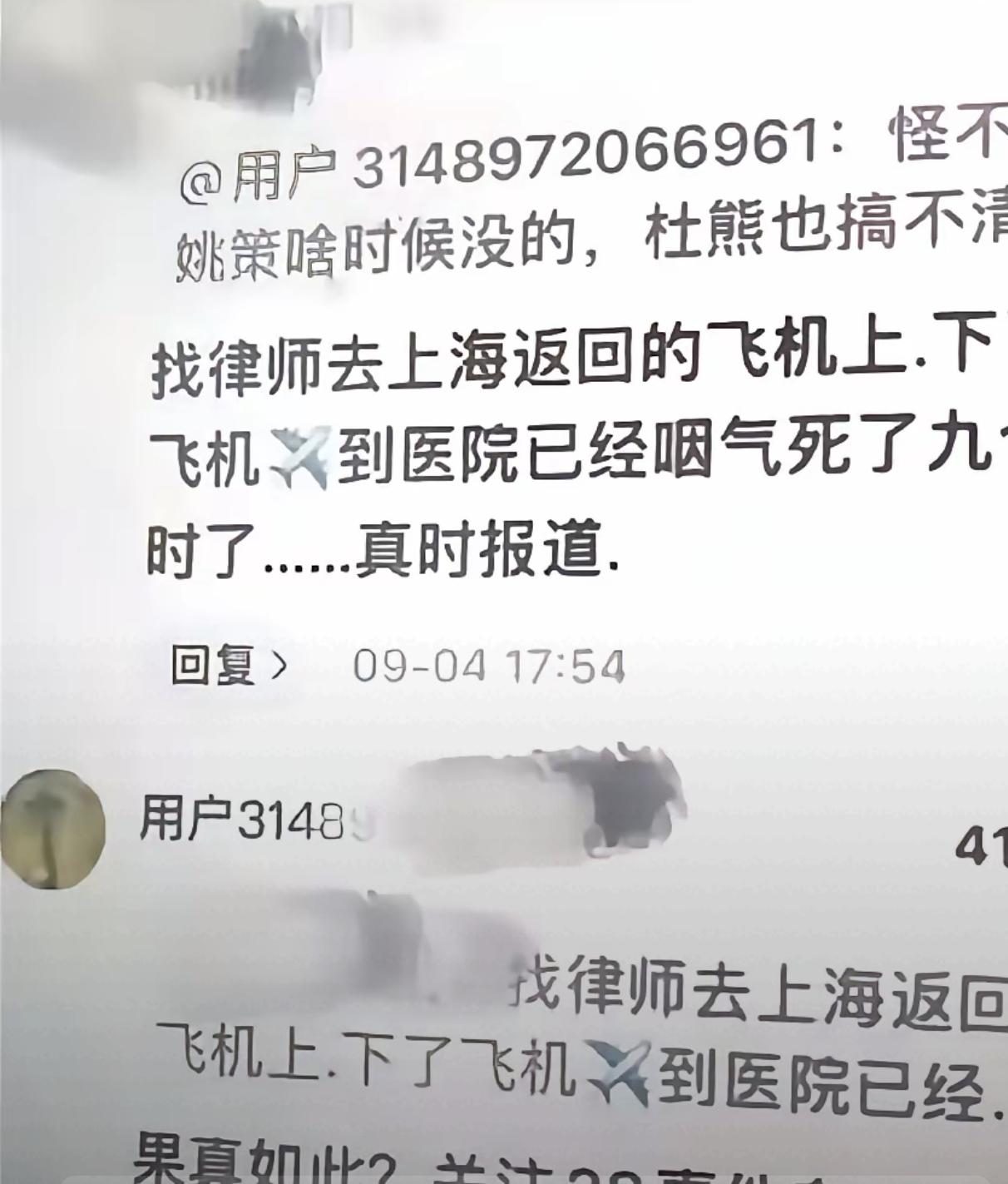1992年,浙大高材生李红涛被警察逮捕,然而让所有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趁着警察查档案的时候,慢慢挪到对方看不到的角落,毫不费力的便把手铐打开,随后气定神闲的走出了公安局..... 1993年11月,昆明看守所死囚室。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霉味,那味道厚重且黏腻。绝望的气息也如影随形,二者交织,仿佛织就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令人窒息。 27岁的李红涛,神情凝滞,目光定格在手中那堆形同“破烂”之物上,眼神里似有迷茫与思索交织,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无声的发呆状态。这是一审判决下达后的第七天,也是他距离脑袋开花最近的时候。 判决书上“死刑”两个字,终于治好了他的狂妄症。这个曾经视法律为无物、把越狱当成智力游戏的浙大才子,此刻不得不面对一个物理学上的绝对真理:即使你的智商能碾压看守所的门锁,也挡不住一颗初速700米/秒的子弹。 若时光回溯至数年前,恐怕无人会相信,李红涛竟会沦落到这般境地。往昔难以揣度当下之困厄,世事无常,令人唏嘘。 20世纪80年代,浙江大学电子工程系宛如一片璀璨星海,吸引众多优秀学子汇聚于此。这里是天之骄子的云集之地,处处洋溢着智慧的光芒与青春的朝气。李红涛拿着全国数学竞赛优胜的成绩单走进去,又带着“昆明某国企技术骨干”的身份走出来。 铁饭碗、户口、美满的婚姻,普通人奋斗一辈子的终点,只是他的起跑线。 但人有时候就是贱。平稳的日子过久了,李红涛觉得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是对智商的侮辱。婚外情成了导火索,他嫌上班赚钱太慢,心理天平彻底崩坏。 于是,他把自己那颗精密的理科大脑,用在了伪造印章和诈骗上。骗了8万块,把自己送进了昆明市公安局。 也就是在这儿,他开启了那个让中国警界至今都觉得离谱的“猫鼠游戏”。 1992年那次越狱,简直是对警方安防流程的一次公然嘲讽。 彼时,尚无高清监控之设备。李红涛双手被铐,形单影只地伫立在那长长的走廊之中,周遭的寂静仿佛都在诉说着他此刻的境遇。他居然趁着警察转身查档案的空档,把自己当成了“开锁匠”。 几根手指在锁芯里鼓捣几下,那副象征国家强制力的手铐就开了。 最绝的是,他没狂奔,而是整理了一下衣服,装成办事完工的工作人员,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公安局大门。路过门卫时,甚至还气定神闲地点了个头。 这岂能用“越狱”简单定义,分明是一种赤祼祼的羞辱。它已超越常规越狱概念,是对规则与权威极大的冒犯,令人愤懑难平。 逃亡路上的李红涛,彻底失控了。他不是在逃命,而是在炫技。 偷奥迪车失败,他就去偷桑塔纳警车。你敢信?一个通缉犯,开着偷来的警车,在情妇的大学校园里瞎溜达。 那种“全世界都在我脚下”的虚妄快感,让他像个磕了药的赌徒。直到在大学校园里被二次抓捕,他还在挑衅警察:“案子别急着结,我还能跑。” 他还真不是吹牛。在看守所,他策反了两个狱友,硬是用餐具和铁片在墙上挖了个洞,钻了出去。 那时候的他,以为自己是现实版的肖申克,其实不过是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耗子。 面对厚重的铁门和荷枪实弹的武警,李红涛终于意识到:再高明的魔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是扯淡。 一审死刑。这四个字像一记重锤,把他砸回了原型。 在等待最高法核准的死亡倒计时里,求生欲逼出了人类潜能的极限。他不想死,他手里唯一的筹码,就是大学时没搞完的那个构想——“无刷电励磁电机”。 看守所所长也是个狠人,居然真给了这个死囚机会。一间破败不堪、堆满杂物的屋子,摇身一变,成了他潜心钻研的实验室。在这看似杂乱的空间里,即将开启一场未知的探索之旅。 条件简陋得令人发指:没有精密车床,他就用牙刷柄做绝缘支架。没有标准转子,他就把牙膏皮熔化了自己捏。冷却装置?那是用饭盒改的。 这哪里是在搞科研,分明是与阎王爷争分夺秒。科研之路本就艰难,如此急迫,宛如在死神手中抢夺每一刻,只为那未知的成果与希望。 最后那几天,电机死活转不起来。李红涛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恐惧。只要电机不转,几天后他就是刑场上的一具尸体。 也许是命不该绝,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那台用垃圾拼凑出来的电机,居然奇迹般地发出了嗡嗡声。 专家鉴定结论出来了:有创新性。看守所紧急上报,枪口在最后一秒抬高了三寸。1995年,一纸改判书宣告了命运的转折:原本的死刑判决被更改为死刑缓期执行,这一变动,在当事人的生命轨迹中掀起了巨大波澜。 劫后余生的李红涛,宛如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转变,恰似换了一个人。他的眼神、举止乃至气质,都与往昔大相径庭。 他在监狱里不仅拿到了发明博览会的金奖,还干了一件极其讽刺的事——他反向利用自己的越狱经验,帮看守所设计了一套严密的监控系统。 以前他琢磨怎么找漏洞钻出去,现在他琢磨怎么把漏洞堵死别让人出去。昆明看守所自此荣膺全国模范之誉。 信源:中国青年网2016-09-19——理科男两次成功越狱 死刑前一天发明神器改判死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