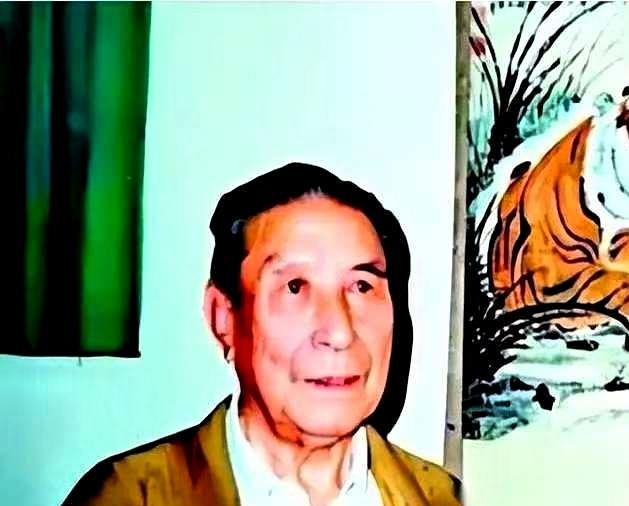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要将他接回承泽园。 1948年的深秋,北京胡同里的风像带了刀子,刮在脸上生疼。袁克定缩在墙根下,一件打满补丁的棉袄根本挡不住寒意,他佝偻着背,手里的拐杖磨得发亮,那曾是根象牙柄的文明棍,如今只剩光秃秃的木头杆。 胡同口的烤白薯摊冒着热气,甜香飘过来,勾得他肚子咕咕直叫。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空空如也,连个铜板都没有。几天前还能从垃圾堆里捡到半个发霉的窝头,今天转了大半个城,只找到几片烂菜叶,被他小心地揣在怀里——那是中午就捡来的,现在已经冻得硬邦邦。 “大少爷?”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袁克定缓缓抬头,眯着昏花的老眼看清来人,浑身一震。那是当年袁家的厨子老刘,如今头发也白了,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短褂,手里还拎着个布包。 老刘眼圈一下子红了,扑通就跪了下来:“奴才该死!奴才这才找到您!”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两个温热的窝头,还有几棵带着泥土的白菜帮子,“您先垫垫,奴才每天都给您送过来。” 袁克定接过窝头,手抖得厉害,滚烫的窝头烫得他掌心发红,却舍不得撒手。他张了张嘴,想说句“不必了”,喉咙却像被堵住,最后只化作一声哽咽。想当年,老刘在袁家后厨当差,连给客人端菜都得戴白手套,如今却要为他这个落魄公子捡菜叶、蒸窝头。 老刘没多说什么,每天天不亮就来,有时带个烤白薯,有时是半碗剩粥,总让他能填上口热的。袁克定靠着这点接济,才没在寒风里冻毙。他不再去捡垃圾,只是每天坐在墙根等,像个盼着亲人的孩子,看到老刘的身影就两眼发亮,那点骄傲早在饥饿里磨没了。 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张伯驹耳朵里。这位民国四公子之一,一听表兄袁克定竟落到这步田地,手里的茶杯“当啷”掉在桌上,茶水溅了一身也顾不上擦。“荒唐!”他猛地站起身,马褂的扣子都扯掉了一颗,“他再怎么说也是袁项城的长子,怎能流落街头?” 张伯驹当天就坐着马车赶了过来。看到墙根下那个缩成一团的老人,头发花白打结,棉袄破烂不堪,正捧着半个窝头小口啃着,哪里还有半分当年“袁大公子”的模样?他鼻子一酸,快步走过去:“克定兄,跟我走!” 袁克定愣住了,嚼着窝头的动作停了下来,浑浊的眼睛看着张伯驹,像没反应过来。 “承泽园我给您收拾好了,有暖炉,有热饭,跟我回去享几天清福。”张伯驹不由分说,让随从把袁克定扶起来。袁克定的拐杖“啪”地掉在地上,他踉跄了一下,被人架着胳膊时,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为自己落魄,是为这迟来的体面。 老刘在一旁抹着眼泪,把布包往袁克定怀里塞:“大少爷,您这就去享福吧,奴才……奴才以后还能去看您不?” 张伯驹拍了拍他的肩膀:“一起去,给表兄做口热饭。” 马车驶离胡同的时候,袁克定掀起帘子回头看了一眼。墙根下的寒风还在卷着落叶,烤白薯的甜香渐渐远了。他低头看着怀里老刘塞的白菜帮子,突然笑了,笑得像个孩子——原来这世上,最暖的从不是山珍海味,是落魄时递来的半个窝头,是绝境里肯认他这“大少爷”的老仆,是肯拉他一把的亲人。 车窗外,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袁克定拢了拢那件借来的厚外套,终于觉得,这深秋好像没那么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