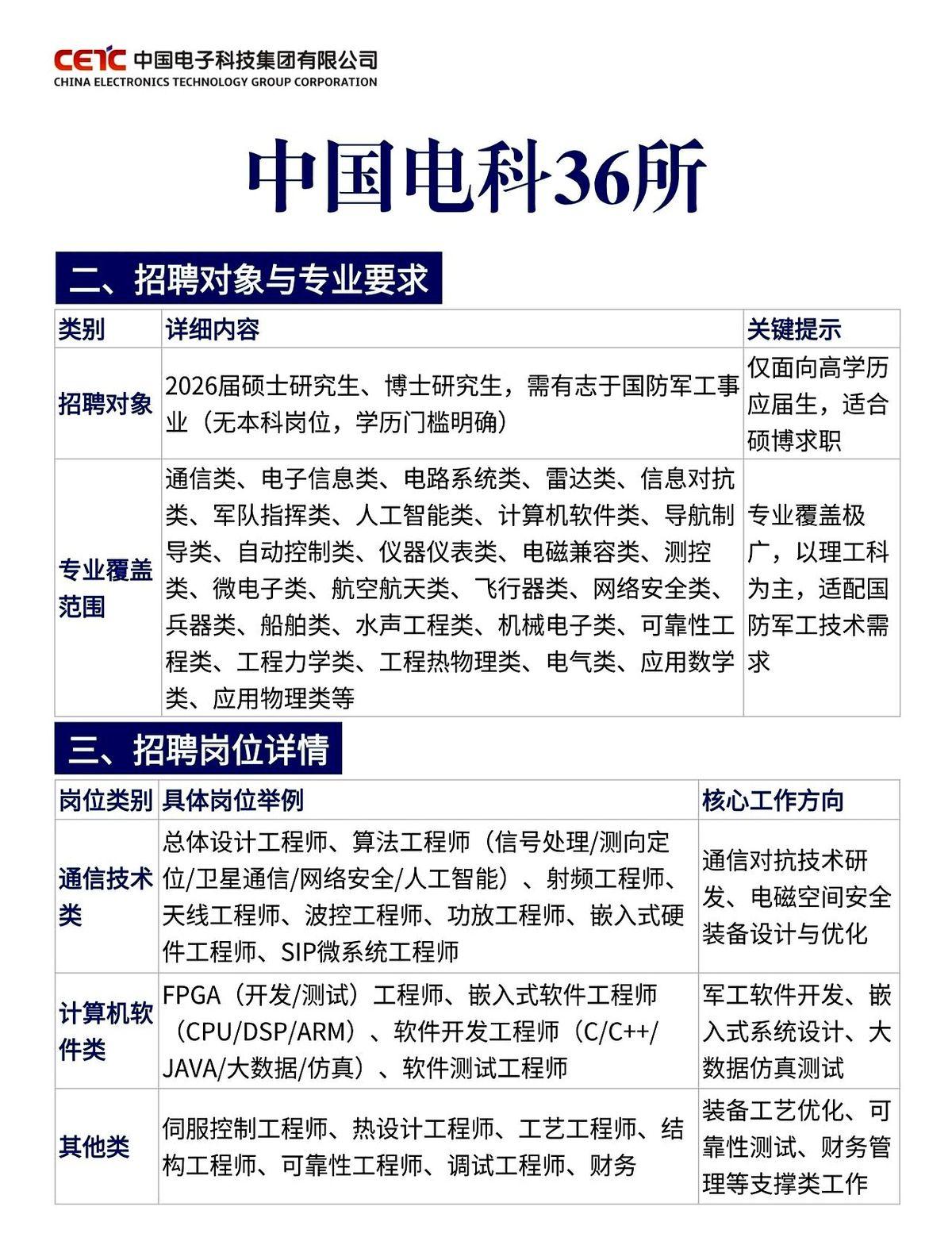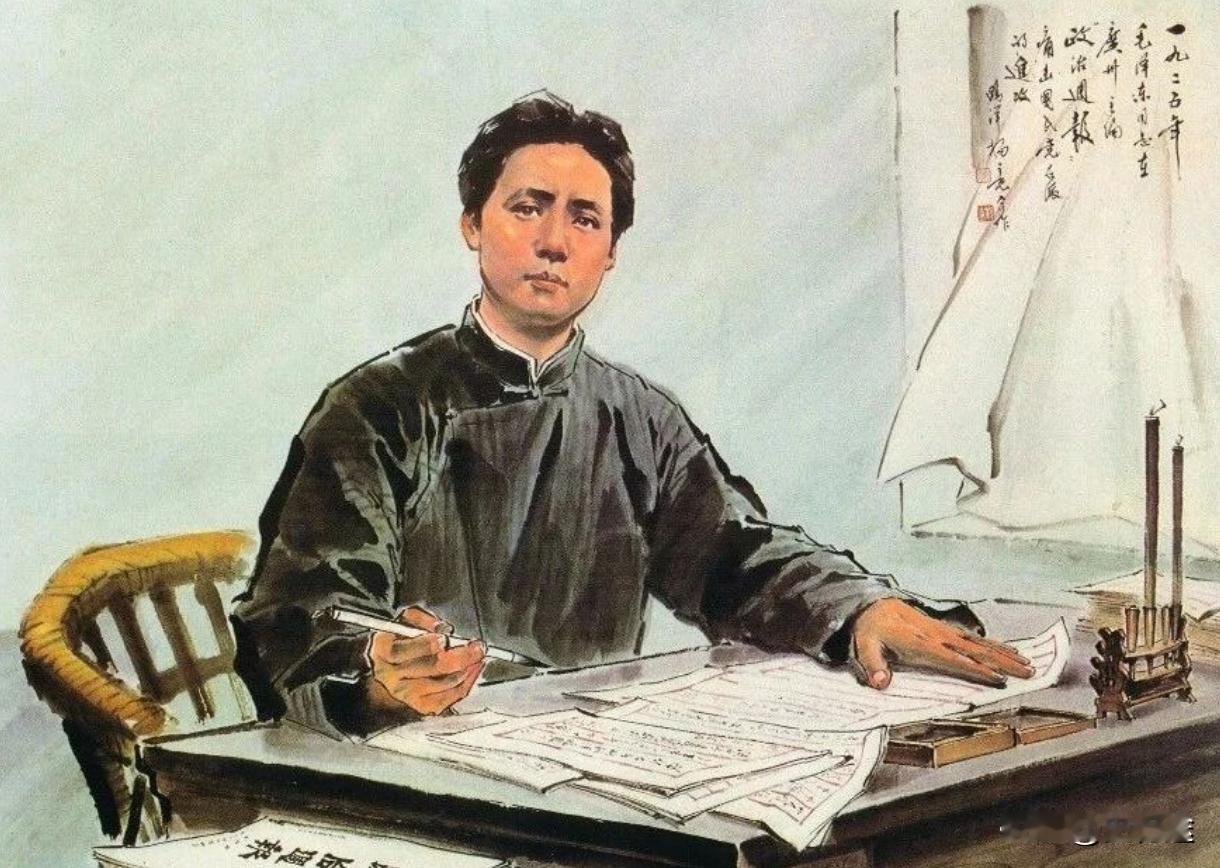图片是1999年六七月份,六弟教育大硕士学位毕业,我们约定浦东机场汇合,然后一起去陆家嘴母亲养病的住处,小住几日我们兄弟俩买了四张软卧带着母亲还有保姆回省城的家里。安顿好母亲,我就带着六弟回故乡牡丹江了。 我和六弟都出生在牡丹江,六弟就出生在桥北我们那个地委大院。大人小孩不知道他大名,都叫他闫六。 我六弟从小长的像老毛子孩,头发发黄自来卷,又从来不讨人嫌,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喜欢他。 他有意回牡丹江看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那个院子就没有了。邻居一部分跟我家一样调入省城,余下的大多数都换新居,散住在牡丹江市区内。 回去能看的就是我们那趟房子东头上,还残留着一颗榆树。 我们小时候房前是一排大人抱不过来那么粗的参天大杨树,后来说是一夜间都给砍伐了。 我和六弟回到老房子旧址,还好遇到发小铁鹏,还有后楼的猪羔子,铁鹏家跟我们家非常好,猪羔子开个歌厅,照片就是在猪羔子歌厅拍照的。 那次回家,老邻居当时在某分局当政委的巍巍给把我们聚在一起。 猪羔子20多年前就去世了,铁鹏好像是疫情前心梗走的。 图片上四个人,现在就剩我跟六弟。 我当兵回来起初是奔着刚刚组建的边防局去的,想不到回到牡丹江,家里已经去了省城。 我在牡丹江度过了两年多非常幸福的时光。 先是被安置到牡丹江啤酒厂,因为我能喝酒,母亲说不要工作也不能去啤酒厂,担心我喝坏了,就去了铁路上。 我到家先是我姐姐我哥哥我们三个一起生活,姐姐在牡丹江市中心医院,不久姐姐调回省城去了祖研。家里就剩我哥俩。反正生活非常好,我们还改造了我家的菜窖,由过去的泥窖,改造成砖砌,水泥预支板顶,我们还砌的门斗,就是房门出来接了一个房子。院子里春天都是丁香树,老邻居已经所剩无几。 八十年代初,我们哥俩鱼肉都不缺,在家吃饭的时候不多。 我在牡丹江西运转车间,三班倒,我还在我们班组织了一个文学沙龙,休班在一起探讨诗歌,小说。我们班组几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当年都住天桥下的铁路第二宿舍,我也经常过去住,经常一起去东一条路白花园饭店喝酒。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开一次病假条,去中心医院找我姐姐同事给开,所以一个月也就上半个月班。 在家主要是跟一墙之隔的邻居二得玩,他那个时候准备考大学,蔡叔就是二得爸爸,恢复职位也调去省城。他家就他自己了。他连续考了两年也没有考上大学。前些年听说他在省粮油纪委书记任上退休了,一直没有往来。二得文笔也挺好的,早些年经常在《新晚报》看到他的稿子。他们兄弟姊妹没少借他哥哥蔡凯夫的光,蔡凯夫担任过省人事厅干部处长,省边贸局长,绥芬河市领导。后来出事了,48 岁车祸没有了,很是可惜,属于英年早逝。 老邻居还有东东,文革后期他爸爸是地区财政局长,小时候比我学习好,他后来当了税官。九十年代我回牡丹江住北山嘉林酒店,当年牡丹江非常好的酒店,东东骑自行车去酒店看我。 我感觉他没有小时候那么光鲜了,我忽然想起鲁迅在《故乡》这篇散文里笔下的两个闰土 ,少年闰土跟中年闰土。 少年闰土: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鲁迅笔下的中年闰土: 头戴破毡帽,身穿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手不再灵动,是“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的劳作之手,眼神也没了光彩,多了麻木与怯懦。 听说东东是税务局副局长退休,还是比中年闰土强多了,但是我们也没有了往来。他妹妹小芳八十年代在哈尔滨上大学,星期天经常来我家吃饭,我母亲对牡丹江老邻居都非常好。 小芳芳长得漂亮大个,我六弟那个时候也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读本科,不明白我六弟跟小芳怎么没有处对象。 往事如烟,忘不了的人和事儿,才是真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