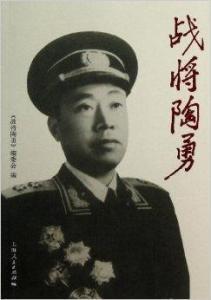1943年春,八路军营长张中如在榆树村沟口伏击鬼子时,被一颗子弹穿透胸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仅仅是漫长痛苦的开始——真正的生死考验,才刚刚拉开帷幕。 张中如是山西五台人,1919年生,家境贫寒,十六岁投奔八路军,从通讯员做到营长,打过不少硬仗。榆树村沟口那一仗,他带队设伏,目标是截一支运送弹药的鬼子车队。战斗打响,他冲在最前,瞄准敌军指挥官正要下令开火,胸口猛地一热,子弹从前胸穿入,带出一股灼痛。战友们把他拖下阵地时,血已浸透军装,呼吸像拉破风箱。卫生员简单包扎,连夜送往后方医院,可那时候缺医少药,条件简陋到连消毒酒精都稀罕。 真正折磨他的,是子弹留在体内的残片与不断恶化的感染。当时的医疗手段取不出深嵌的弹片,只能靠盐水冲洗和草药敷贴控制炎症。伤后第三天,他开始高烧不退,伤口周围红肿发黑,疼得整夜无法平卧。看护的战士轮流守着他,用棉签蘸水润他干裂的嘴唇,他却总说别管自己,让同志们多休息。可他心里清楚,一旦熬不过去,不止是命的问题,伏击战的情报和经验都会跟着他埋进黄土。 转机出现在军区调来一位懂西医的军医。那人检查后发现,弹片压迫肺叶导致积液,再拖下去会危及生命。手术没有麻醉,只有几片止痛药顶着,张中如咬着木棍,汗顺着下巴滴到床单上。 军医用简陋的镊子和探针摸索着取碎片,每动一下他都浑身抽搐,却硬是没吭一声。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取出三块大小不一的金属,其中一块边缘带血肉,足见嵌入之深。术后他虚弱得连抬手都难,但总算把最凶险的感染压了下去。 康复过程比手术更煎熬。肺部受伤让他呼吸短促,走几步就喘,夜里常咳醒。可他没歇着,稍微能动就开始做呼吸训练,扶着墙一步一步挪,把力气一点点找回来。有人劝他转做后勤,他摇头,说营长不光是指挥打仗,更得带头适应战场上的任何状态,真到再上阵时,没力气就是拖累。1944年初,他回到部队,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冲锋在前,却用经验和沉稳带着连队打了几次漂亮仗。 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很深。伤后留下的后遗症伴随多年,阴雨天胸口会隐隐作痛,呼吸也不如常人顺畅。可他从不拿这个当借口,抗战胜利后,他继续留在军中,从作战部队转到训练岗位,把在生死线上悟出的战术要领教给新兵。他说,打仗不光靠勇,还得懂怎么在绝境里保住有用之身,把命延续到能再拼一次的时候。 张中如的故事让人看清,很多军人的生死考验不在枪林弹雨那一刻,而在中弹之后的漫长抗争。前线负伤只是起点,能不能活下来,要看意志、医疗条件、护理支持,还有那份不肯放弃任务的执念。他挺过来了,不是因为运气好,是因为哪怕在剧痛和虚弱里,他依旧想着队伍和战局,把个人的痛压到一边,先顾全大局。这种选择,让一次普通的伏击战伤员,变成了能继续带兵作战的骨干。 从榆树村沟口到后方医院,从没麻药的手术台到一步步恢复训练,他的经历像一根链条,一环扣着一环——中弹是意外,活下来是挣扎,重返战场是信念。现实中,伤病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会把人的身体、心理、使命感受全部搅在一起。有的人挺不住,悄悄退出;有的人咬牙撑住,把残缺变成另一种力量。张中如属于后者,他让“营长”这两个字在后半程多了沉甸甸的份量。 这事也提醒我们,评价一个战士不能只看他在战场上的英姿,还要看他倒下后如何站起来。真正的硬气,有时是忍着痛做完手术,是喘着气练回体力,是把伤痛当成日常的一部分继续向前。战争年代,这样的人不是少数,他们的坚韧构成了队伍一次次从血里爬出来的底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