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itizing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South Korea–Japan dispute over materials–parts–equipment products》(作者 Min Gyo Koo,发表于 2024 年),我尝试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故事的大概是2019年,日本限制向韩国出口三种关键材料,一度掐住韩国高科技产业的“喉咙”。韩国痛定思痛,把“材料-零件-设备”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豪掷数十亿美元推本土化。短期见效,长期隐忧:安全化成了政治口号,补贴催生“僵尸企业”。这场日韩科技争端,揭示了全球制造的新现实——技术就是安全,产业就是地缘政治。
故事开端:两个邻居+一个突发的出口限制
在东亚,有两个老朋友/竞争者 —— South Korea(韩国)和 Japan(日本)。它们的制造业链条长期以来高度互补:日本在“材料-零件-设备”(Materials-Parts-Equipment,简称 MPE)领域有强势技术和产业基础,韩国在半导体、显示器、电子整机等方面快速崛起。文章指出,贸易互依程度之高,甚至韩国进出口总额中贸易依赖度曾达70%。
故事的转折点出现在 2019 年:日本政府在“白名单”(whitelist)制度中,将韩国从简化出口程序的名单中剔除,针对三项关键材料(氟化高纯度氢氟酸、高纯度光刻胶、氟化聚酰亚胺)实施更严格出口控制措施。 
日本的官方说法是:因为信任机制受损,韩国可能把这些关键物资再转出口给不利国家(如北韩/伊朗)从而威胁日本的“安全利益”。 
对于韩国而言,这是一记警钟:它发现自己在高端制造链条中虽然强劲,但却在很多关键材料/零件/设备上仍对日本高度依赖。文章指出,“日本在全球这三项产品的市场份额达 70-90%”。
在被限制之后,韩国政府(当时为 Moon Jae‑in 主政)决定:不能再被动依赖,要主动出击,将“材料-零件-设备”(MPE)产业定位为 国家安全、高科技竞争力 和 产业自主化 的关键。 
具体来说,他们设定目标:选择约 100 项关键MPE产品(后扩展到 150 项),希望在 1 年内稳定 20 项、5 年内稳定 80 项;并在 2020 年通过《MPE 特别法》,准备投入约 100 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支持。预算从 2020-2022 年累计约为 7.1 万亿韩元。 
这些产业政策工具包括:技术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贷款支持。 
从“工业升级”角度看,韩国试图走一条所谓 “新型工业政策”(new industrial policy, NIP) 路径:不仅是被动应对(出口受限),而是将产业链自主与国家安全挂钩。
文章在理论部分回顾了 “经济国家手段”(economic statecraft)和 “产业政策” 在全球化与供应链高度互依背景下的新形态。
故事高潮:政策执行的困境与现实折射
不过,故事并没有完全按照英雄剧本来。文章指出,韩国这条“本土化”强化MPE产业链的路径虽看起来很强气,但在实践中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目标/工具驱动过于意识形态化
政策优先考虑“减少对日本依赖”、“国家安全化”诉求,而不是基于产业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产业内学习”“协同效应”等典型 NIP 设计原则。文章批评说:政策运作更多的是政治动员与意识形态宣言,而非严密的产业设计。 
2. 执行机构政治捕获、缺乏反馈机制
虽然执行主体是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MOTIE),但事实上因为总统府高度介入、把产业政策作为外交/民族主义工具,造成行业政策被政治因素绑架。文章指出,MOTIE缺乏政策“探索—反馈—改进”机制。 
3. 政策成效与成本疑云
虽然官方数据显示:如高纯氢氟酸对日依赖降了约 30%、光刻胶日本来源降至 50%以下、氟化聚酰亚胺几乎实现替代。  但文章指出,这些替代可能只是“换了供应地”(例如日本公司在比利时设厂对韩国出口)而非真正脱离日本技术/资本控制。更多关键是:整体进口额反而从 2019 的 329 亿美元增至 2021 的 393 亿美元。 
文章还指出:大量补贴下的“僵尸”MPE企业数量从 2019 到 2021 翻倍,说明“赢家选定”(picking winners)风险大、资源错配严重。 
4. 产业链分工优势被忽视
韩国与日本原本在全球生产网络(GPN)中形成互补:日本提供高端材料/设备,韩国提供中下游制造出口。文章指出,过度强调本土替代、切断这种分工关系,反而可能削弱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福利。 
5. 安全化倾向泛化的风险
当国家安全成为所有高科技产业的标签,政策就难以界定“哪些是应优先补贴”“哪些是真正战略”——作者警示:“如果把所有事情都说成国家安全,那么政府支持就无边界,资源也会被分散、造成道德风险。”
故事尾声:反思与启示
文章最后总结说:这起韩国–日本MPE争端,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国家手段”加“产业政策”叠加的案例。它展示了在全球供应链高度互赖、技术竞争激烈的时代:贸易、技术、产业、国家安全已经难以分割。
但作者也强调:政策不能只是被动反应、也不能把“安全”挂在所有事情上,而应当“有意识、有框架、有战略”。简单来说:政府在介入产业政策的同时,需要明确目标、设计工具、评估反馈、选择真正的“关键点”,而不是全面地、模糊地把“所有核心产业”都纳入“国家安全”范畴。 
对于韩国而言,这一轮政策虽有短期“减少对日依赖”成效,但长期是否提升整体福利、是否提升产业竞争力,尚待观察。文章呼吁:政策制定者需谨慎,不应被短期民族情绪/政治动员所主导。
在研究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价值流分析、新型工业化等,这篇文章从产业政策+价值链+安全视角提供了几个重要视角:
• 价值链依赖与脆弱性:韩国虽然制造强,但在关键环节(高端材料/设备)依赖日本。对你研究中国制造业、江苏/邯郸产业集群、数字化升级的情境,这提醒:即便在整机制造环节强势,若核心零部件/设备/材料被他人控制,就会形成战略弱点。
• 产业政策的设计框架:文章引用了 Dani Rodrik 等学者关于“新型工业政策”的设计原则(例如:目标明确、工具配套、政策机构能力、反馈机制、避免资源错配).  对你在政府报告、招商策略中思考“如何设计支持政策”“怎样避免‘补贴→僵尸企业’”尤其有参考价值。
• 安全化/国家化视角的警示:在数字化、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背景下,“数据安全”“供应链安全”“关键设备安全”越来越被挂上“国家安全”的标签。文章提醒:若所有制造业都标注为“安全产业”,就会模糊优先级、导致资源分散。你在建议政府或产业园区策略时,应注意区分“真的战略关键”与“普通提升项目”。
•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产业协作:韩国–日本的争端说明:切断供应链中的互补关系不是简单“国产化”就能解决的。你在江苏/邯郸产业集群研究,或在为生物基、机器人供应链设计招商话术中,也应考虑“与上下游、国际伙伴的协作”而不仅是“国内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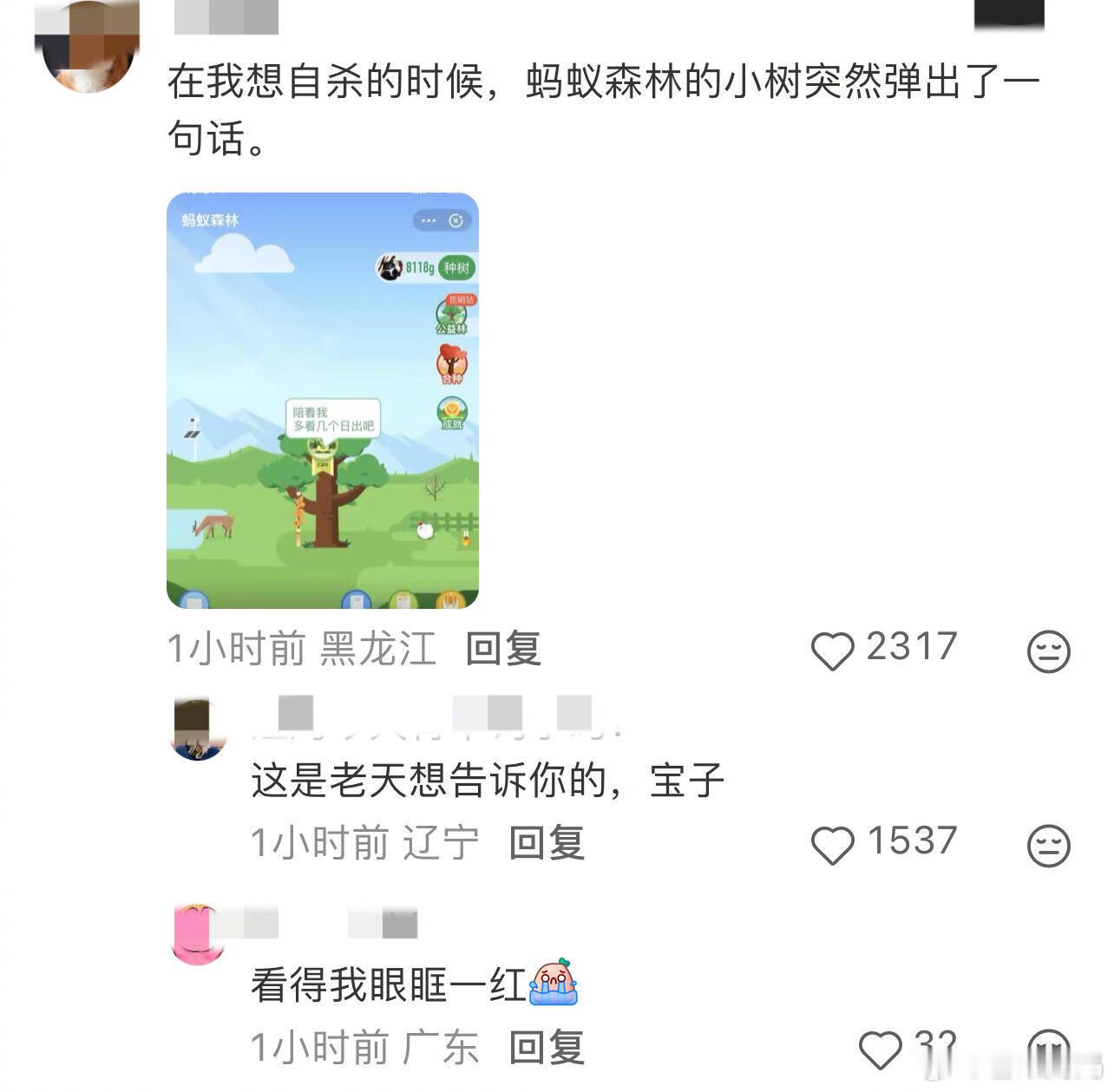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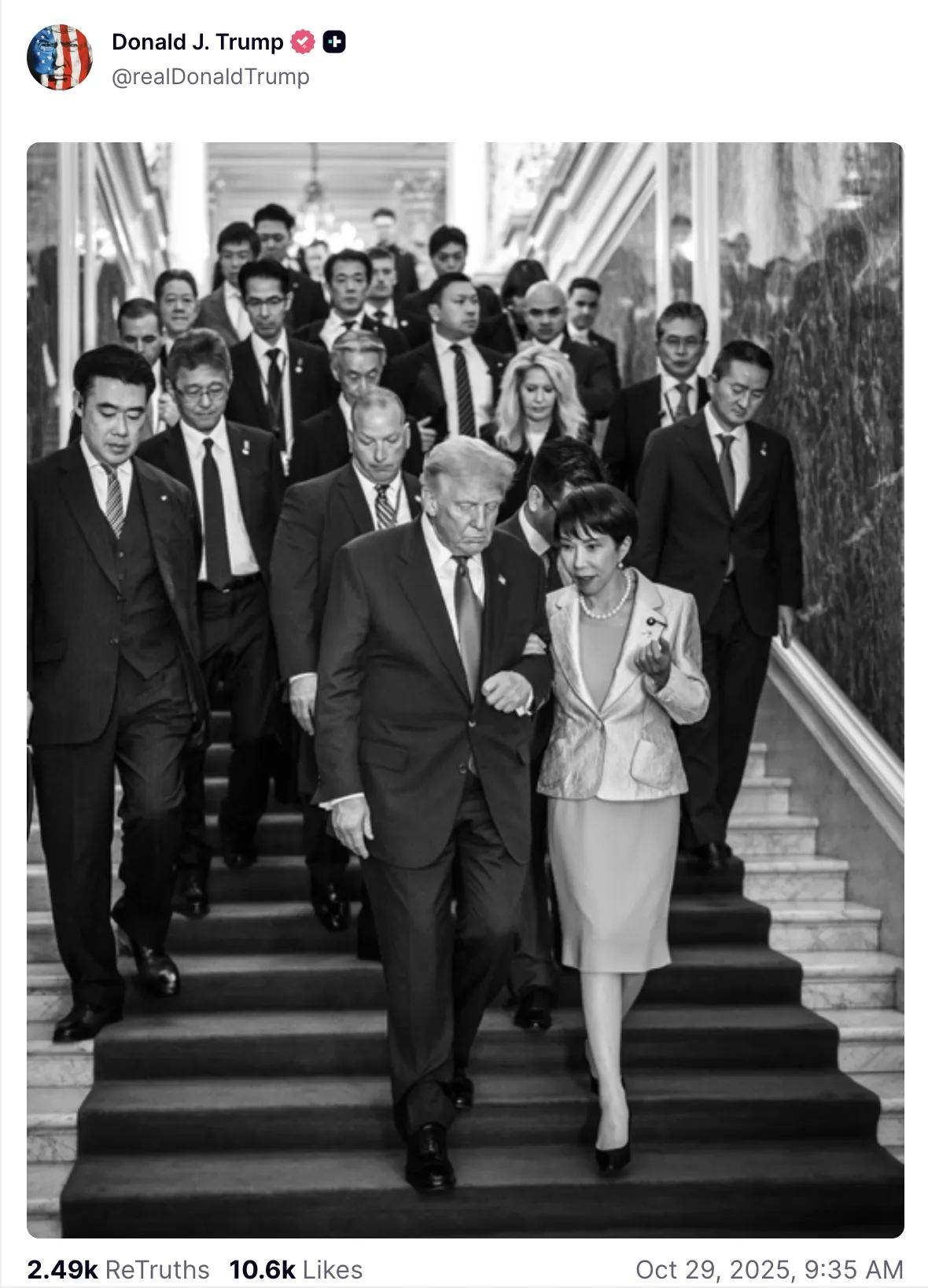

![这个热点词好妙🤣满天星连夜改名钻石星[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4170560403530478688.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