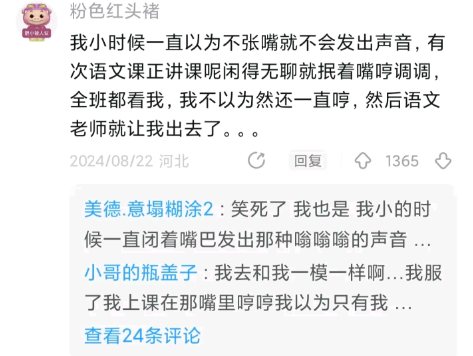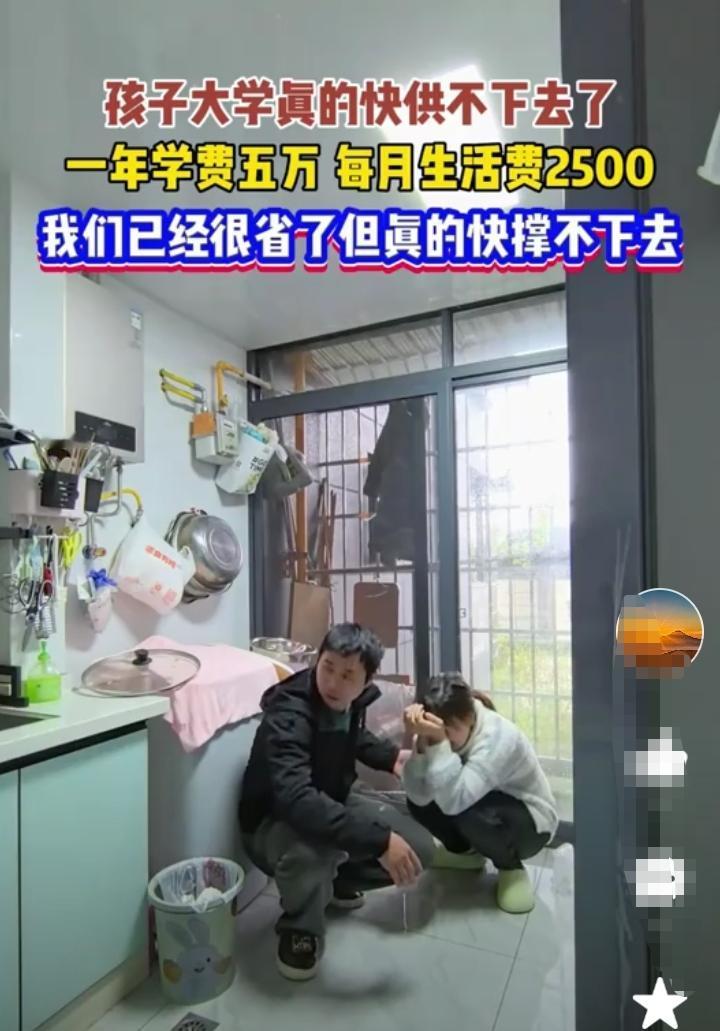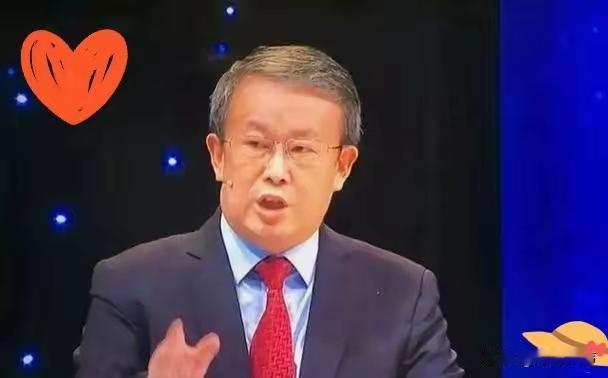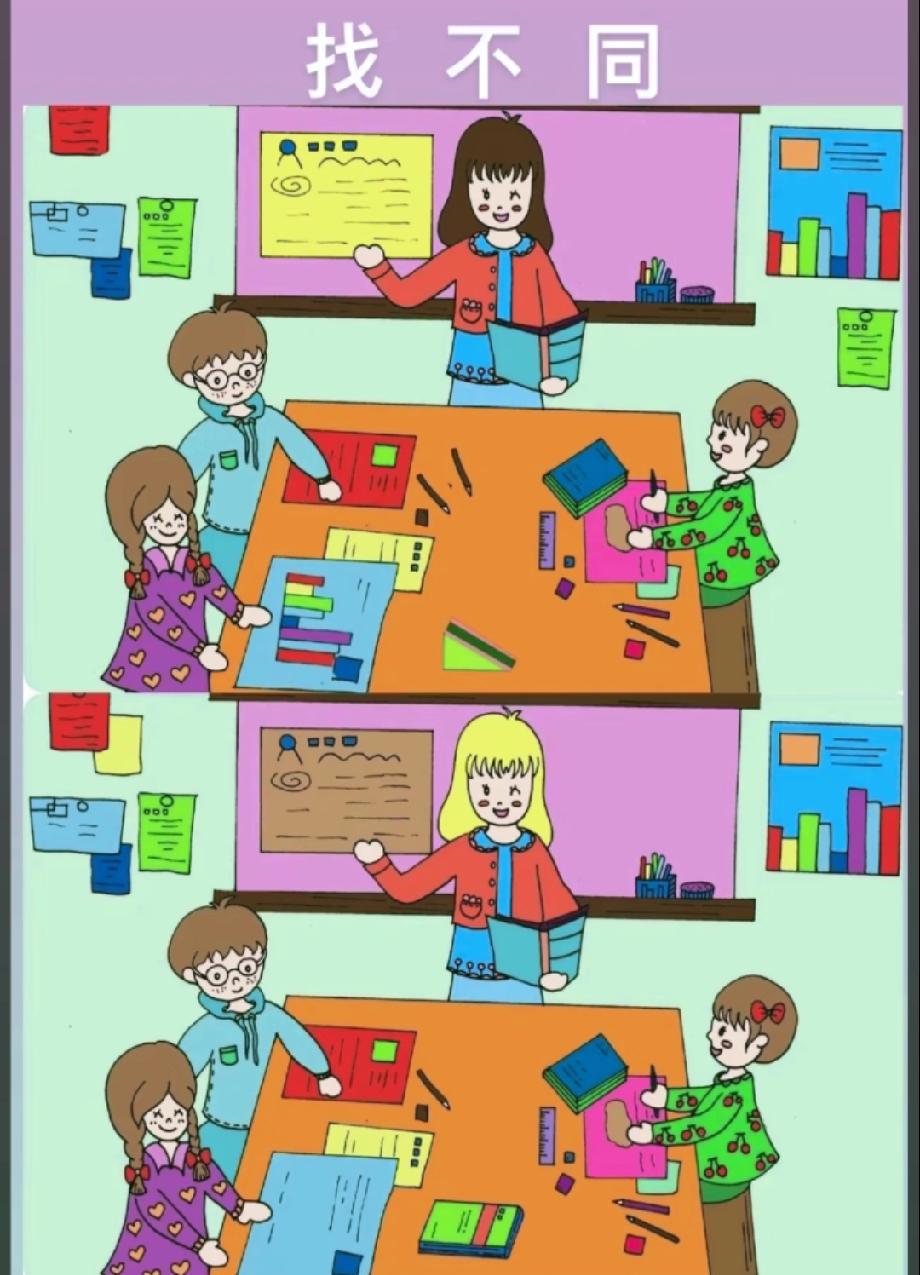1977年,知青张梅香考上大学。临别前夜,她轻轻的,解开上衣扣子,红着脸,对农民男友郭明亮说:“今晚,让我做你的媳妇吧!”谁料,张梅香刚走,郭明亮就开始相亲,竟然还看上了:带着2个娃的农妇。 1969年的陕北高原,北风卷着沙土扑打着破旧的窑洞,19岁的张梅香挑着两只木桶走在陡坡上,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摔进泥坑。水洒了,裤腿破了,手掌渗出血珠,她咬着嘴唇没哭出声,却在拾起摔坏的钢笔时终于崩溃,那是父亲送她的生日礼物。 就在这时,一双粗糙的手接过她掌心的钢笔,郭明亮蹲在身旁,从怀里掏出块蓝布仔细擦拭笔杆:“俺弟也会修笔,明儿个让他试试。” 这个沉默的农村青年,就这样走进了张梅香的生命,他教她辨认糜子和谷子,深夜偷偷帮她修补漏雨的屋顶,寒冬清晨总在她门口放一捆柴禾,最让张梅香难忘的是那个饥荒春天,郭明亮把仅有的两个烤红薯全塞给她,自己嚼着榆树皮说“俺吃过了”。 1975年夏收时节,公社副主任黄书良把张梅香堵在麦垛后,这个被社员暗地里称作“黄鼠狼”的中年男人,满嘴酒气地要拉她去“汇报思想”,郭明亮突然举着镰刀出现,麦穗般的汗珠顺着额角滚落:“黄主任,县里来人查账了。” 等黄书良骂骂咧咧走远,这个平日温厚的青年一拳砸在麦垛上:“他再碰你,俺跟他换命!” 月光下的窑洞里,张梅香把北京带来的绒线手套拆了重织,暗红色围巾在郭明亮颈间格外醒目,他则用三个月工分换来钢笔零件,在煤油灯下拼凑到半夜。两颗心在黄土高原的朔风里越靠越近,却都默契地避谈未来,直到1977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惊雷炸响山沟。 张梅香收到录取通知书那晚,郭家窑洞飘出久违的肉香,郭明亮母亲杀了下蛋的母鸡,颤巍巍把鸡腿夹到张梅香碗里:“闺女,到了北京……常念着咱黄土坡的好。”老太太转身抹泪时,张梅香看见郭明亮把脸埋进灶膛的阴影里。 深夜的打谷场上,新收的谷秸堆成小山,张梅香突然抓住郭明亮结满老茧的手,贴在自己剧烈起伏的胸前:“明亮,今晚让我……”话音未落,青年像被烫到般猛地抽回手,用破棉袄紧紧裹住她:“你傻不傻?你是要念大学的人!” 他掏出一块上海牌手表,表带还带着体温:“拿上这个,上课看时辰。”见她不肯接,急得声音发颤,“你要不收,俺现在就跳沟!”最终妥协的是张梅香,她把珍藏的笔记本塞给他,扉页写着“四年后结婚用”。 第二天清晨,驴车卷起的尘土遮住了送行的人群,张梅香频频回头,始终没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她不知道,郭明亮正蹲在崖畔的老槐树后,把拳头塞进嘴里咬得鲜血淋漓,驴车转过山坳时,他疯狂刨开树根旁的泥土,埋进那个散发着雪花膏味的笔记本。 北京的求学生活如期展开,张梅香在信里描述未名湖的波光,郭明亮的回信却越来越薄。第23封信里,他写道“村里人都说咱不般配”,张梅香当即寄去两人合影,背面认真标注“未婚夫妻”。她不知道,与此同时的郭家正在上演一场抉择,郭父咳着血沫拍炕席:“你要耽误人家大学生一辈子?” 刘桂兰,这个带着两个幼子的寡妇,局促地在衣襟上擦手:“明亮常念叨张同志……”话音未落,她三岁的小儿子突然摇摇晃晃扑向张梅香,举着半块枣糕直往她手里塞。 黄昏的打谷场上,两个身影隔着麦垛沉默。郭明亮终于开口:“桂兰男人修水渠塌方没了,她婆家连抚恤金都扣……”他踢着脚下的土块,“去年俺娘瘫炕上,都是她端屎端尿。”突然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四年来的信件捆得整整齐齐,最上面是那张合影。 张梅香的目光落在远处,刘桂兰正蹲在菜园里拔草,四岁的女孩乖巧地给母亲擦汗,夕照给母子三人镀上金边,她想起离京前导师说的话:“苦难不是用来歌颂的,但尊严可以在苦难里开花。” 第二天送别时,郭明亮往行李塞满小米红枣,张梅香走到村口突然折返,将钢笔别在他胸前口袋:“留给娃娃认字用。”转身时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呜咽,像很多年前那个摔倒在泥泞里的少女,她这次依然没有回头。 而在陕北的农家乐庭院里,郭明亮正给游客演示犁杖的使用,他的孙子举着手机录像,镜头扫过墙上斑驳的奖状,“优秀乡镇企业代表”,暮色中老人摩挲着玻璃相框,里面珍藏着1977年的笔记本残页,隐约能辨出“结婚”二字被重重划去,旁边添了稚嫩的铅笔字:“奶奶说这是传家宝。” 黄土地上的麦子熟了一茬又一茬,那些被时代洪流冲散的爱情,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在岁月里扎根。当城市的月光与乡村的星辉在记忆里交汇,人们终于懂得:有些告别不是辜负,而是让彼此在各自的田野上,长出更饱满的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