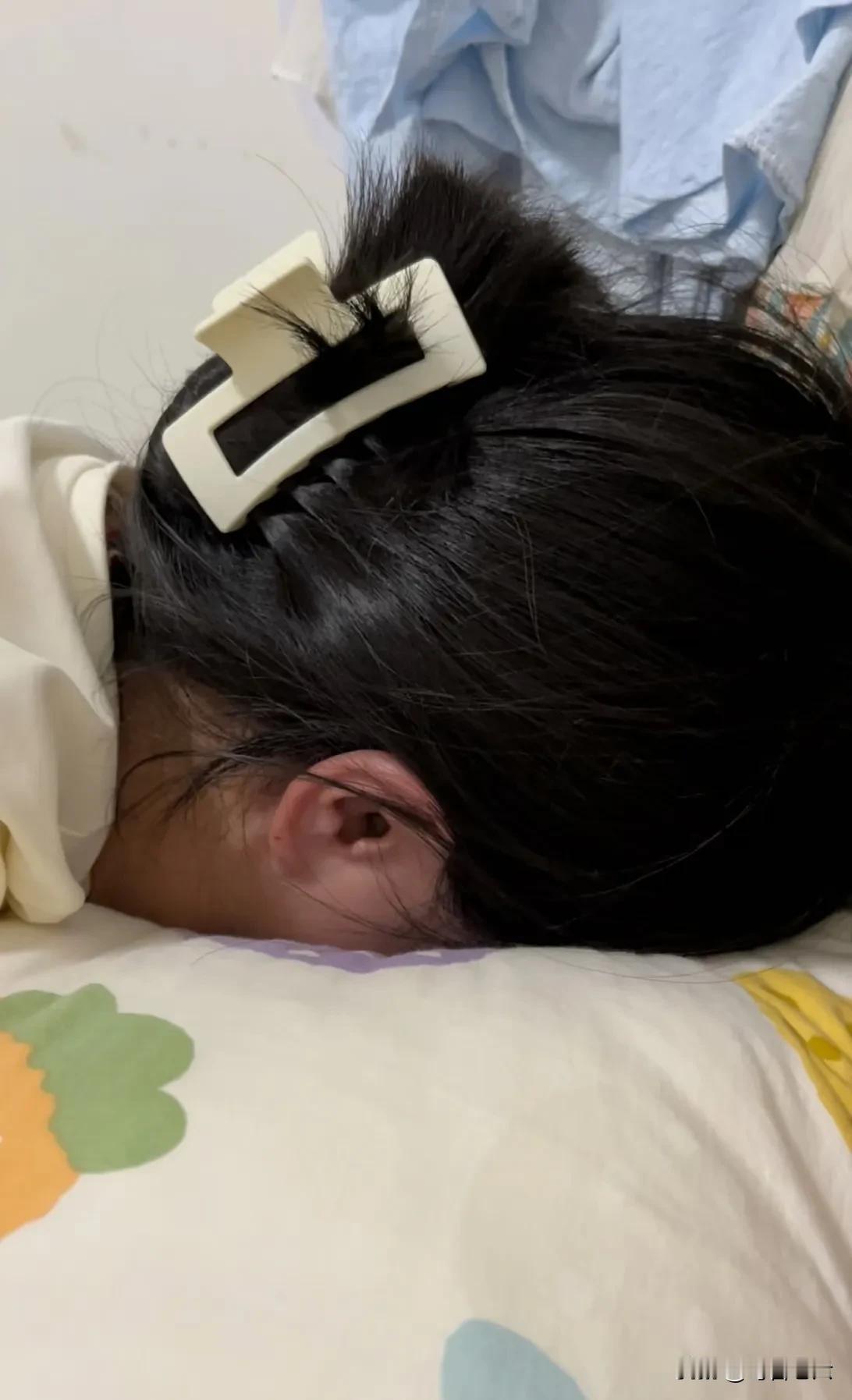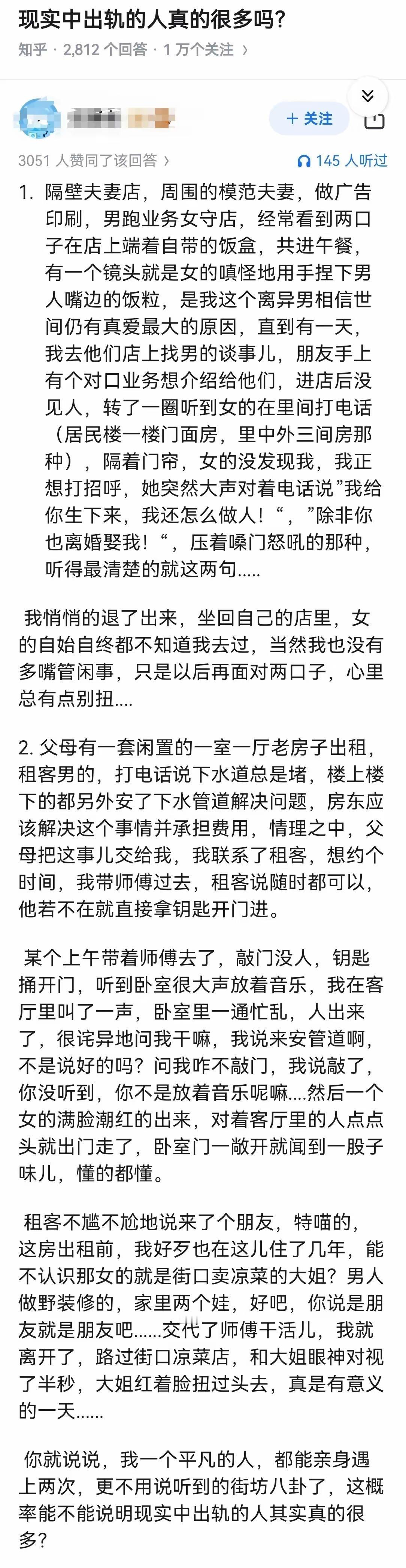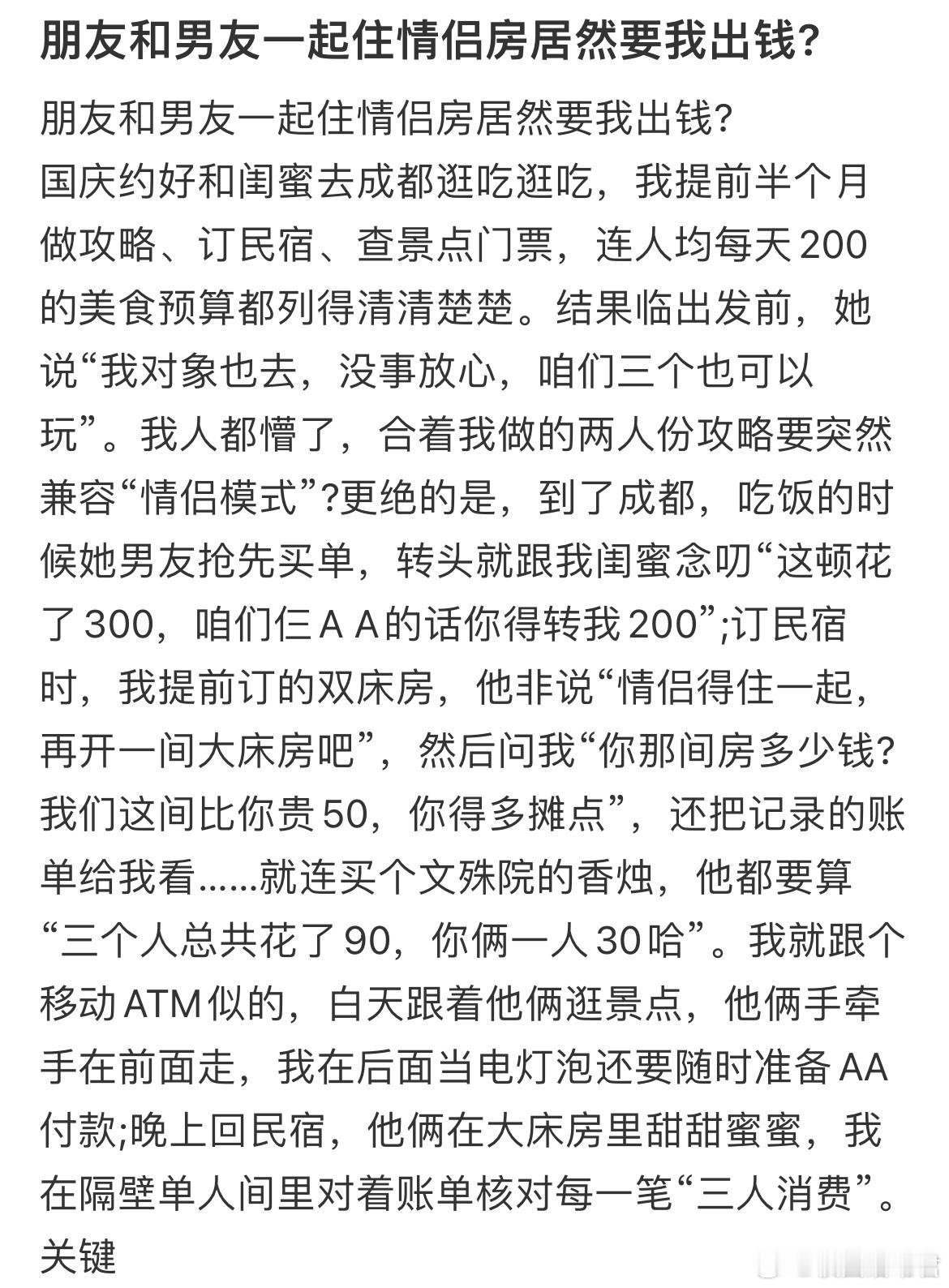1934年,新婚第1天,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在一起调情,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凭你也想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夜深灯灭,屋里还剩两人影子。门虚掩着,缝里透出人影交错。新婚第一晚,鞋没脱,灯没熄,新娘停在门口没动脚。屋子里传来笑声,低语夹着喘息,躲不开,也听不清。 脚步没退,也没前,手握成拳,指节泛白。她看着丈夫身影落在表嫂肩头,愣了几秒,转身走开,像什么也没看见。 几天后,婚宴热闹,亲友道贺,家里摆满红纸金字。她换了笑脸,招呼宾客,端茶倒水,拍照合影,脸上一点波澜也没有。 新屋那张床她重新铺过,红被褥翻晒两次,连香囊都换了。隔天起床烧饭,洗衣煮粥,一样不落,像从没发生过那晚的事。亲戚嘴碎,背后说她福气重,能压住那人一身野劲,她听到了,也没回嘴。 第一胎来得快,肚子还没大几月,就有人在她背后说话。说她真能忍,也真能生。一个接一个,孩子围着膝头转,背着篓子还得抱娃喂奶。 饭桌上碗筷一响,她就得起身夹菜、添饭、擦嘴角。夜里小儿啼哭,她披衣起身,一只手哄一只手揉眼睛,床那边翻个身继续打鼾,仿佛家里只有她一个人醒着。 白天忙家务,晚上带孩子,有时还得记账抄稿。她不是没想过离开,也不是没写过信。桌上那封信写了一半,墨迹晕开,第二天就被撕掉。 她知道,自己走了,五个孩子没下落,也知道留着,等不到体面。可再难,也得撑。撑着煮米,撑着进药铺,撑着把孩子一个个送进学堂,撑着写稿养家。谁让这一家人,早就靠她活着。 那天手里只剩几枚铜子,米缸底露出瓷花,她拎着碗去厨房,米粒都数得清。她没声张,照旧做晚饭,等锅冒热气才去书房开口。话还没说完,耳光先响了。 响得狠,响得脆,脸一歪,耳膜嗡嗡响。她愣住了,手还举着,空气像凝住。对面那人甩下一句冷话,拂袖而去。她站在原地没动,锅里的粥糊了,孩子在哭,她转身出门,脸上青紫,手上还捏着那枚铜子。 街上人来人往,她低头走进印刷铺。坐下开始码字,字挤在一起,行距都缩。她一口气写完三篇稿,没改就投,稿费换来半袋米和几张油纸。 她抱着米回家,路边摊卖糖葫芦,孩子拉她衣角,她没停步。米扔进缸那刻,她拍了拍手,笑了一下。 日子一天天过去,稿件越投越多,字越写越狠。她笔下写尽女人苦楚、婚姻泥潭、家庭困兽。她不吵不闹,也不哭不闹,只用字刮人脸,用文刺人心。 有人骂她泼辣,有人说她毒舌,她都收着,回家继续写。有时稿子退回来,她就改;有时稿费被扣,她就再写一篇。 她没读完大学,却把文坛搅得风生水起。连隔壁邻居都知道,这个女人不是吃闲饭的,也不是挨打不还手的。日子过得紧,她也不求人。 孩子病了,她写;灯坏了,她修;冬天缺柴,她上街捡树枝。孩子大了,问她当年怎么熬过,她笑着说,活着就不算输。 那年书展,她站在台上,身后一排作品展板。有人在台下喊她名字,也有人不屑地撇嘴。她都看见了,只是不接。采访时她说,这些年吃的苦,写出来太多,留下一半就够了。 有人问她,那个男人现在怎样,她只说了一句:那是过去的影子,已经没有轮廓。 那天晚上的红烛早灭,婚床早塌,耳光的火辣也早冷掉。留在记忆里的,是那个深夜她翻出米袋,把最后一粒米抖进锅里的声音,清脆、响亮、像一声回击。 不吵不闹,不退不让,她用整整十年,写出一份清账。不是对那个男人,而是对当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