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天,齐白石已经快90岁了,他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把将25岁的新凤霞拉进一个房间,指着一个放满钱的立柜:看到了吗,这里全是钱,你随便拿。 门一推开,空气瞬间凝住。立柜发出“咯吱”一声,柜门半掩,角落泛出一片暗金光。房间不大,墙上挂着写意牡丹,桌上摞着画稿、宣纸、墨块,全压着一个小木盒。 柜子边站着一个瘦小老头,手一挥,柜门全开,钱堆得满满,整整三层,塞得抽屉都合不上。那人眉毛一挑,眼神带火,像在宣判,也像在试探。 地板吱呀响,步伐停在柜前。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那儿,脸色微红,手指紧握。面前这堆钱压得她直不起腰,呼吸也慢了一拍。 她没动,也没说话,目光扫过每一张钞票,再扫过那扇还没关紧的门。窗帘晃了一下,阳光从缝里钻进来,刚好落在她脚边。 屋外有人路过,脚步忽快忽慢。两人一动不动,气氛像罩了层玻璃。谁也没先开口,谁也没后退半步。立柜里传出轻微摩擦声,是风吹进柜门,纸币互相摩擦。 老头的手还搭在柜门边,指节用力,泛出青白。没人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只知道那动作,不是随便指指,是认真的。 时间往前推,新凤霞刚入评剧圈不久,唱腔一出,台下掌声不断。她年纪不大,声线干净,眼神里有股倔劲。那年演出完,几位画坛前辈轮流登台献画敬艺,最后一个就是齐白石。 他那时已经坐轮椅,须发皆白,手却稳得像铁钩。一幅虾完成,落款写了个“凤”字,旁人看不懂,他自己却点头。有人说是随手写的,有人说是赠人留名。 从那次起,两人来往渐密。新凤霞演出完常去拜访,齐白石也常提笔画她。评剧扮相、素衣影像、甚至一只素手,都画过不止一次。画送了不少,墨香也多了几分亲近。 旁人看在眼里,起初当成老少传艺,后来议论越来越多,连家属都开始留意。有一天,齐白石突然关上屋门,把那年轻人叫进房里,就有了立柜那一幕。 有人说那柜子里的钱是卖画得来的,也有人说是几十年积攒下的稿费,还有人说那是他留给自己“传艺之人”的见面礼。说法多,真相没人敢问。当事人也没回应过。 只知道那段时间,新凤霞每次来访,门总是虚掩,茶总是热的,屋里总是安静。再后来,画送得更勤了,名字落款也换成了两个字:“白石”。 外人看不透这段关系,有人说是父女情,有人说是知音意。画界有人打听,戏圈有人猜测,话传得越来越远,版本也多了起来。 有说齐白石一心想收她为徒,有说他想把全部财产交给她。说得最多的,是那立柜事件,说得最夸张的是“当场拿走三叠现钞”。可谁也说不清,新凤霞到底动没动那个钱柜。 新凤霞那几年演出不断,忙得脚不沾地。台上唱,台下练,间或拜访名人学艺。她的名字跟齐白石的画一样,在圈子里传开了。 有人说她的评剧里多了股“画意”,唱腔更沉稳,身段更有味。这些变化,也许来自那个老人的教导,也许来自那间不对外开放的小房间。 有人还记得,那年她拿到一幅画,背面写着一句话——内容没人记得清,只记得那纸泛黄,落款不是齐白石,而是个简单的“石”字。她把画收进箱子,从不示人。 有一次朋友来家,她搬出一大箱剧服,无意中露出那卷画,只一眼,就被收了回去。朋友笑着问,她没解释,只说一句:“这画不能卖。” 后来两人见面少了。齐白石身体大不如前,出门也得靠人搀扶。新凤霞忙着成家立业,评剧改编、排新戏、带学生,连夜里也不歇。 有次采访,她被问到齐白石对她影响,她只说:“他是个很认真的人。”记者追问别的,她摆手,不说了。 那张立柜照片流传多年,有版本说拍摄那天正是1952年,有人还记得,柜子上放着一本旧账本,红纸封面,角落写着“凤”字,墨迹未干。 谁也不知道,那年那柜子的钱,最后去哪儿。有人说她一分没拿,有人说她拿了其中一叠,用来做演出资金。 也有人说,那柜子后来被老人的家属锁了,再没开过。说法不少,真真假假,但那一幕始终像一幅未完的画,留在人们脑海里。 一老一少,一个画尽春秋,一个唱尽人生。那间屋子,那扇柜门,那些钱,那些眼神,全藏进了历史的褶皱里,不再被翻动。 只留下几张泛黄的照片,几幅署名的画,还有评剧舞台上,一个人一出戏,唱出几十年都不肯改的腔调。

![完了,全都会,我也被韩流影响了[哭哭]](http://image.uczzd.cn/13425078599971931367.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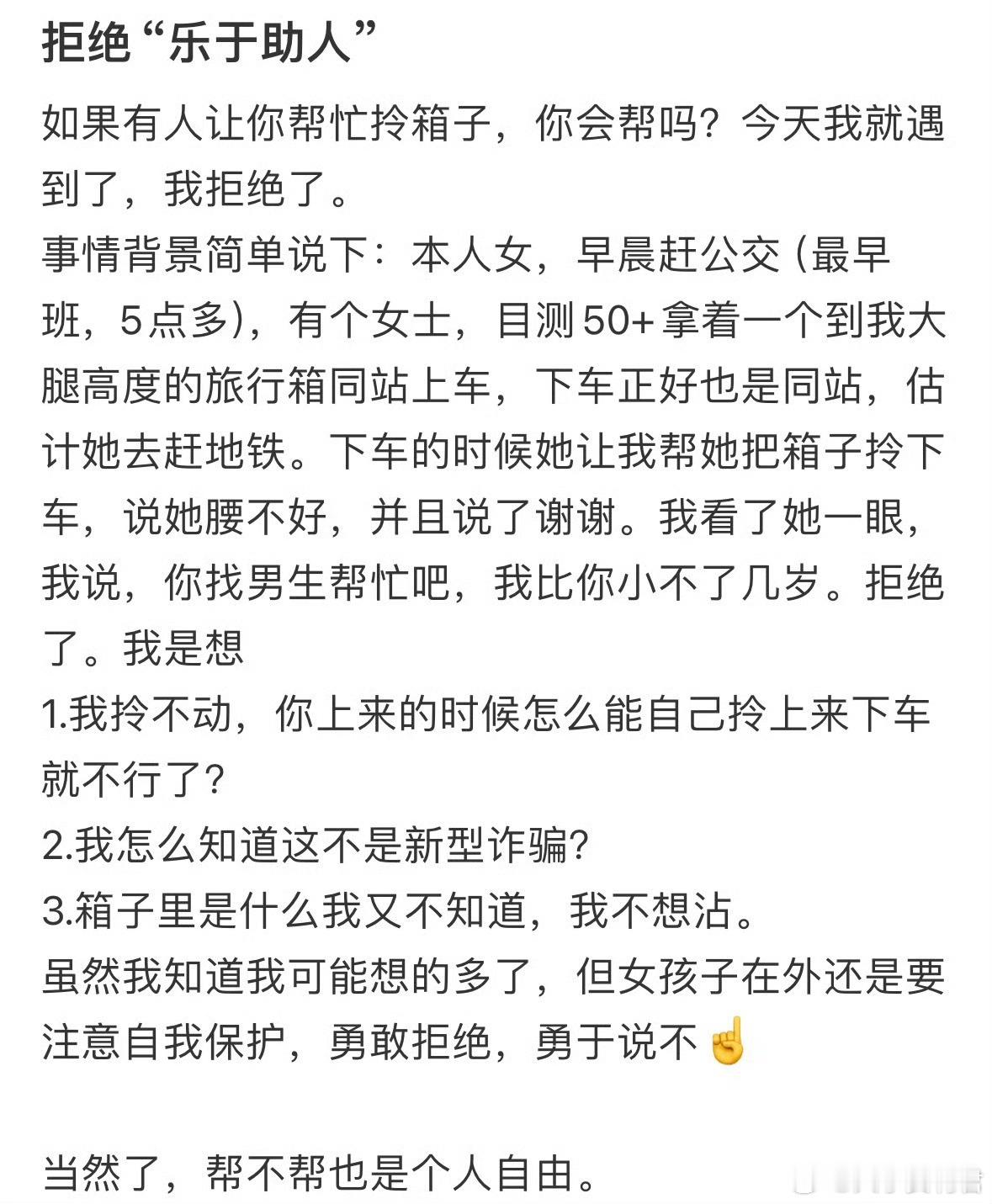
![莎莎,咱能不犯迷糊吗?[捂脸哭]阿三的饭是一坨一坨的,方便用手抓着吃。不过,给其](http://image.uczzd.cn/14413853472154123065.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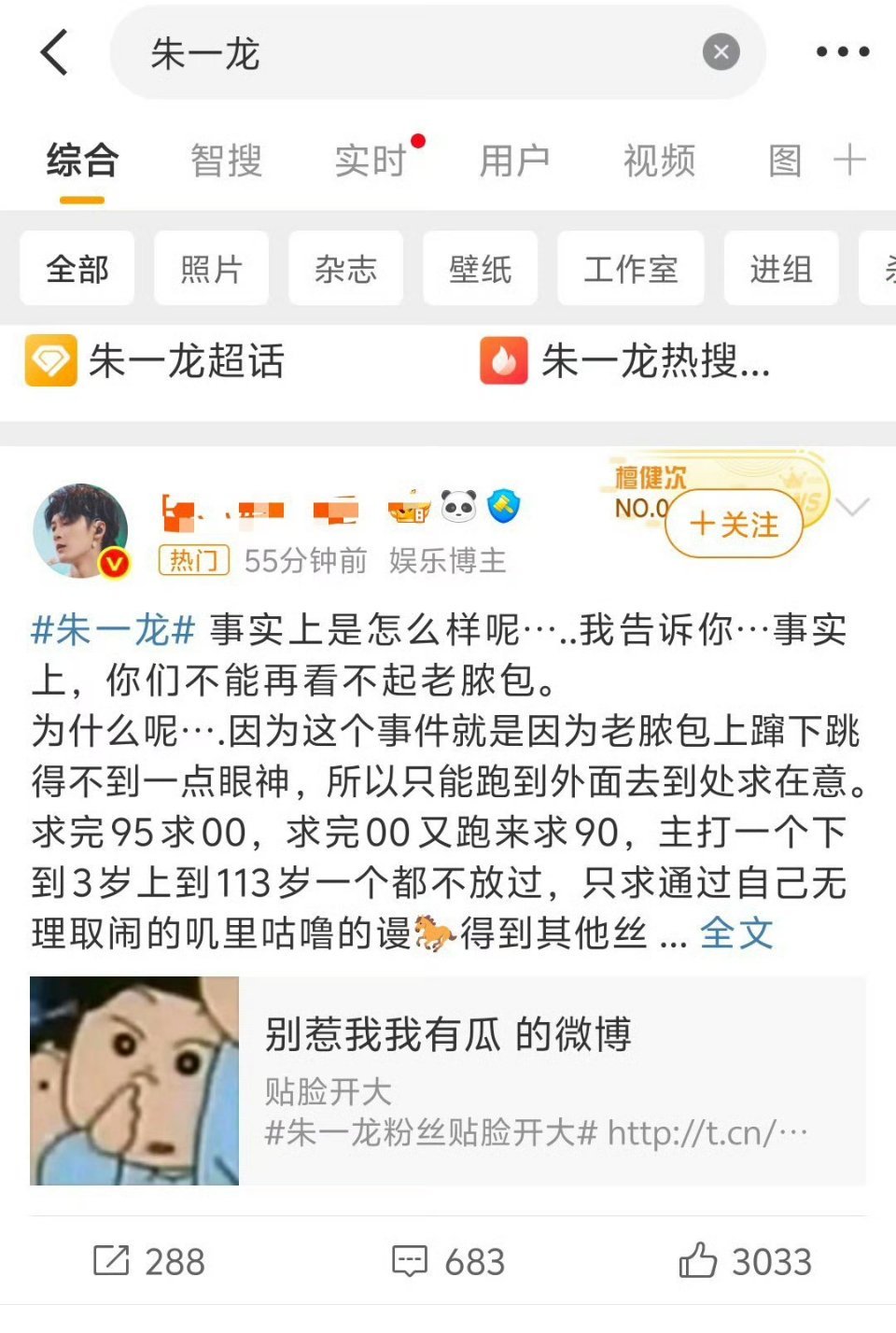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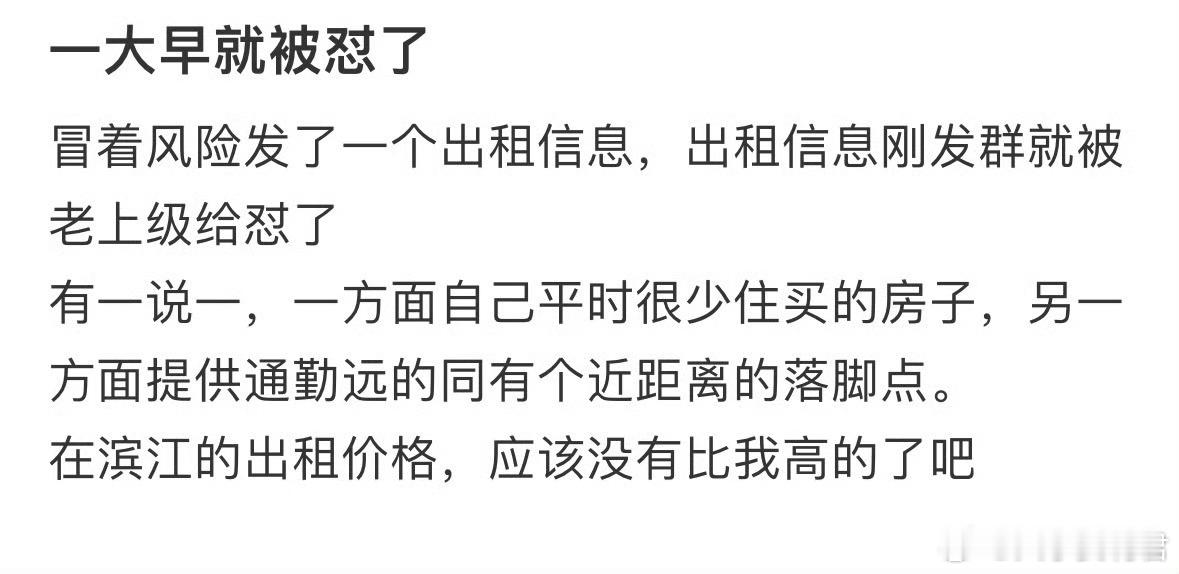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尿[doge]](http://image.uczzd.cn/13686550403384031096.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