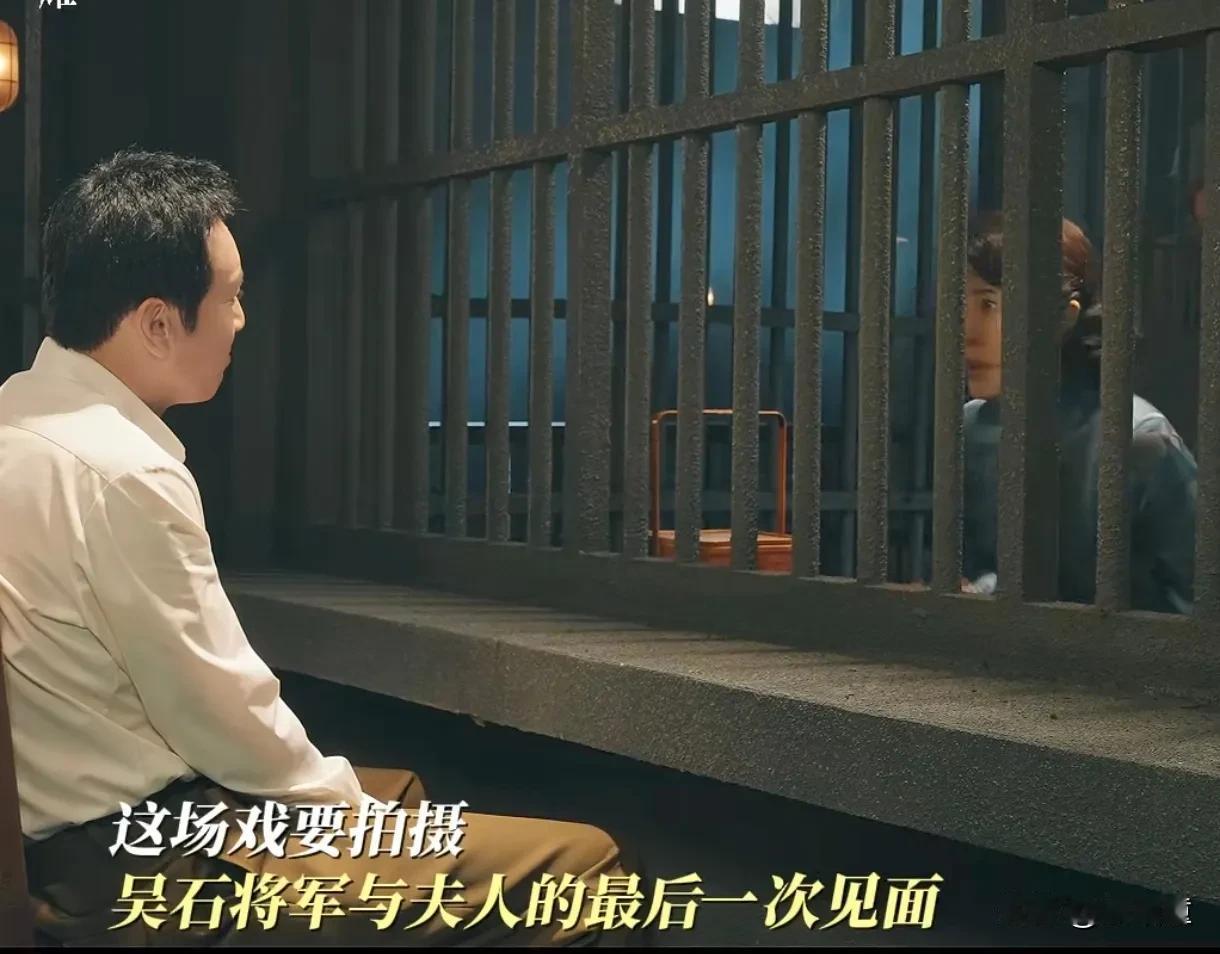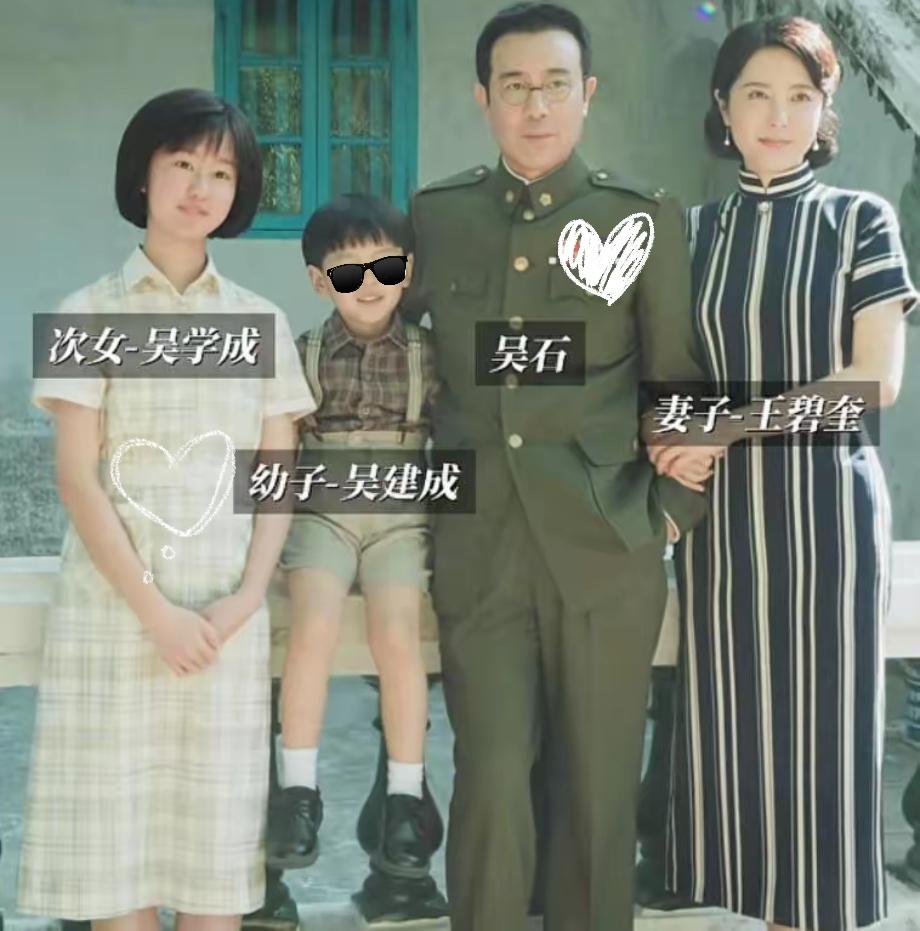1975年,12岁的刘玉璞正在洗澡,醉醺醺地父亲发疯般地踹开门,冲进浴室里,死死拽住她的头发,对她拳打脚踢。事后,又亲吻着刘玉璞的伤痕,对她说“以后洗澡,都不要锁门!” 12岁那年,她在浴室里被父亲一脚踹开门的那一刻,大概就明白了,“家”这个词,不是港湾,是围栏。 没有人会来拉她一把,甚至门外那个走得很轻的女人,她的母亲,也没有停下来问一句“怎么了”,从那天起,她学会了一个词:闭嘴。 1984年,电视上那个灵气逼人、眼神里满是锋芒的赵敏,是刘玉璞,可你不知道的是,那个角色她演得太好,不是因为演技,而是命中注定。 刘玉璞早熟得惊人,18岁那年,有星探在街头看见她,说她有镜头感,她答应得很快,因为她知道,这是逃出去的唯一机会,她不是为了红,是为了活。 别人怕吃苦,刘玉璞不怕,替身不来,她自己上;打戏太猛,她照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甚至吐过血,但她从不喊疼。 因为她早就把疼当成日常,比起父亲的拳头、母亲的冷眼、丈夫的控制,这些真不算什么。 镜头关了,她常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发呆,那时候她红极一时,金庸都说她是“最贴近原著的赵敏”。 可赵敏敢爱敢恨,她却连“爱”这个字都不敢轻易说出口。她怕,爱上谁,谁就会变成父亲。 后来刘玉璞遇到了张建中,一个教堂里的牧师,温文尔雅,听她倾诉,不打骂她,还说她值得被爱,她信了,22岁时她嫁了他,放弃了演艺圈,放弃了自由,换来一个看似安稳的“家”。 但第二个牢笼,比第一个更难挣脱。 婚后,张建中变了,他不再温柔,他开始控制刘玉璞,从穿什么衣服、走哪条路,到能不能出门见朋友,他说:“你是牧师的妻子,要有样子。” “样子”,成了刘玉璞被绳索捆住的借口,她想求医,说自己精神不太对劲,他冷笑:“你要让教会蒙羞?” 她回娘家试图求助,母亲说:“你少拿死来威胁人。”父亲更干脆,直接动手,她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出口,都被关上了。 绝望成了她的日常,她多次自杀,最严重那次,她吞了上百颗药,走向海边,警察发现了她,她被救回来了,但她哭着对朋友说:“我是真的病了”不是矫情,不是作,是病了。 可没人把她的痛苦当回事,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她的社会角色,都只希望她“正常”,希望她“识大体”,希望她“不要丢人”。 2007年,她终于决定离婚,没有财产,没有孩子,净身出户,她提着行李回娘家,门还没开,就挨了一顿打。 刘玉璞以为自己长大了,能反抗了,结果她错了,在原生家庭面前,年龄从来不算数,她那时候账户里只剩87块钱。 87块,换不来尊严,也买不起未来,但她还是咬牙活着,靠着教画画、写书、接小角色,她撑了下来。 她写书,是为了告诉别人:抑郁症不是“想开点就好”的事,她说:“我试过了,我真的试过了。”她的书《打开心飞》里,满是求生的痕迹,她不是不想活下去,只是太累了。 2009年母亲节,她主动打电话给母亲,聊了很多往事,还寄了一幅画过去,那是她最后一次试图修复关系,她还是没能彻底放下这个家,哪怕它一次次让她失望。 几天后,她因心脏病突发离世,没人知道她走了,直到三天后朋友报警,床边是没吃完的抗抑郁药,还有一本密密麻麻记录药物反应的日记。 她是认真地在跟病拼命,只是没人陪她一起抗,刘玉璞不是输给了命运,是被命运耗光了力气。 从浴室到镜头,从教堂到病房,她一生都在逃:逃离父亲的拳头、母亲的沉默、丈夫的控制、社会的偏见,甚至逃离她自己。 她的人生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不是为了赢,是为了不死。 她演过最成功的角色,是赵敏,可赵敏能策马江湖,她却连锁上浴室门的权利都没有,她曾经那么努力地想成为一个“正常人”,但这个世界从没给她“正常”的起点。 她在书里写:“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会爱我。”这不是悲伤,是结论,是她被一次次推开的手、一次次冷漠的眼神、一次次不被理解的病痛,推出来的结论。 不能疯、不能懦弱、不能喊疼,连痛苦都得藏着掖着,还不能影响别人,你活着要有用,不然就别活。 但刘玉璞已经很“有用”了,她美,她红,她拼命工作,她隐忍,她配合,她甚至连病都不敢被人知道,可最后,她还是孤零零地死在了公寓里,三天后才被人发现。 有研究说,人在童年时期受到的心理创伤,会改变大脑结构,这不是玄学,是科学,父亲的一脚、母亲的沉默,不会随着时间淡去,而是变成在你心里反复播放的监控录像。 你越想忘,它越清晰,我们总说“家是最安全的地方”,可对很多人来说,家是第一个让他们想死的地方。 刘玉璞没有等到“被理解”的那天,心理创伤不是软弱,而是病;原生家庭不是私事,而是社会议题;女性不是“该忍”,而是“该活”。 愿每个孩子都能锁上浴室的门,愿每个成年人都不用再演赵敏,愿这个世界,少一个刘玉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