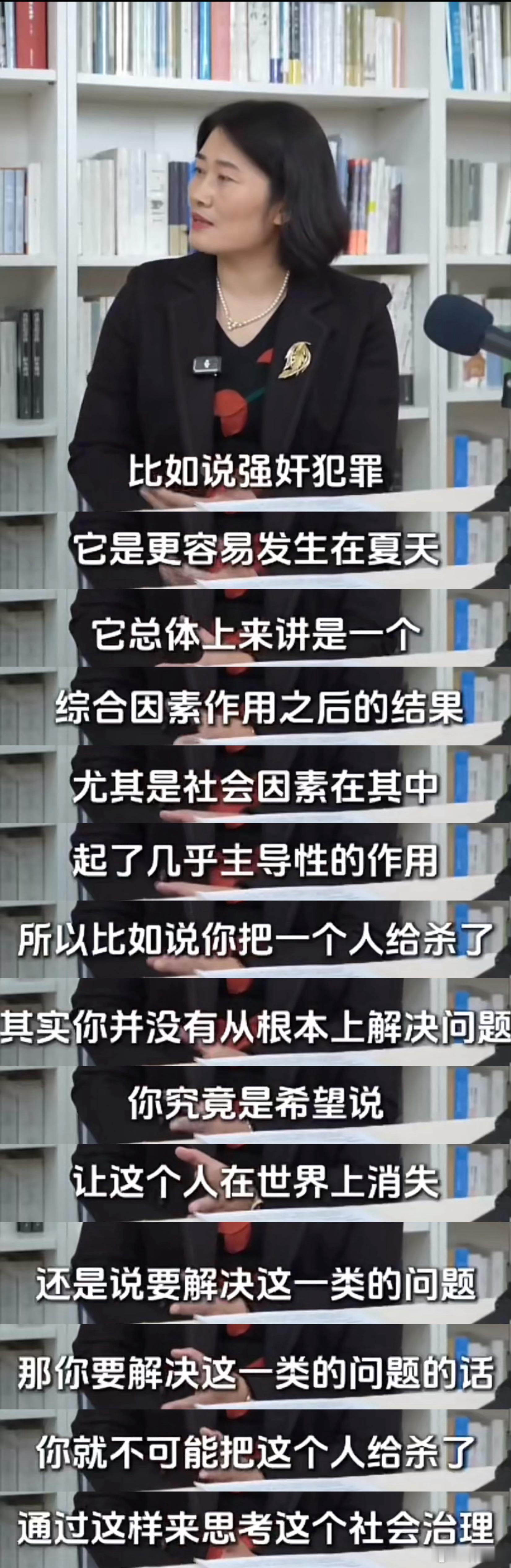1997年,士兵江国庆强奸女童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十四年后,真正的凶手落网,法院却判真凶无罪当庭释放。 江国庆含冤被枪决27年,真凶脱罪,维权者只剩白发老妪。 没有正义昭雪的圆满,只有一个家庭耗尽半生,却求而不得的公道。 年过八旬的江母,依旧背着沉甸甸的冤情材料,走在维权路上。 她的脊背早已佝偻,脚步蹒跚,却每一步都踏得格外坚定。 没人知道,这个瘦弱的老人,曾为了替儿子洗冤,数次直面死亡威胁。 有一次,她在台空军司令部门口讨说法,被不明人士强行拖拽。 对方威逼利诱,让她放弃维权,否则就对她不客气,她却宁死不从。 她死死抱住大门的栏杆,嘶吼着“我儿无罪”,直到被保安强行拉开。 回家后,她浑身是伤,却第一时间整理好被扯烂的冤情材料。 这样的恐吓,在她27年的维权路上,早已是家常便饭。 可她从未退缩,哪怕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梦见儿子满身是血的模样。 时间拉回2013年,那场让所有人心寒的二审判决,击碎了江家最后的希望。 台高等法院当庭宣判许荣洲无罪释放,理由荒诞得让人无法接受。 “轻度智能不足、自白矛盾”,轻飘飘的几个字,就抹去了一条冤死的人命。 更让人愤怒的是,当年对江国庆实施逼供的八名军官,竟全身而退。 他们以追诉期已过为由被不起诉,甚至公开否认逼供,毫无愧疚之心。 江母拿着判决书,在法院门口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哭声嘶哑却无力。 她想不通,铁证如山的案件,为何会变成这样荒诞的结局。 没人记得,2011年那个秋天,江母曾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正义。 台军事法院再审,判决江国庆无罪,还给了她一亿多新台币的赔偿金。 可她拿到赔偿金的第一时间,没有花一分,全部用来继续维权。 她要的从来不是钱,是真凶伏法,是逼供者受惩,是给儿子一个交代。 这份执念,要从1997年那个让她痛不欲生的日子说起。 那天,她接到军方电话,被告知儿子江国庆因强奸杀人,被执行枪决。 她当场晕厥过去,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她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老家,孤身前往台北,开启了漫漫维权路。 起初,她连相关部门的大门都进不去,只能在门口蹲守。 她学会了写冤情信,一笔一画,写满了儿子的冤屈和自己的渴求。 她把信塞给每一个愿意停下脚步的人,哪怕大多时候会被随手扔掉。 丈夫江支安后来也赶来台北,夫妻俩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他们每天吃着最便宜的泡面,省下钱来复印冤情材料、请人代写诉状。 为了寻找新的证据,他们走遍了当年案发的营区周边,走访了上百人。 有一位当年的营区老人,被他们打动,悄悄告诉他们许荣洲的异常。 老人说,案发后不久,许荣洲就变得异常沉默,还常常做噩梦。 这个线索,成了他们维权路上的一束光,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信心。 可他们没想到,这份线索递上去后,依旧石沉大海,无人理睬。 长期的奔波和绝望,压垮了江支安,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他常常走失,每次找到他时,他都在街头哭喊着儿子的名字。 江母一边照顾丈夫,一边继续维权,日子过得暗无天日。 2010年,江支安在绝望中离世,临终前,他还攥着儿子的照片不肯松手。 丈夫的离去,让江母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却也让她愈发坚韧。 同年,台“监察院”的调查结果出来,认定军方当年非法取供。 专案小组重新检测证物,发现案发现场的掌纹和血迹,都指向许荣洲。 2011年,许荣洲被传唤,面对铁证,终于再次承认自己是真凶。 江母以为,儿子的冤屈终于可以洗清,公道终于可以到来。 可她万万没想到,两年后的二审判决,会给她致命一击。 如今,又是十几年过去,江母已经80多岁,身体大不如前。 她的眼睛花了,耳朵也背了,却依旧能清晰说出儿子的冤情。 出租屋里,摆满了厚厚的维权材料,还有儿子的军装和照片。 她每天都会擦拭这些东西,轻声和儿子说话,诉说自己的坚持。 她依旧会定期去相关部门递交材料,哪怕工作人员早已认识她。 许荣洲早已回归正常生活,那些逼供的军官,也依旧安然无恙。 只有江母,还在执着地坚守着,守着一份遥不可及的公道。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久,却始终没有放弃的念头。 这场跨越27年的维权之战,没有终点,只有一个老母亲无尽的悲凉与坚守。 信源:百度百科 江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