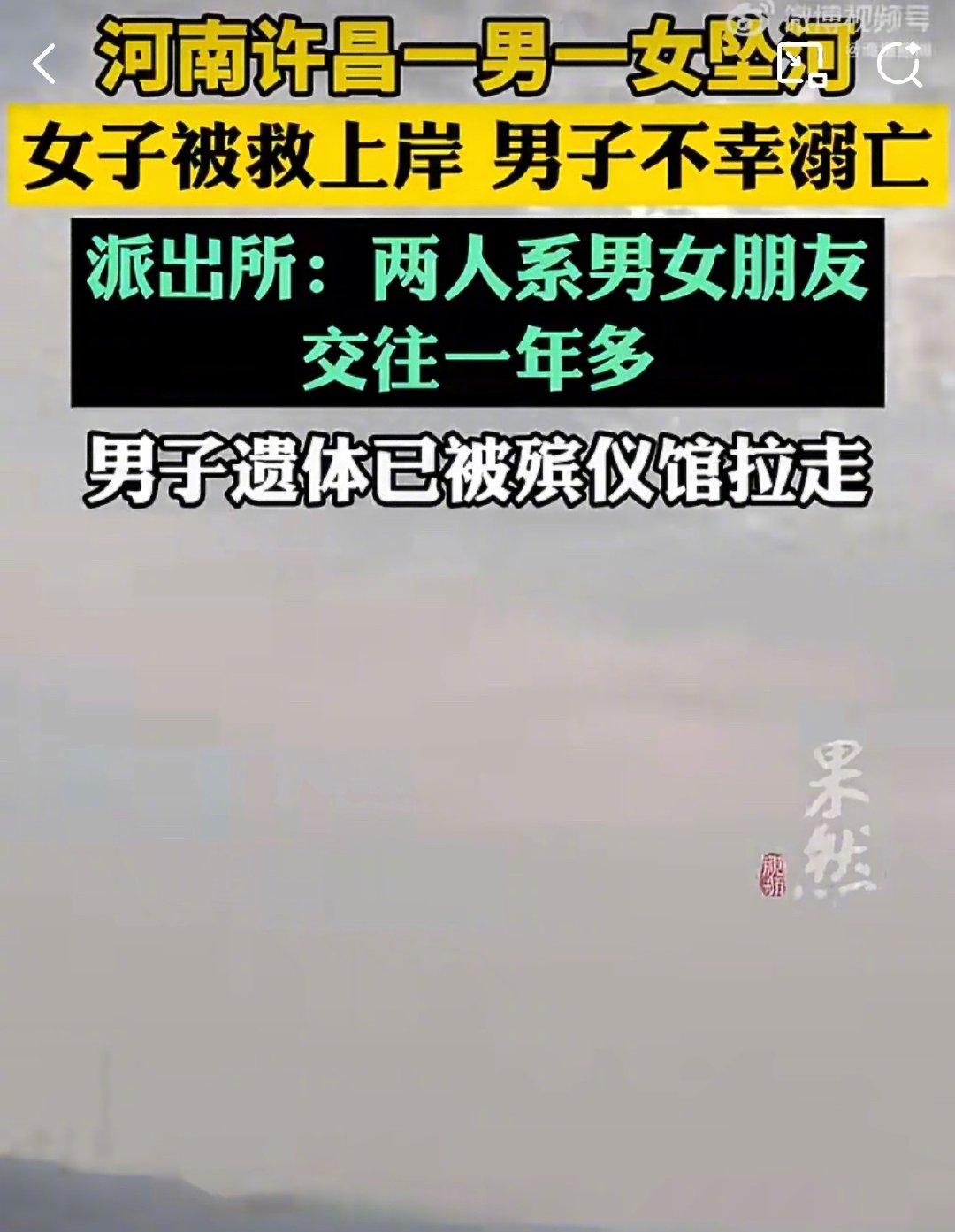1988年,武汉女教师在医院生下一个小男孩。谁知,丈夫突然在她耳边说:“老婆,把氧气管拔掉吧,我们还能再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女教师脸色大变,怒斥道:“我真后悔嫁给你!” 1988年,在武汉市妇幼保健院里,邹翃燕躺在产床上,宫缩的剧痛让她眼前阵阵发黑。 护士急促的脚步声里,一声微弱啼哭终于响起。 护士抱着襁褓凑近:“恭喜啊邹老师,是个男孩!” 邹翃燕勉强睁眼,却在看清婴儿面色青紫的刹那,心头猛地一沉。 “宫内窒息超过十分钟,”主治医师摘下口罩,“重度窒息,就算救回来……大概率脑瘫或者智力缺陷。” 病房陷入死寂。 角落里一直沉默的男人突然扑到床边:“老婆,拔了吧……我们还年轻,再生个健康的……” 邹翃燕一把推开丈夫的手,抓起枕头狠狠砸过去:“你再说一遍试试?我真后悔嫁了你这种畜 生!” 在监护仪尖锐的警报声中,她死死盯着保温箱里那个脆弱的小生命。 丈夫摔门离去时丢下的话还在耳边嗡嗡作响:“那你一个人养!拖累全家算什么本事!” 接下来的三个月,邹翃燕的世界只剩医院走廊惨白的灯光。 护士递来第五张病危通知书:“邹老师,实在不行……” “签字!” 邹翃燕抓过笔手抖的签下字,“我儿子阎王爷都带不走!” 当丁丁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回到家中,这个襁褓里的婴儿轻得像片羽毛。 邹翃燕的工资刚过百元,奶粉钱都得掰着指头省。 邻居们摇头叹息:“瘫子娃娃就是烧钱的祖宗。” 她白天教书,晚上抱着丁丁做康复训练。 孩子身子软绵绵的,连最简单的抬头都做不到。 亲戚劝她:“送去福利院吧,别耽误你自己。” “我儿子听得懂话!” 邹翃燕把儿子贴在耳边,指着识字卡片一字一顿,“丁丁,这是‘妈’字,跟着念!” 三个月后的深夜,奇迹悄然降临。 当她哼唱摇篮曲时,丁丁突然转动眼珠追着她的手指移动。 邹翃燕冲向医院,检查结果却让她嚎啕大哭:“智力正常!他听懂了!” 希望的曙光刚冒头,更大的阴影笼罩而来。 一岁多的丁丁依然瘫软如泥,连勺子都握不住。 康复科主任告诉她:“脑瘫导致运动神经损伤,三岁前不介入高强度康复,这辈子别想站起来。” “怎么治?” “‘揪皮疗法’。” 主任比划着,“徒手揪捏拉伸皮肤和肌肉,每次半小时,隔天一次。” 诊室外的走廊上,邹翃燕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撕心裂肺哭喊,双腿灌了铅似的挪不动步。 回到家翻开存折,工资107块,一次训练费5块。 “砸锅卖铁也得治!” 第一次治疗时,五六个康复师按住丁丁四肢。 当粗糙的手指狠狠揪起他细嫩的皮肤,小家伙的哭声像被踩住脖子的幼猫。 “妈妈,疼……”丁丁挂着泪珠的小脸仰起,伸出小手要抱。 “丁丁乖,再忍忍。” 三年间,她身兼三份家教,凌晨两点还在改作文。 1994年初春的清晨,厨房飘来米香。 邹翃燕切菜时,突然听见卧室传来“咚”的一声闷响。 冲进去的瞬间,她呼吸骤停,丁丁正手脚并用扒着床沿。 “妈…妈!”他扭头朝她咧嘴笑,口水顺着下巴滴在床单上。 邹翃燕的眼泪“唰”地涌出来。 她哆嗦着扶住儿子,感觉怀里的小身板不再是棉花,而是有骨有肉的生命。 那天起,丁丁开始了地狱式特训。 学步车被他摔得散架,膝盖结满血痂。 有次在小区摔倒,他趴在地上哭到喘不上气:“不学了…再也不学了…” 邹翃燕蹲在儿子面前,掏出珍藏的水果糖:“还记得热干面不?你答应过要带妈去吃的。” 丁丁抽着鼻子拼命点头。 当丁丁摇摇晃晃迈出独立第一步时,邹翃燕的影子在朝阳下拉得老长。 那双磨穿血泡的脚丫,正踏碎十九年阴霾。 2007年7月,邮递员按响门铃。 丁丁从快递员手中接过牛皮纸信封,手指抚过“北京大学”四个烫金大字时,突然腿一软跪在地上。 “妈!我考上了!真的考上了!” 邹翃燕捧着那张印着校徽的通知书,十九年前保温箱里那个青紫的婴儿,此刻正用清亮的眼睛望着她:“妈,我能自己去北京上学了。” “傻小子,”她笑着捶儿子肩膀,“妈等你这句话等了十九年。” 如今的丁丁,已是哈佛法学院博士生。 去年回国探亲时,他特意去了趟妇幼保健院。 丁丁在邹翃燕当年站过的走廊尽头停下脚步说:“妈,当年要是听了那个人……” “哪有那么多要是。” 邹翃燕挽住儿子胳膊,“你活着,就是最好的答案。” 当世俗认定该放手时,总有人愿意押上性命赌一场。 因为有些火种,宁可烧穿掌心也要护住它燎原。 所谓奇迹,不过是凡人把“不可能”三个字,嚼碎了咽下去,再从骨头缝里长出翅膀。 主要信源:(潮新闻客户端——从“脑瘫”到哈佛:邹翃燕做客“王金海聊家庭教育”直播间倾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