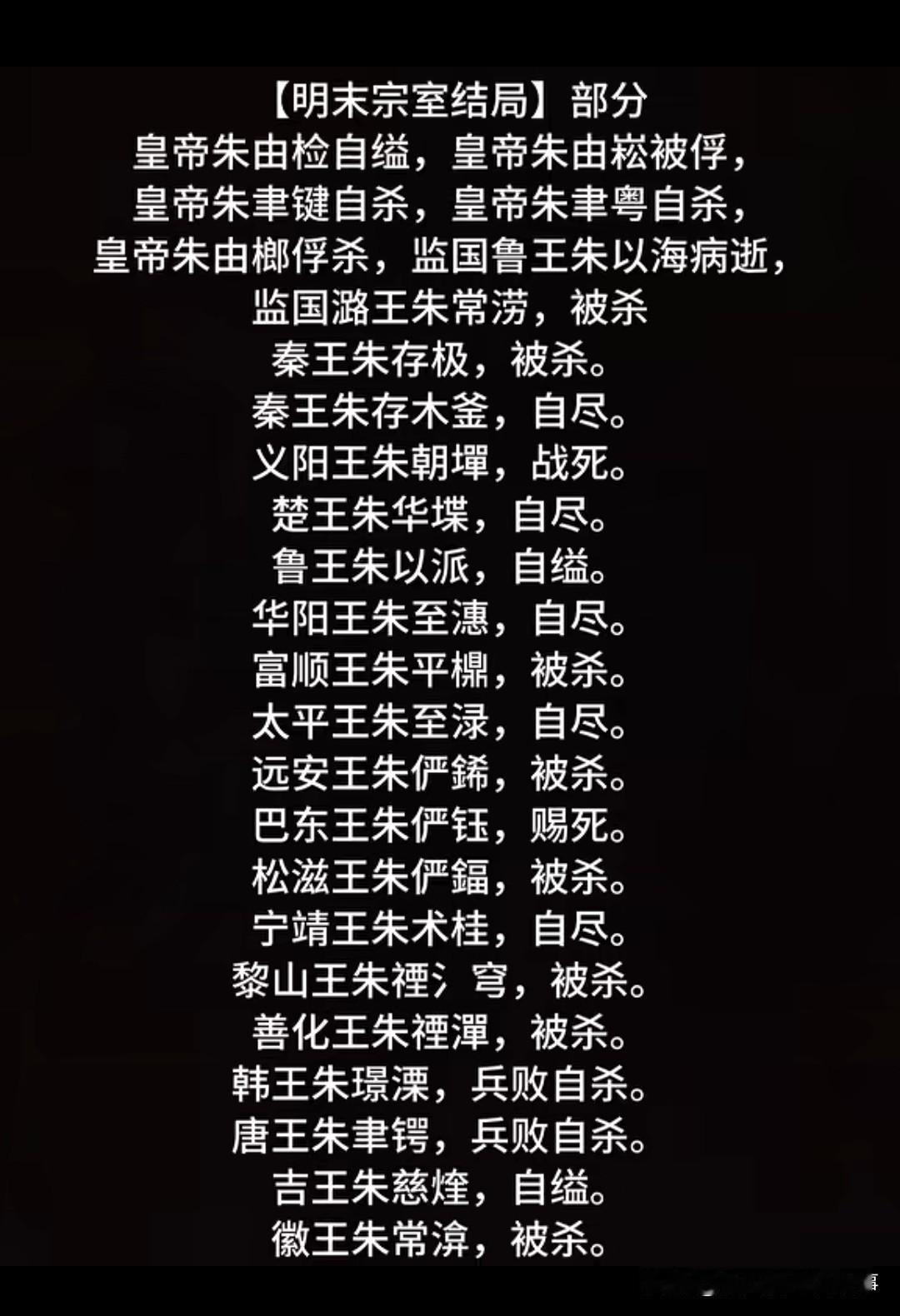洪武二十年秋,在外当了二十年差的锦衣卫副指挥使陈二虎,解甲归田,回老家凤阳来了。 老管家陈福远远看见人影就迎上去,接过马缰绳,眼泪一下就出来了:“二爷,您可算回来了!” 走到家门口,陈二虎脚步顿了顿。老宅还是那扇黑漆大门,颜色都斑驳了。可不对劲的是,东边一半的院墙明显是后砌的,用的全是新砖,墙头愣是比自家这边高出了半尺。门楣上那块“陈宅”的匾额倒还在,只是漆色更黯淡了。 陈福看他目光停在那儿,嘴唇哆嗦着,抢上前就要说话。陈二虎脸上没什么表情,只“嗯”了一声,推开了自家这边吱呀作响的院门。院子里落叶满地,厢房的窗户纸破了好些洞,一股子破败气。 陈福跟在后头,嘴里絮絮叨叨,说占宅子的人叫张旺霸,在乡里如何横行,放高利贷逼得人家破人亡,占了东跨院都十年了,愣是没人敢惹。 “知道了。”陈二虎打断他,把简单的行李放在堂屋积了灰的桌子上,“东跨院,现在谁住着?” “张旺霸把他一个外室和小崽子安排在那儿,他自己偶尔过来。”陈福恨得牙痒痒,“二爷,您如今回来了,可得好好整治这厮……” 陈二虎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口气平淡:“福伯,收拾间能住的屋子出来。东跨院那边,他们爱住,就先住着。” 陈福一听,愣住了,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二爷!这怎么行?那是咱家的祖产啊!” 陈二虎走到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天色,“我累了,先歇歇。对了,明天你去趟县里,买些香烛纸钱回来。” 陈福一肚子憋屈和疑惑,但看着二爷那副平静的样子,也不敢再多问,只得唉声叹气地去收拾了。 接下来几天,陈二虎深居简出。除了让陈福去买祭品,就是偶尔在自家破败的院子里转转,修剪一下荒草,或者坐在堂屋里静静喝茶。对隔壁东跨院的动静,他好像完全没听见。那边倒是知道正主儿回来了,头两天还消停点,后来见这边没反应,又开始有说笑声和孩子的跑闹声传过来。 陈福急得嘴上起泡,陈二虎却像没事人一样。 第五天一大早,陈宅那扇破旧的大门就被拍得山响。陈福心惊胆战地去开门,门一开,他惊呆了。 门外黑压压跪了一片人!为首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正是恶霸张旺霸。他此刻脸上半点横气都没有,只有满满的恐惧,手里哆哆嗦嗦捧着一个红木托盘,上面堆着些玉器、瓷瓶、房契地契。 “陈大人!小人有眼无珠!猪油蒙了心!占了您老人家的宅子!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啊!”张旺霸一边哭喊,一边左右开弓,啪啪地扇自己耳光,“东西全在这儿,一件不少!求陈爷开恩!饶小人一家狗命吧!” 他身后一家老小也跟着哭嚎,场面“壮观”极了。 陈二虎这才从后面慢慢踱出来,站在门槛里面,看着门外这一大片跪着的人。他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既没有得意,也没有愤怒。目光扫过张旺霸手里的托盘,又扫过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脸,停了片刻,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让门外的哭嚎声瞬间低了下去: “宅子收拾干净,东西归位。以后,别让我在凤阳再看见你。” 张旺霸如蒙大赦,磕头磕得更响了:“谢陈爷开恩!谢陈爷开恩!小人这就滚!滚得远远的!”说完,连滚带爬地起来,带着一家子,眨眼功夫就跑没影了,比来时还快。 陈二虎转身往院里走,吩咐道:“福伯,把东西收好,找人把东墙拆了,恢复原样。” 陈福到现在还云里雾里,忍不住问:“二爷,这……您是怎么……” 陈二虎停下脚步,回头看了老管家一眼,淡淡地说:“我回来的第二天,让人给知府递了张名帖,只说了一句,‘陈家祭祖,图个清静’。” 陈福恍然大悟。原来二爷根本不用自己动手。他只要让本地的父母官知道,当年在御前行走、执掌诏狱的锦衣卫副指挥使陈二虎,回来了,要祭祖了。剩下的事,自然会有人去办。那张旺霸横行乡里,屁股底下能干净吗?知府大人正愁没机会在新归乡的这位“陈大人”面前表现呢,查他点罪状,敲打敲打,还不是轻而易举?这才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陈二虎看着老管家了然的神情,补了一句,声音依旧平淡:“跟这种人动刀动枪,跌份儿。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有些人的威风,需要喊出来;而有些人的威严,只要他站在那里,就足够了。陈二虎用五天时间,给老家的“江湖”,好好上了一课。
乾隆二十二年,康熙帝97岁的定妃去世。她一生仅被康熙帝宠幸过一次,却凭着这次偶然
【3评论】【28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