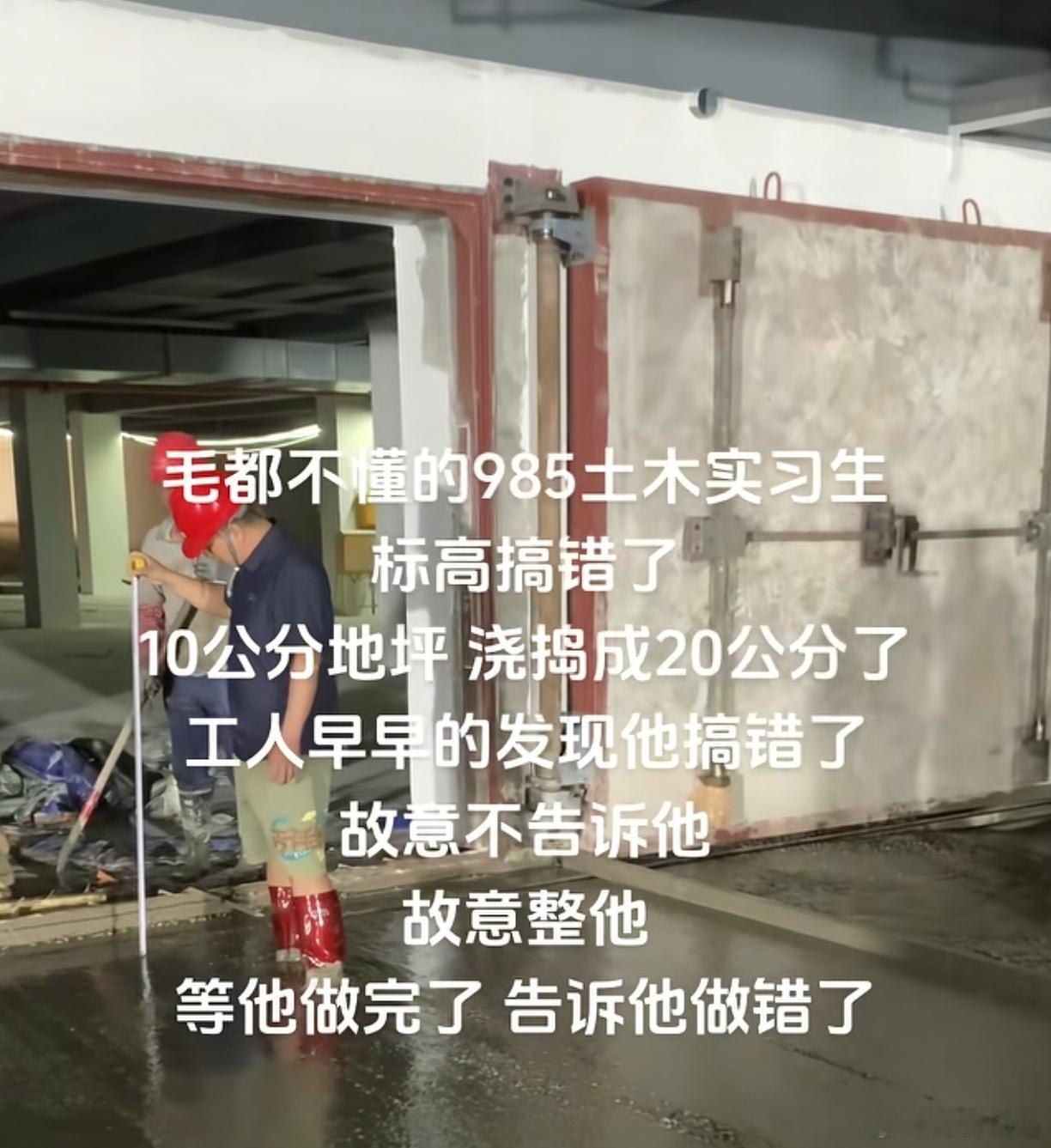我这辈子最该记着的人,是陈姐。那年我十七,在工地搬砖,为了多挣两块钱,抢着去卸三楼的槽钢。绳子磨断的时候,我整个人跟着往下坠,风灌进喉咙,脑子里一片空白,以为这辈子就交代在这了。是陈姐,那个在工地项目部管财务的女人,扔了手里的账本,踩着高跟鞋扑过来拽住了我的胳膊。她的力气大得吓人,指甲嵌进我皮肉里,喊得嗓子都劈了。后来工友们赶过来,七手八脚把我拉上去,她瘫在地上,白着脸,半天说不出话,额前的碎发被冷汗打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我胳膊擦破了一大片,血混着灰往下淌。她带我去项目部的休息室,翻出红药水和纱布,仔仔细细地涂,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我。她比我大十岁,穿素色的衬衫和直筒裙,眉眼清亮,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弯出一点好看的弧度。“以后小心点,”她说,“命比钱金贵。”那天她留我吃了碗面,卧了两个鸡蛋。汤是骨汤熬的,鲜得很,我吃得鼻尖冒汗,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家穷,爹妈顾不上我,长到十七岁,没人跟我说过这样软和的话。我想报答她,可我身无分文。只能每天收工后,绕到项目部楼下,帮她擦干净那辆半旧的自行车,把她窗台上的绿萝浇得水灵灵的。她总说不用,脸上却笑着,隔三差五会给我带个馒头,或者塞袋咸菜。工地的人嚼舌根,说我是她的小跟班,说她一个城里来的漂亮女人,心肠未免太软。她听见了,也不恼,只说:“这孩子心善。”三个月后,我爹捎信来,让我回家当兵。走的那天,她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五百块钱,还有一双她纳的布鞋。鞋面是藏青色的,纳得密密实实。“到了部队好好干,”她拍着我的肩,掌心温温的,“别惦记家里,也别惦记我。”我攥着布包,眼泪掉在布鞋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我跟她说,等我混出个人样,一定回来报答她。她笑着摆手,让我快上车。车子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她站在路边,穿一件杏色的风衣,风吹起她的长发,像一幅淡墨的画,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部队的日子苦,我咬着牙熬。训练受伤的时候,我就摸出那双布鞋,想起她的话,又觉得浑身是劲。我立了功,转了士官,工资慢慢涨起来。我给她写过几封信,地址是工地的,却都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查无此人”。工地早就拆了,盖起了高楼,她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我找了她很多年,问遍了当年的工友,都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时间长了,那点念想被日子磨得淡了些,却从没断过。我退伍,工作,结婚,离婚,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只是偶尔看见纳鞋底的针线,心里会咯噔一下。再次见到陈姐,是在二十年后。那天我去老城区办点事,路过一条窄巷,看见一个女人蹲在墙角,正给几只流浪猫喂猫粮。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头发烫成了卷,有几缕已经花白,可眉眼间,还是当年那股清亮的样子。我多看了两眼,脚步突然顿住。是她。我走过去,声音有点发颤:“陈姐?”她抬头看我,眼神浑浊了一瞬,随即亮起来,愣了半天,才开口:“你是……小勇?”我的眼泪一下就涌了上来。是她,真的是她。她领着我回了家。房子很小,一室一厅,家具都很旧,却收拾得一尘不染。客厅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她年轻时的照片,穿白衬衫,站在工地的梧桐树下,笑靥如花。她说,当年工地散了,她跟一个搞工程的男人走了,那人说会娶她,她信了,跟着他天南地北地跑,最后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他众多女人里的一个。男人的老婆找上门闹过几次,闹得人尽皆知,她被赶了出来,身无分文,最后辗转到了这里,买了这套小房子,从此再没见过那个人。“我当了半辈子小三,”她笑了笑,笑得有点苦,“让人戳脊梁骨,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我没说话,只是帮她把散落在桌上的药瓶归拢好。她的身体不好,风湿,腰也疼,走路都有点不利索。那天我留了下来,帮她换了耷拉下来的窗帘,修好了吱呀响的木门合页,又去菜市场买了菜,给她做了顿像样的饭。她坐在桌边,看着我忙前忙后,眼睛里亮晶晶的,像藏着星星。吃完饭,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打开来,是那双布鞋。鞋面已经泛黄,鞋底却还是结实的。“当年想着,你是个好孩子,就盼着你能有个好前程。”她摩挲着鞋面,声音很轻,像怕惊了什么。我心里发酸,说:“陈姐,我找了你好多年。”她没接话,只是抬头看我,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像一汪深水。后来我就住了下来。我没地方去,离婚后房子判给了前妻,手里的钱也不多,陈姐的小房子虽挤,却让我有了落脚的地方。我每天买菜做饭,把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帮她揉腰泡脚,将她攒了许久的衣物洗得干干净净。她的话慢慢多了起来,跟我说当年工地的事,说她算账时的仔细,说她纳布鞋的时候,扎破了好几次手指。小区里的人开始说闲话,说我是她的老相好,说我图她的房子。她听见了,气得发抖,要去找人理论,我拉住她,说:“别去,嘴长在别人身上,随他们说。”她看着我,突然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干,布满了皱纹,攥得我有点疼。“小勇,”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报恩的,可我……”她的话没说完,我却懂了。我轻轻抽回手,给她倒了杯热水。“陈姐,”我说,“在我心里,你一直是我姐。当年要不是你,我早就没了。现在我陪着你,是应该的。”她的手僵在半空,眼神慢慢暗了下去,像燃尽的炭火。她低下头,没再说话,只是拿起桌上的布鞋,一遍一遍地摩挲,指尖的纹路,和布鞋上的针脚缠在一起。日子还是一天天过。我陪着她买菜,陪着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陪着她看咿咿呀呀的老电视剧。她不再提那些话,只是看我的时候,眼神里总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蒙了一层雾。那天阳光很好,金晃晃的,洒在阳台上。楼下的月季开得正好,有风吹过来,带着淡淡的香。她靠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嘴角还带着一点浅浅的笑意。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看着她眼角的皱纹,想起十七岁那年的项目部休息室,想起那碗卧着两个鸡蛋的面,想起她踩着高跟鞋,攥着我的胳膊,喊得嗓子都劈了的样子。有些恩情,不是钱能还的,也不是话能说清的。我只是想陪着她,像当年她陪着我一样。
我这辈子最该记着的人,是陈姐。那年我十七,在工地搬砖,为了多挣两块钱,抢着去卸三
展荣搞笑
2026-01-03 08:57:49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