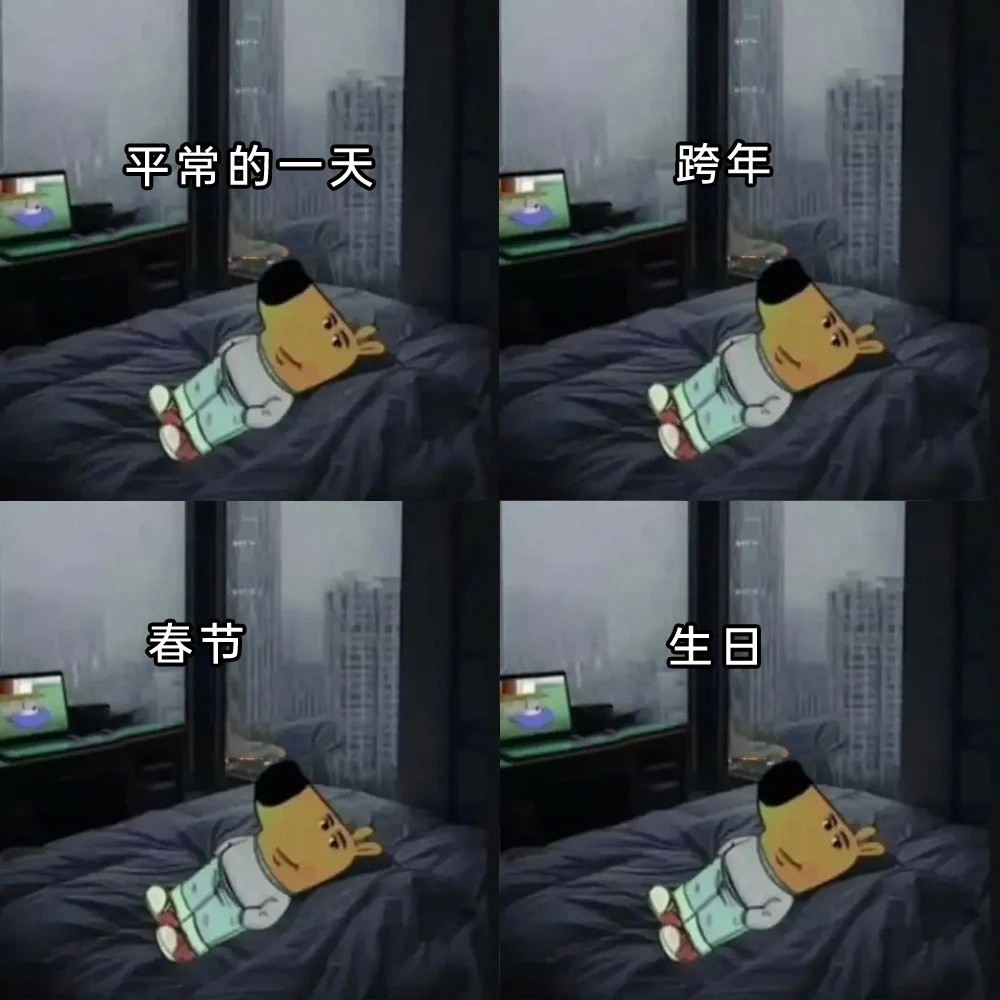我有一个堂哥,他今年七十多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做羊皮生意,挣了不少钱,是我们村中的万元户,是我们村中的首富,大家都很羡慕他。 那会儿他住的还是土坯房,跟别家没两样,只是堂屋墙上挂着个木头框子,里头镶着张县上发的“致富能手”奖状,红绸边都褪成粉的了。 我常看见他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锅子是铜的,擦得锃亮,抽两口就用拇指把烟灰弹在脚边的砖缝里,一声不吭。 娘跟我说:“你哥有钱了咋不显摆?隔壁二柱家刚盖了瓦房,他倒好,还守着这老房子。” 有年夏天我去他家玩,见他趴在炕桌上算账,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账本边角卷得像狗耳朵,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小字,有的地方还用红笔打了勾。 我凑过去问:“哥,你算啥呢?”他赶紧把账本合上,顺手拿过旁边的搪瓷缸子盖住,缸子沿上磕了个豁口,里头的茶水都凉透了。 后来听婶子抱怨,说他挣的钱“见不得光”,有回她想扯块花布做新袄,他掏出钱包数了半天,只给了五块钱,气得婶子哭了半夜。 村里人也有闲话,说“首富抠门”,“挣了钱忘了本”,他听见了也不恼,照样每天扛着杆秤去村口收羊皮,秤砣晃悠晃悠,称完了还得让卖主自己再看一眼刻度。 八六年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一尺厚,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堂哥家灯还亮着,窗户上映着个弯腰的影子。 我溜到窗根下往里瞅,见他正拿刷子刷羊皮,每一张都铺在木板上,顺着毛势刷,刷完了翻过来摸皮子,指腹在肉面上搓来搓去,嘴里还念叨着啥。 突然他咳嗽起来,咳得直不起腰,婶子在里屋骂:“不要命了!冻出病来拿啥看?”他回了句:“这批皮子得赶在年前发走,人家等着做皮衣呢,不能掺一张次的。” 那年开春,村东头的狗蛋考上了中专,家里没钱交学费,狗蛋爹找了好几家借钱都碰了壁,最后硬着头皮去了堂哥家。 我正好在他家借镰刀,听见狗蛋爹在院里搓着手说:“陈哥,你看能不能……”话没说完,堂哥就进了屋,出来时手里攥着个信封,塞给狗蛋爹:“拿着,不够再来找我。” 狗蛋爹千恩万谢地走了,我纳闷问:“哥,你不是没钱给婶子扯布吗?”他摸了摸我的头,没说话,转身又去翻他的账本,红笔在某一页打了个新的勾。 后来我才知道,那账本上的小字,记的根本不是收入支出,而是谁家孩子上学差钱,谁家老人看病缺药,打勾的都是已经帮过的。 有回县上供销社的人来村里,说能弄到便宜羊皮,利润比正经收的高一半,只要掺在好皮子里头卖,看不出来。 堂哥当时正在给羊皮喷水保湿,手里的喷壶“啪嗒”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他指着门口说:“你走吧,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路财。” 那人走的时候骂骂咧咧:“死脑筋!有钱不赚是傻子!”堂哥没接话,蹲在地上捡喷壶,手指被壶嘴划了个口子,血珠滴在羊皮上,红得刺眼。 再后来,市场上假羊皮越来越多,他的真羊皮卖不动,仓库里堆了大半屋,最后只能半价处理,本钱都没回来。 有人说他傻,守着“诚信”当饭吃,他听了就嘿嘿笑:“钱没了能再挣,要是名声臭了,走在村里都得低着头,划不来。” 他不做羊皮生意后,把账本收进了木箱子,上了锁,钥匙挂在裤腰带上,干活的时候叮叮当当作响。 我结婚那年,他来喝喜酒,送了个红包,里面不是钱,是张纸条,写着:“生意做赔了不怕,良心做亏了才怕——你哥记。” 现在我自己开了个小超市,进货的时候总想起他刷羊皮的样子,每回都要拆开包装看保质期,有回供应商说“就差两天没事”,我想起堂哥划出血的手指,摇了摇头把货退了。 上个月回老家,堂哥从箱子里翻出那本旧账本,封皮都快掉了,他戴上老花镜一页页翻,翻到狗蛋那页,红勾旁边又用铅笔写了行小字:“狗蛋现在是医生了,去年给三奶瞧病没收钱。” 他指着那行字笑:“你看,这账记的值不值?钱花出去是流水,人心暖了,能传好远呢。” 我看着他满是皱纹的手,突然明白,当年村里人羡慕他的万元户头衔,其实他真正的“财富”,早就在那本卷了边的账本里——每一笔勾,都勾着一颗热乎的心;每一页纸,都写着“踏实”两个字,比任何奖状都亮堂。
我有一个堂哥,他今年七十多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做羊皮生意,挣了不少钱,是我们村
好小鱼
2025-12-31 18:52:53
0
阅读: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