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甥女打来电话,说她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姐在医院人不行了,让我们去医院看看。我一听着急的不行,赶紧给大姐打电话,让她收拾一下我去接她一起去医院,大姐却说,他去不了,他的孙子要喝中药,只能她看着,别人看着他孙子吃不进去。我说,我的姐姐,你的妹妹要不行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你孙子的中药一顿不喝能有什么大问题?大姐说,不行,一顿不喝,怕孩子的咳嗽再厉害了。我气的骂了娘,可大姐依然固执己见,她说人不行了,就是去看了,人也不能好起来,顺其自然吧,我懒得再跟他啰嗦一个人赶去了医院,还好见到了二姐最后一面。 我打车往医院赶,司机师傅看我手抖,把收音机音量调小了,后座塑料袋里的苹果撞来撞去——出门时顺手从茶几上抓的,二姐以前总说吃苹果比吃药强。 到住院部三楼,刚拐过走廊就听见笑声,我心里咯噔一下,扒着病房门往里瞅,二姐正靠在床头啃梨呢,见我进来就笑:“你外甥女这报丧电话打得,比你小时候偷摘邻居家枣还利索。” 外甥女红着脸递纸巾:“妈非说你们忙,不肯让来,我只好……” “只好编排我快死了是吧?”二姐瞪她一眼,又冲我招手,“过来,让我摸摸,你看你这汗出的,头发都粘脑门上了,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我挨着床边坐下,手被她攥住,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有劲,心里那股火“唰”地就灭了,又有点气:“那你也不能让孩子瞎编啊,我跟大姐都快急疯了!” 二姐叹口气,梨核扔垃圾桶里:“急疯的是你,你大姐才不急呢——她那人,精着呢。” 这话我爱听才怪,刚想反驳,手机响了,屏幕上跳着“大姐”俩字。 她声音哑哑的,像含着口棉花:“老二咋样了?我把小的哄睡了,现在过去,你在哪个病房?” 我报了房号,挂了电话跟二姐说:“你看,我说她不是不心疼你吧。” 二姐没接话,眼睛盯着床头柜上的搪瓷缸子——那是我妈留下的,以前她俩抢着用,后来给了二姐当嫁妆,缸沿磕了个豁口,还能看见里面掉瓷的白茬。 没十分钟,病房门“吱呀”一声开了,大姐扶着门框喘气,手里提溜着个保温桶,蓝布兜子磨得起了毛边,边角还沾着片干枯的槐树叶。 “你可算来了!”我起身想接她,她摆摆手,径直走到床边,把桶往桌上一放:“老二,我给你熬了小米粥,你小时候最爱喝的,加了点南瓜,甜乎。” 二姐鼻子抽了抽,没回头:“谁爱喝你熬的,上次熬糊了还硬说焦香。” “那这次没糊,”大姐也不恼,掀开桶盖,拿勺子搅了搅,“我守着锅搅了四十分钟呢,就怕跟上次似的——”她突然顿住,看了眼外甥女,把后半句咽下去了。 我心里跟猫抓似的,拉着外甥女到走廊:“你奶奶刚才说上次,上次咋了?” 外甥女挠挠头,踢着墙根:“就上个月呗,我弟半夜发烧惊厥,我爸妈出差不在家,姥姥背着他跑了三站地去医院,到那儿自己也晕过去了,医生说她血压都飙到180了,输了半宿液才缓过来。” 我愣住了,想起刚才大姐哑着的嗓子,还有她扶着门框喘气的样子——她不是不想来,是真怕孙子再出啥岔子,更怕我们知道她自己身体也扛不住。 回到病房,大姐正拿勺子给二姐喂粥,二姐眼角亮晶晶的,嘴上还硬:“咸了。” “咸了就对了,”大姐手没停,粥吹凉了才送她嘴边,“小时候你抢我咸菜吃,现在该你还回来了。” 那天下午太阳挺好,从窗户斜斜照进来,落在二姐床头的旧照片上,是我妈带着我们仨在老槐树下拍的,大姐站最左,二姐挤中间,俩小辫翘得老高,跟要飞似的。 后来二姐出院,大姐每天骑着三轮车来送汤,车斗里总坐着那个喝中药的小孙子,裹得跟个小粽子似的,露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 有次我逗小孙子:“你奶奶偏心,给老姨奶奶熬粥不给你喝。” 他奶声奶气地扒拉着车斗栏杆:“奶奶说,老姨奶奶以前把馒头分给她吃,现在该她分粥了——奶奶还说,中药比粥苦,我得先苦后甜。” 我突然琢磨过味儿来,亲情这东西,哪用得着在生死关头表忠心?它就藏在四十分钟搅动的粥里,在背着孩子跑三站地的黑夜里,在那些说不出口的“放心不下”里,跟二姐床头那搪瓷缸子似的,看着磕磕绊绊,装的全是热乎气儿。 就像二姐总说的,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急出来的——那天我骂娘的火气,现在想想,倒像是给这碗热粥加了把柴,越熬越香了。
我外甥女打来电话,说她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姐在医院人不行了,让我们去医院看看。我一听
好小鱼
2025-12-31 18:52:53
0
阅读:1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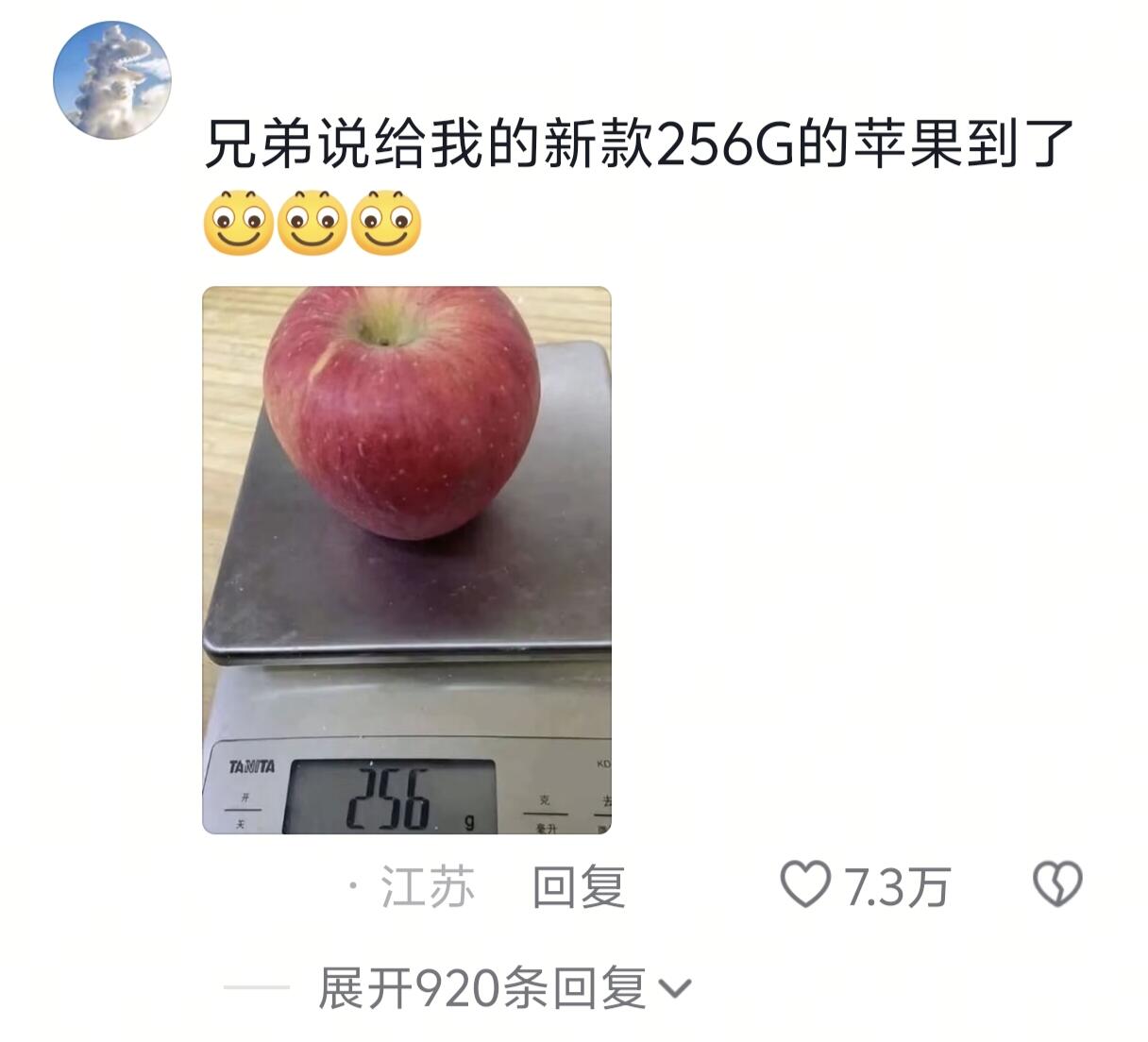






乐乐
到底是见最后一面把人见活了,华佗再世啊!
Q3Q
这种故意编病重的事还是少来,万一不是打车而是开车,又着急,很容易出意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