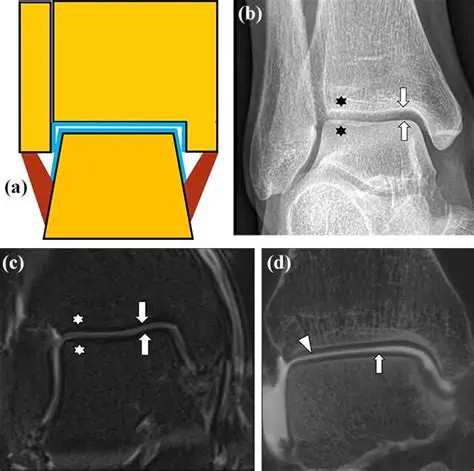我五岁那年娘跟人跑了,爹整天喝酒,喝醉了就打我。后来爹也死了,我就跟着大伯过。大伯家五个孩子,我去了就是第六张嘴。从那时候起,我就没穿过一件囫囵衣裳,冬天光脚踩雪地里捡柴火,脚后跟裂得跟老树皮似的。 大伯母是个寡言的女人,手背上布满了冻疮和老茧,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面、喂猪,忙到深夜还在缝补一家人的衣服。她从没说过嫌弃我的话,只是每次盛饭时,都会悄悄往我碗里多舀一勺红薯;我捡柴火回来冻得直哆嗦,她会把我的脚揣进她的棉袄里暖着,嘴里念叨“娃的脚咋冻成这样,明天给你找双旧鞋”。 五岁那年,娘跟着别人走了,没留下一句话。 爹开始整天抱着酒坛,喝醉了就红着眼骂,巴掌落在我身上时,冬天的风都比他的手温柔些。 后来他也走了,在后山的土坡上缩成一个小小的坟包。 我成了大伯家的第六张嘴,五个堂兄妹挤在土炕上,我抱着膝盖坐在炕角,那时候我总在想,这个家里多我一个,是不是真的太挤了? 冬天的雪片子打着脸,我光脚踩在雪地里捡柴火,脚后跟裂开的口子渗着血珠,冻得发木,像老树皮上的沟壑。 大伯母话少,手背上常年堆着冻疮,老茧比针脚还密。 天不亮她就蹲在磨盘前,吱呀声里转出一家人的口粮,喂完猪又去缝补衣服,油灯昏黄时,她的影子在墙上拉得老长。 我从没听她说过“你是累赘”这样的话——倒是我自己,总在心里反复掂量这句话的重量。 但每次盛饭,她的勺子总会在我碗里多顿一下,红薯块堆得比堂兄妹们高出一截; 有次我捡柴回来,冻得牙齿打颤,她突然把我拽到炕边,一把将我的脚揣进她的棉袄里,暖和的热气裹上来,她的手搓着我的脚踝,嘴里嘟囔:“娃的脚咋冻成这样?明天说啥给你找双旧鞋,可不敢再光脚了。” 我一直以为,她不说嫌弃,是因为大伯的面子,是因为她是“好嫂子”该有的样子; 直到那天她棉袄里的温度烫到我心里,才突然明白,在五个孩子都填不饱肚子的年月,多舀的那勺红薯,揣进怀里的那双脚,哪有什么“应该”?不过是她自己也苦,却舍不得让我更苦罢了。 她从没说过“爱”或“疼”,可那勺多出来的红薯,那双揣进棉袄的脚,让我在漫天风雪里,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飘着的蒲公英;后来我走南闯北,见过太多繁华与落魄,总记得蹲下来给乞讨的老人买个馒头,给加班的同事留盏灯——那些沉默的善意,早就在我心里生了根。 那年冬天过去,我脚上真的有了双旧棉鞋,虽然前头开了胶,却暖得能焐化冰碴子。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温暖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自己也难的时候,还愿意分一点光给别人。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沉默的人——话不多,手脚却总比嘴快——不妨递杯热水,说句“你也歇会儿”,他们的好,值得被看见。 如今想起那年冬天的雪地,脚后跟的裂口好像还在疼,但更清晰的,是大伯母棉袄里的温度,是她嘟囔时呼出的白气,混着灶膛里柴火的焦香,把整个童年的冷,都烘成了暖烘烘的回忆。
我五岁那年娘跟人跑了,爹整天喝酒,喝醉了就打我。后来爹也死了,我就跟着大伯过。大
正能量松鼠
2025-12-31 18:42:16
0
阅读: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