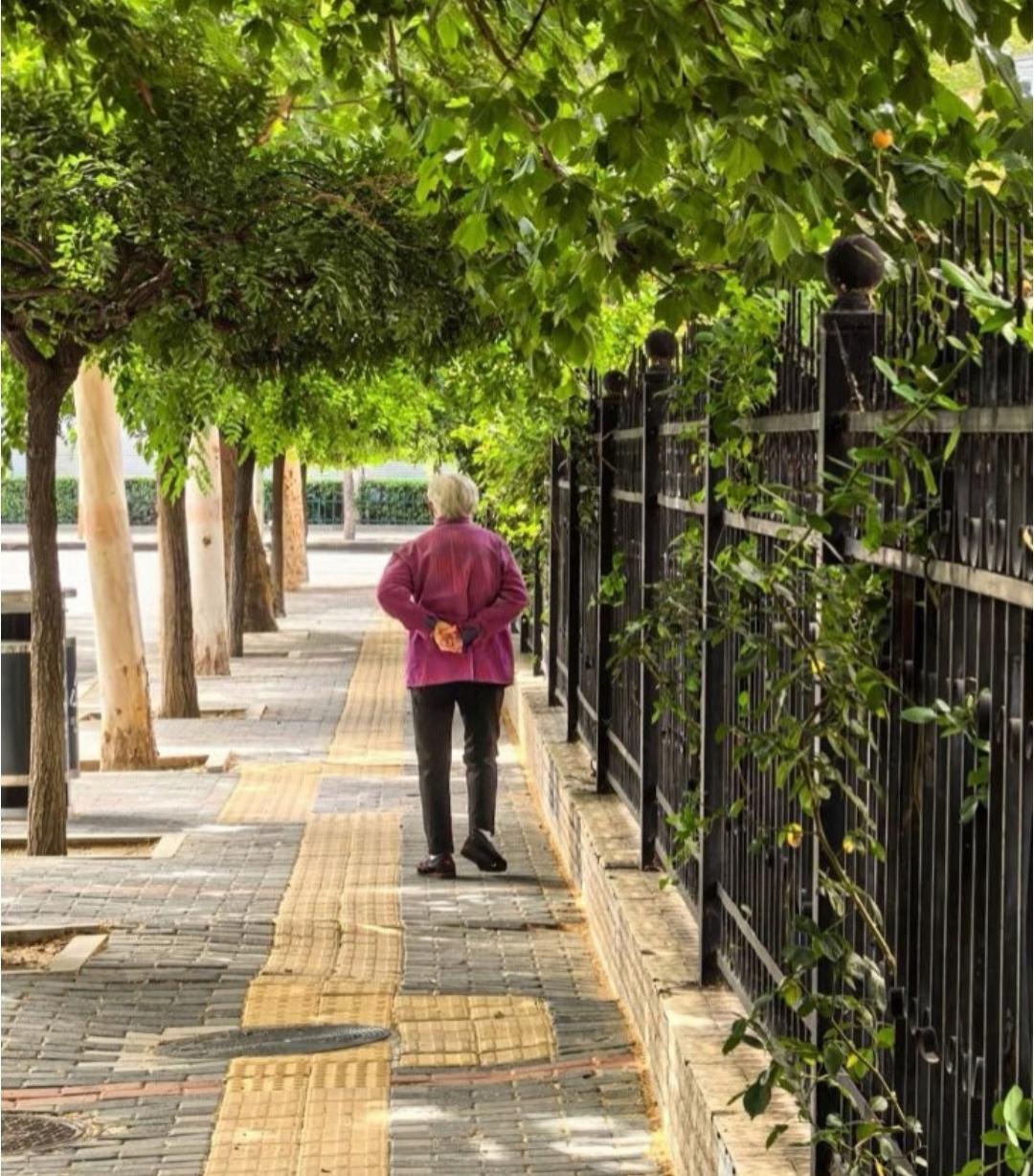那年,我们矿区房屋拆除,挖废铁、捡废铁的人很多,那两年废铁很贵。我爸那时候刚从矿上退下来,闲不住也跟着凑热闹。矿区老房子拆得七零八落,钢筋、水管、旧锅炉碎片,只要沾铁的都有人抢。 那年矿区拆房,黄尘裹着铁锈味漫了半条街——老砖碎成渣,预制板砸在地上闷响,穿迷彩服的、戴旧布帽的,都猫着腰在废墟里扒拉。 我爸刚从矿上退下来,蓝布工装洗得发白,挂在衣柜里三天没动过;他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圈飘到拆房的方向,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膝盖上的老茧——那是攥了三十年风镐磨的。 第四天清晨,他揣着馒头就往废墟走,帆布包甩在肩上哐当响——里面装着我妈连夜缝的厚手套,还有把磨尖了的钢钎。 别人抢钢筋时,他专挑角落里的碎铁:水管接头、锅炉铆钉、甚至暖气片上的小螺丝,指甲缝里嵌满黑泥,傍晚回家倒在院里,哗啦一声堆成小丘。 有次他蹲在墙根扒砖,砖缝里掉出个生了锈的铁皮盒,打开时簌簌掉灰——里面不是铁,是半块啃过的玉米饼,裹着张泛黄的纸条:“给下工的你留的,趁热”。 邻居王婶撞见了,打趣他“老陈也为钱折腰啦”,他嘿嘿笑,把铁皮盒塞进包里——后来我才知道,他捡的碎铁卖了钱,全给矿上的老张买了轮椅,老张去年炸山伤了腿,儿子在外地。 你说他图啥呢?退休工资够花,家里又不缺那点钱。 那天他坐在院里擦铁皮盒,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盒子上的锈迹被磨出小块亮斑,像极了他年轻时矿灯照在煤层上的光——那光里有他三十年的早班,有我妈在矿道口等他的身影,有老张拍着他肩膀说“明天还搭伴下井”的笑声。 他不是闲不住,是怕被日子丢下——就像矿上的老机器,停了转就容易生锈;捡废铁不是抢生计,是给自己找个“下工”的理由,让每天的太阳升起时,他还有个地方可去,有件事可做。 后来矿区拆完了,他把铁皮盒收在书柜最上层,旁边摆着我小时候画的“爸爸是矿工超人”。 再后来他迷上了养花,月季、吊兰、仙人掌,把阳台摆得满满当当,说“这跟伺候机器一样,得天天看顾着”。 原来长辈的“折腾”,不过是想在时光里找个锚点,让自己觉得还“有用”——下次你家老人蹲在楼下捡纸壳,别急着拉他,陪他蹲会儿,听他说说那些“没用”的往事。 现在每次回老家,我都要打开那个铁皮盒,里面的玉米饼早没了,纸条也脆得一碰就碎,但那股混着铁锈和玉米香的味道,还像那年拆房的黄尘一样,一闭眼就漫过来——漫过他弯腰扒砖的背影,漫过他把碎铁倒进收购站磅秤的哗啦声,漫过他说“活着就得动,动着才有劲儿”时眼里的光。
那年,我们矿区房屋拆除,挖废铁、捡废铁的人很多,那两年废铁很贵。我爸那时候刚从矿
正能量松鼠
2025-12-28 13:41:53
0
阅读: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