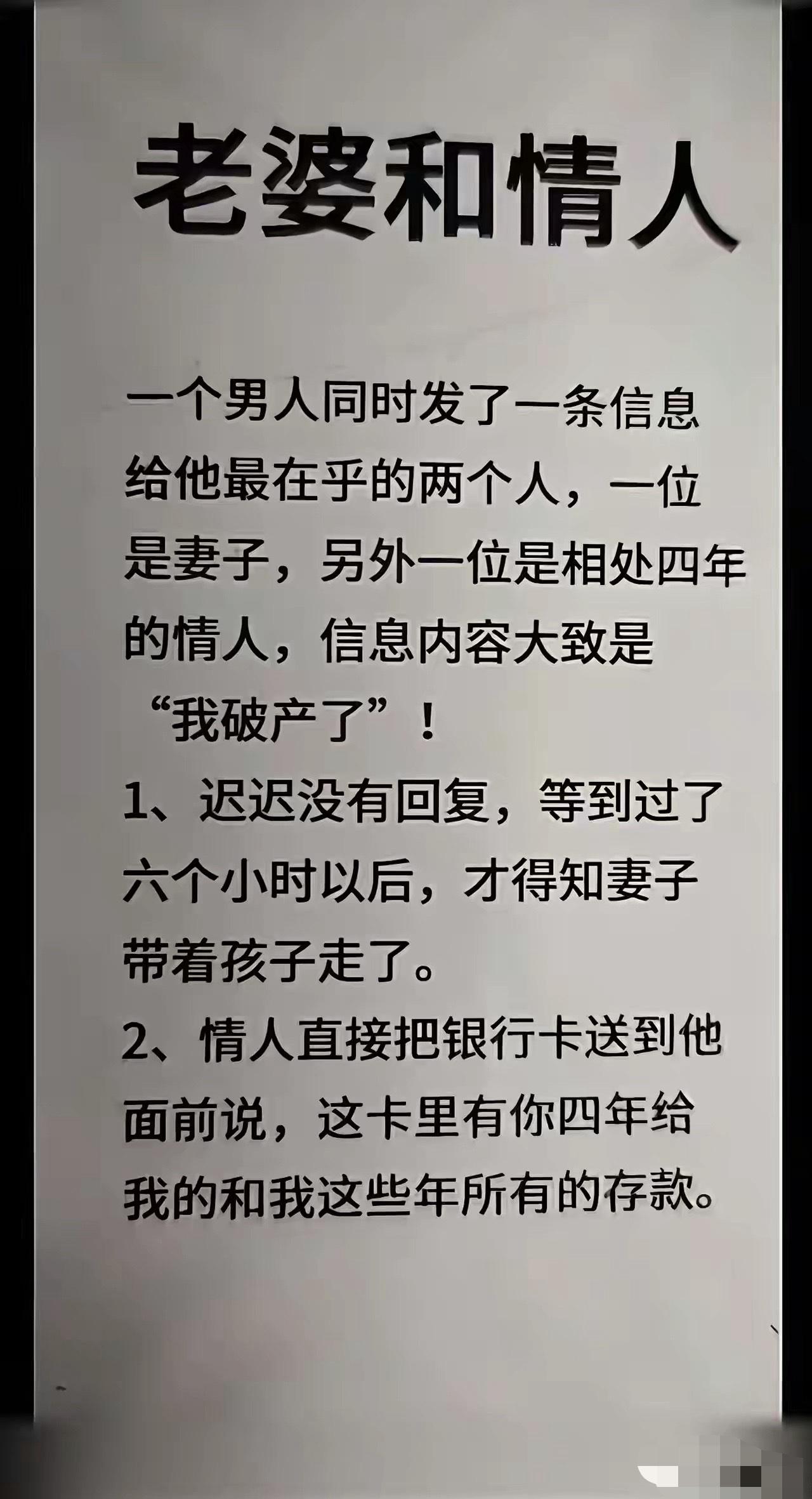1948年,一老农民因贪便宜娶了一个不要彩礼的女人,并为他生了8个孩子。 展晖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在村口捡回的女人,会让他在三十年后的冬夜,攥着一封遗书直打哆嗦。 那会儿他刚把最后一捆柴火搬进灶房,山风撞开木门,卷着几片雪沫子落在灯芯上,晃得满屋子人影都在颤。 那年头兵荒马乱,山里汉子娶媳妇难如登天。 展晖都快四十了还是光棍,每天守着两亩薄田和破草屋,夜里听着隔壁娃哭,心里像被虫蛀似的空。 直到那天在山坳里遇见她,蓝布衫沾着泥,头发乱糟糟的,却直挺挺站着问:“我没地方去,你要是肯娶我,啥彩礼都不要。”展晖以为自己听错了,搓着手嘿嘿笑:“你可想好了?我家就这三间土房。”女人没说话,只是把怀里的小包袱往身后藏了藏,那包袱皮上绣着朵他不认识的花。 成亲那晚,展晖才知道她叫张春莲。 这女人实在古怪,吃饭时筷子捏得笔直,不像村里婆娘那样扒拉着碗;夜里纺纱,纺车摇得轻,嘴里却哼着他听不懂的调子,调子软乎乎的,像水漂在云上。 更奇的是她会打算盘,账本子记得比先生还清楚,把家里几袋粮食、几只鸡鸭都归置得明明白白。 展晖有时看着她教娃写字的背影,会突然想起她包袱里那朵花他总觉得这女人不是山里该有的。 日子一晃过了三十年,八个孩子都长成人,最小的也能背柴了。 张春莲还是老样子,只是夜里写信的次数多了,写一封烧一封,灶膛里的灰总带着点纸烬的白。 有回小儿子半夜起夜,看见娘对着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红衣裳发呆,那衣裳滑溜溜的,领口开得很低,不像庄稼人穿的。 孩子问:“娘,这是啥?”她手一抖,衣裳掉在地上,慌忙拾起来塞进柜底:“没啥,老早前的破烂东西。” 1978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早。 展晖正在院里劈柴,三个穿公安制服的人进了村,脚步踩在雪地上咯吱响。 他们径直走到他家门口,张春莲刚好端着饭碗出来,看见人,手没抖,只是把碗轻轻放在石磨上:“我跟你们走。”展晖冲上去拦,被她按住胳膊,她手心的茧子蹭着他的手腕,就像刚成亲那晚替他补衣服时一样。 “有封信在枕头下,你看看。”她声音低低的,说完跟着人走了,蓝布衫在雪地里越变越小。 展晖抖着手摸出枕头下的信,信纸泛黄,开头三个字让他眼发黑“素贞绝笔”。 原来她不叫张春莲,是当年保密局的人,连名字都是假的。 信里说她嫁给他不是为了躲事儿,是真觉得跟他过日子踏实;说那几件旗袍是从前的衣裳,舍不得扔;还说教娃读书,是想让他们走出去,别像她一样一辈子活在影子里。 展晖看到最后,“其实我早不是张素贞了,我是你娃的娘”,眼泪啪嗒掉在纸上,晕开一片墨迹。 后来公安又来了一趟,说她没啥大罪,放回来了。 展晖在村口等她,见她还是穿着那件蓝布衫,头发白了大半。 他接过她手里的包袱,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那几件旗袍,叠得整整齐齐。 “烧了吧。”她轻声说。 展晖没说话,把旗袍抱回家,塞进柜底最深处。 再后来张春莲走了,走的时候很平静,拉着展晖的手说:“下辈子还嫁给你,还不要彩礼。”展晖没应声,只是看着她闭了眼。 如今他常坐在门槛上抽烟,烟袋锅子一明一灭,柜底的旗袍还在,只是压着一封泛黄的遗书,上面“素贞”两个字早就看不清了。 八个孩子都孝顺,时常回来看他,没人再提那些年的事儿,就像娘一直是张春莲,爹一直是那个贪便宜娶了不要彩礼的女人的老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