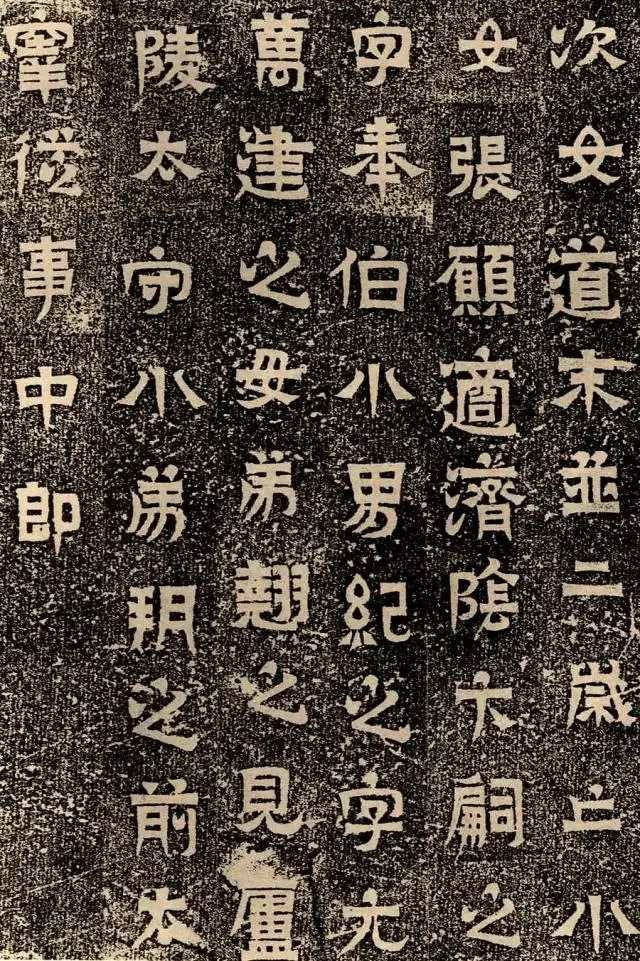1955年大授衔后,远在大洋彼岸的李奇微看到报纸上十大元帅的名单后,命人送到麦克阿瑟那里,麦克阿瑟看到后,气得拍起了桌子:“马修这是想羞辱我吗?他这意思分明是说,在中国还有九个跟彭德怀一个级别的人存在,而朝鲜战场上只派了一个彭德怀就把我们十几个国家打败了!” 一九五五年的纸张很薄,压在桌上却像压着一整场战争。 十大元帅的名单从北京漂到大洋彼岸,李奇微看了一眼,把报纸折好,吩咐送去给麦克阿瑟。 那位老将军戴上眼镜看完,手一抬,桌子先挨了一巴掌,茶水晃出来,人像是被拽回了鸭绿江边的冷风里。 这口气从哪儿憋起的,还得往前追很远。 一八六六年,朝鲜处死了几名美国和法国的传教士,军舰开到近海,计划结成联军,真要登陆时又缩回去。一八八二年,美朝在天津签条约,特地写上一句“彼此遭受不公正对待要互相支援”,听着挺讲义气。 轮到甲午战争,这句漂亮话就露了底。 清廷惨败,日本人闯进朝鲜,美国既没有动兵,也不愿多走一步,在外交上干脆把朝鲜往边上挪。后来不少军政人物回忆,当时对朝鲜的印象就是穷、远、不值得,真该下血本的是欧洲和太平洋,半岛不过夹在中间的一块石头。 二战结束,格局翻篇。 苏联从北线压下,美国从南线上去,三八线划在地图上,半岛被切成两截。一九四八年,杜鲁门公开强调,美国不要在朝鲜陷得太深,不能谁在那儿开一枪,华盛顿就跟着把仗打大。这句话听上去挺冷静,离一九五零年的炮声却只差两年。 另一边,新中国刚刚站起来。 解放军打到海边,毛主席和中央心里明白得很:如果让敌对力量把阵地推到鸭绿江边,东北老家迟早不得安生。 美国和苏联盯着的是中国这块大棋盘,可脚底下那条缝恰恰就是朝鲜。 等半岛起火,美军披着联合国军的牌号上阵,中国志愿军顶着“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呼越过江去,几路人马在冰天雪地里撞在了一起。 对麦克阿瑟来说,朝鲜一开始不过是太平洋战史后面的一道附加题。 他习惯用一种老成看戏的眼光审视战场。第一次战役过后,前线的报告一份份压到总司令部:大批中国军队已经投入战斗,人数多,打得也狠,不能再把对手当小股部队。这些提醒从山沟里一路传到东京,到了麦克阿瑟耳边,却被他一句“他们撑不了多久,两星期内就能结束”压了回去。 接下来第八集团军照旧一路猛冲,在志愿军布好的几道口袋阵里被打得七零八落,公路上堆满丢下的武器车辆,司令沃克死在慌乱撤退途中,这是美国军界抹不掉的阴影。 两位统帅的差别,不止在脾气,更在那七百英里的距离。 麦克阿瑟人窝在东京,隔着海看战报和沙盘,数字不合心意就当估算偏差。 彭德怀把指挥部往前线一点点挪,带着参谋翻山趟河去看阵地,火力点、穿插线、伏击位得自己用眼睛量,很多决心是在前沿阵地上琢磨出来的,不是在灯光底下推演出来的。 战局失控以后,华盛顿按捺不住,决定请麦克阿瑟退场,让李奇微接手。 新来的总司令心里门儿清,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出的政策红线,谁踩上去谁吃苦头,所以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往前线跑。几场硬仗打下来,他发现一个规律:志愿军的猛攻大多能咬住七天,前几天像潮水一样往前扑,过了这个坎,火力和动作都慢下来,补给绷到极限。 抓住这条脉,他琢磨出了那套“磁性战术”。 阵地不再一味后退,而是像磁铁一样先把志愿军黏住,在对方最猛的几天硬顶着,等那股子劲过去,再配合大规模空袭,对公路、桥梁和运输队做所谓“空中绞杀”。 结果就是,山路上越来越多背着弹药粮食的身影,黑夜里趁着星光赶路,天刚蒙亮就得抬头提防飞机。 靠着这一套打法,联合国军从溃退边缘拉回到僵持线上,李奇微在美国国内也被捧成“把局面救回来”的人物。林登约翰逊当面追问麦克阿瑟:假如真把中国军队赶回鸭绿江对岸,而中国既不签条约,也不谈未来安排,美国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这一问,把整场战争的空心处戳了个正着。 麦克阿瑟说不出什么长远方案,只习惯性地强调中国撑不久,不会一直打下去。 为什么要打,打成什么样算够,付出到什么程度该止损,这几道题在美国高层心里一直模模糊糊。类似的迷糊,在中东也能看到。以色列建国之初,是苏联先伸手承认,美国后来才意识到这块小地方的价值,急匆匆挤进去,局面越拖越乱。 名单上的彭德怀三个字,落在麦克阿瑟眼里,很难只被当成一个对手的名字,更像是一整段记忆的封条。那行字提醒人们,朝鲜那些被轻看的山沟雪谷,曾让十几个国家摔了个跟头。 纸张静静铺在桌上,老将军的指尖慢慢移过一个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