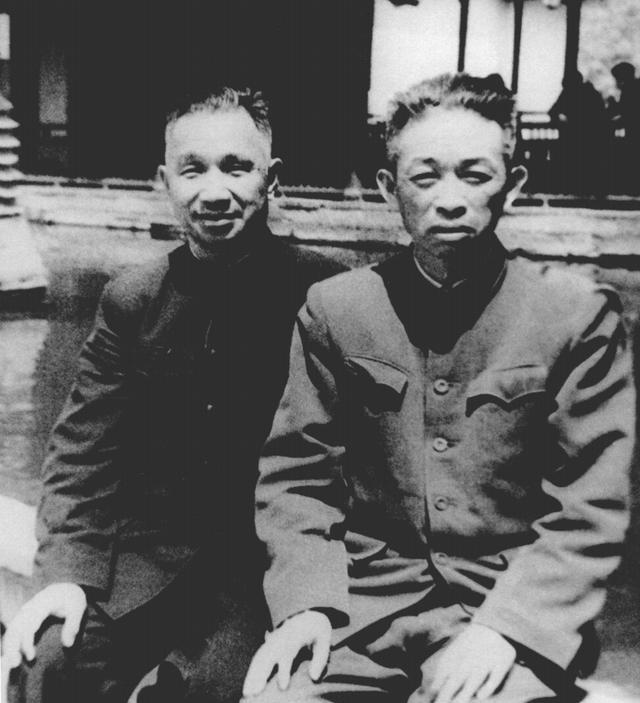1949年12月,国军军长鲁崇义劝说参谋长何沧浪起义,然而何沧浪却涨红了脸,梗着脖子道:“军长!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拼死一搏,或许还能杀出一条血路!” 鲁崇义听着,没立刻回应,只是沉着脸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那份厚厚的名单。何沧浪站在原地,手还搭在腰间的皮带扣上,脸色涨得发紫。 鲁崇义把名单“啪”地一声摊在桌上,声音冷下来:“这些名字你看过吗?这是第三十军士兵家属的登记,全是我们的兄弟带着一家老小从西北一路逃到成都的。” 他盯着何沧浪的眼睛说,“他们打了十几年仗,不是为了今天全军覆没。” 距离重庆失守已经两个星期,胡宗南的命令还在不停地发过来:“坚守阵地,死战到底。”可鲁崇义心里清楚,那不过是纸上的话。 自从贵州被解放军穿插突破后,整个西南的防线就已经崩了。他的部队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收到新的补给,仓库只剩下一些罐头和干粮,弹药不够打一场像样的遭遇战,连电台也因零件老化而断断续续。 鲁崇义不是没想过死守成都,但现实不允许。第三十军本是国民党中央军系统下的老部队,大部分官兵出自甘肃、宁夏、陕西一带,抗战期间驻守西北线,虽没打过什么大仗,但忠诚可靠。 他们不是不能打,而是没有打下去的条件。 军中开始有传言,有人夜里在帐篷里偷偷议论“军长可能另有安排”。鲁崇义并没制止,他默许这些流言往下传。他明白,这些流言传播得越广,说明大家对继续作战越没信心。 他在心里已经做出决定。 几天前,他以“商讨防御部署”为由召集营连主官,开会的地方选在营地一处偏僻的破木屋里。他没直接说“起义”两个字,只是问大家一句:“你们想活着回去,还是死在这?” 屋里沉默了一阵,一个团副轻声说:“我们这仗打不了多久了。” 那晚会议后,鲁崇义彻夜未眠。他回想起1937年入伍时,跟着部队在西北冻得嘴唇裂开,后来一路南调到西南战区,几次小规模作战他都冲在最前头。 可现在,他明白,一支部队的价值,在于是能否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死守的代价,是整个第三十军被全歼,那些跟随他多年的老兵,一个都活不下来。 他不甘心。 12月23日深夜,他带着心腹军官去联系了解放军前线。双方代表在距离成都几十公里外的一处村落秘密碰头。鲁崇义开门见山:“我不要条件,不要求保官衔,不要求保功勋。我只要我的人活下来。” 解放军方面很快回应:“只要第三十军不抵抗,按整建制接收,不清算、不追责、不打扰百姓。” 回到成都,鲁崇义又找了何沧浪。何沧浪还穿着整齐的旧式军服,袖口被补过几次,眼神坚决。 鲁崇义没有与他争吵,只是把何沧浪拉到窗口。窗外,士兵们正默默地收拾行李,有的在写信,有的蹲在火堆边烤冻得僵硬的手。 1949年12月25日清晨,成都雾气浓重,鲁崇义站在临时搭起的指挥台前,望着集结完毕的全军官兵。他只说了一句话:“命令如下,全军停止抵抗,整建制接收改编,严禁哗变,严禁扰民。” 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反对。所有人静静站着,然后慢慢解下帽徽和袖标。何沧浪没说话,他站在人群中,摘下自己的肩章,小心包进帆布包里,随后站直,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和平解放在清晨的沉默中完成。之后,第三十军多数官兵被安排复员,也有一部分进入新编部队。鲁崇义没有留下,在提交了一份简短的报告后,他离开了军职,去了川北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