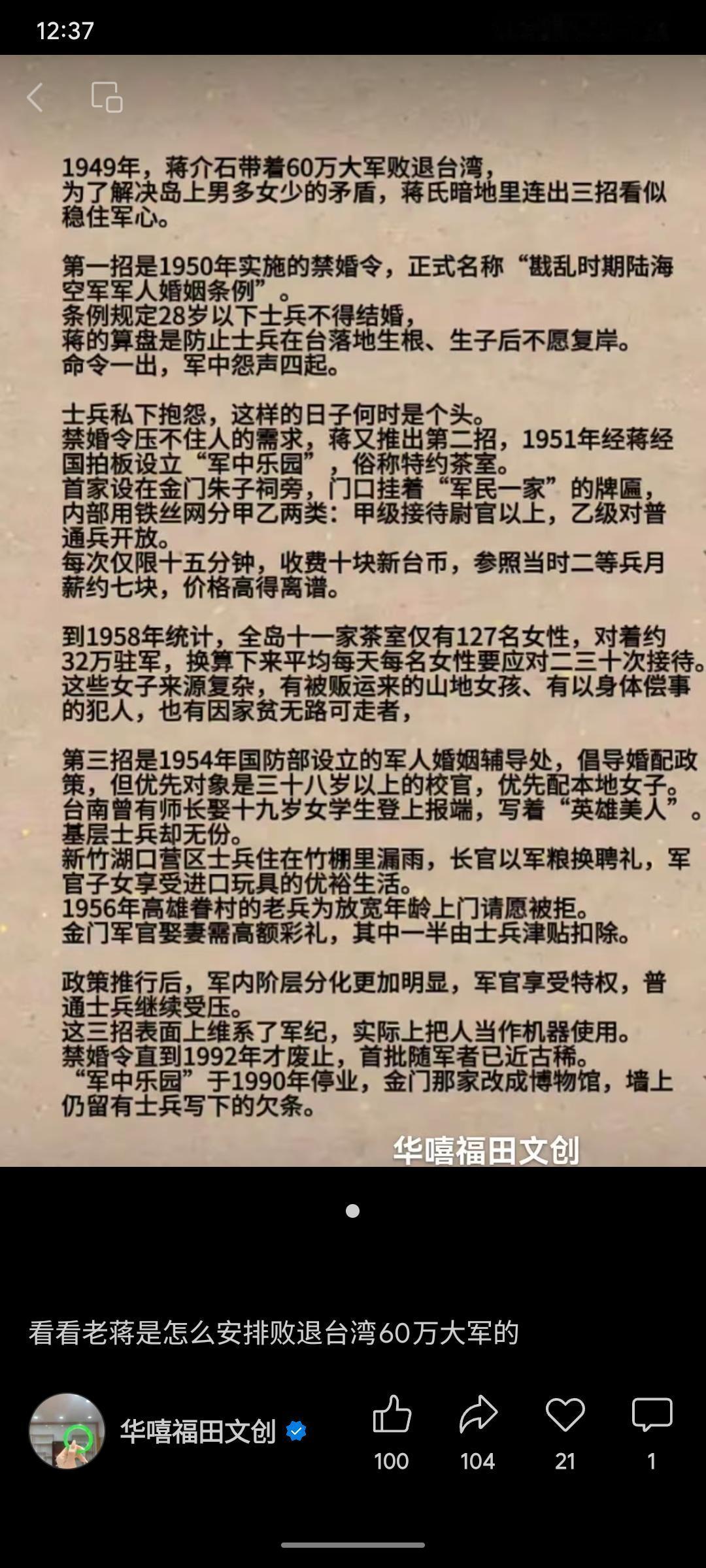1939年四位于淞沪之役负伤截肢的战士,从左至右:李家雄、葛仁祥、任成玉、曾炳山。其行其志,足见抗战之艰、将士之勇。 这张黑白照片的拍摄地,是湖南衡阳的一座后方医院。镜头里的四位战士,军装洗得发白,空荡荡的袖管或裤管被简单扎起,脸上却没有丝毫颓唐——李家雄嘴角紧抿,眼神依旧锐利;葛仁祥双手扶着桌沿,坐姿挺拔如松;任成玉微微侧头, 似乎在听战友说话;曾炳山则望着镜头,眉宇间藏着未凉的战火。他们身后的墙壁上,“坚持抗战,还我河山”的标语墨迹未干,那是1939年最朴素也最坚定的信念。 李家雄那年才19岁,是四川万县的农家娃。1937年8月,淞沪战役打响,他瞒着父母报名参军,编入第88师262旅。日军的炮火比想象中更凶残,10月的蕴藻浜战役,他所在的连队负责坚守前沿阵地,日军的汽油弹呼啸着落下,阵地瞬间变成火海。 为了掩护战友炸毁日军碉堡,他左臂被弹片击中,动脉断裂,军医在战壕里紧急为他做了截肢手术,没有麻药,他咬着毛巾,硬生生挺了过来。“不后悔,”后来有人问他是否遗憾,他总是摇头,“能多杀一个鬼子,少让一个同胞受苦,断条胳膊算什么。” 葛仁祥是四人中年纪最大的,参军前是江苏南通的木匠,手上的老茧是常年拉锯留下的痕迹。淞沪战役时,他是第19路军的机枪手,在江湾一带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日军的坦克冲破防线,他抱着炸药包冲向坦克,却被侧翼的日军机枪击中右腿。 战友把他从战场上救下来时,右腿已经血肉模糊,送到后方医院时,伤口已经感染化脓,为了保住性命,只能截肢。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凿子,那是他唯一的念想。“等抗战胜利了,我还要给乡亲们做家具,”他常对病友说,“到时候做最好的木床,让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 任成玉来自山西大同,原本是铁路工人,日军占领东北后,他一路南下参军,加入了第67师。淞沪会战中的罗店战役,被称为“血肉磨坊”,双方反复争夺阵地,尸体堆成了小山。任成玉所在的排负责坚守一座小桥,日军的炮火持续了整整一天,桥梁被炸毁,他的左腿被坍塌的桥面压住,等到援军赶到时,左腿已经失去了知觉。 截肢后,他一度消沉,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裤管,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医院里的伤兵们互相搀扶着练习走路,听到孩子们隔着窗户唱《松花江上》,他突然醒悟:“我还有一条腿,还能为抗战做点事。”之后,他主动承担起医院的文书工作,帮伤兵们写信、记录战功,每一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 曾炳山是广东梅州人,家里世代务农,淞沪战役爆发时,他刚结婚三个月。他所在的部队负责防守宝山县城,日军的军舰在江面上狂轰,城墙被轰出一个个缺口,日军步兵趁机攻城。曾炳山手持步枪,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在巷战中,他的右臂被日军的刺刀刺穿,骨头断裂。 为了不拖累战友,他自己扯下军装布条包扎伤口,继续战斗,直到失血过多晕倒。被救醒后,他发现自己的右臂已经无法保住。“我对不起妻子,”他偶尔会对着南方落泪,“答应过她,抗战胜利就回家,可现在……”但落泪之后,他总会立刻擦干眼泪,跟着战友们一起唱抗战歌曲,他说:“只要能把鬼子赶出去,就算一辈子不回家,也值。” 很少有人知道,这四位战士在医院里相遇后,组成了一个“抗战宣讲小组”。没有假肢,他们就拄着拐杖,或者互相搀扶着,到周边的乡村、学校宣讲前线的战斗故事。 李家雄讲蕴藻浜的火海,葛仁祥讲江湾的拉锯战,任成玉讲罗店的惨烈,曾炳山讲宝山的坚守。他们的声音或许沙哑,他们的身影或许残缺,但每一个故事都能点燃人们的爱国热情。有村民给他们送粮食,有学生给他们送鲜花,有老人握着他们的手说:“有你们这样的战士,中国不会亡。” 淞沪战役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军队投入兵力超过百万,伤亡达30余万人。像李家雄、葛仁祥这样负伤截肢的战士,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有的留在后方医院,有的回到家乡,有的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各地,但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没有放弃抗战的信念。没有手臂,就用嘴咬着炸药包;没有腿,就坐在地上射击;没有视力,就听声辨位,传递情报。他们用残缺的身体,扛起了民族的希望。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正是这些平凡的战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长城。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将士之勇”;他们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却用最坚定的信念,见证了“抗战之艰”。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早已不用面对枪林弹雨,但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奉献的战士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榜样。他们用残缺的身体告诉我们,民族的尊严,需要用勇气和热血捍卫;国家的安宁,需要用坚守和奉献守护。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