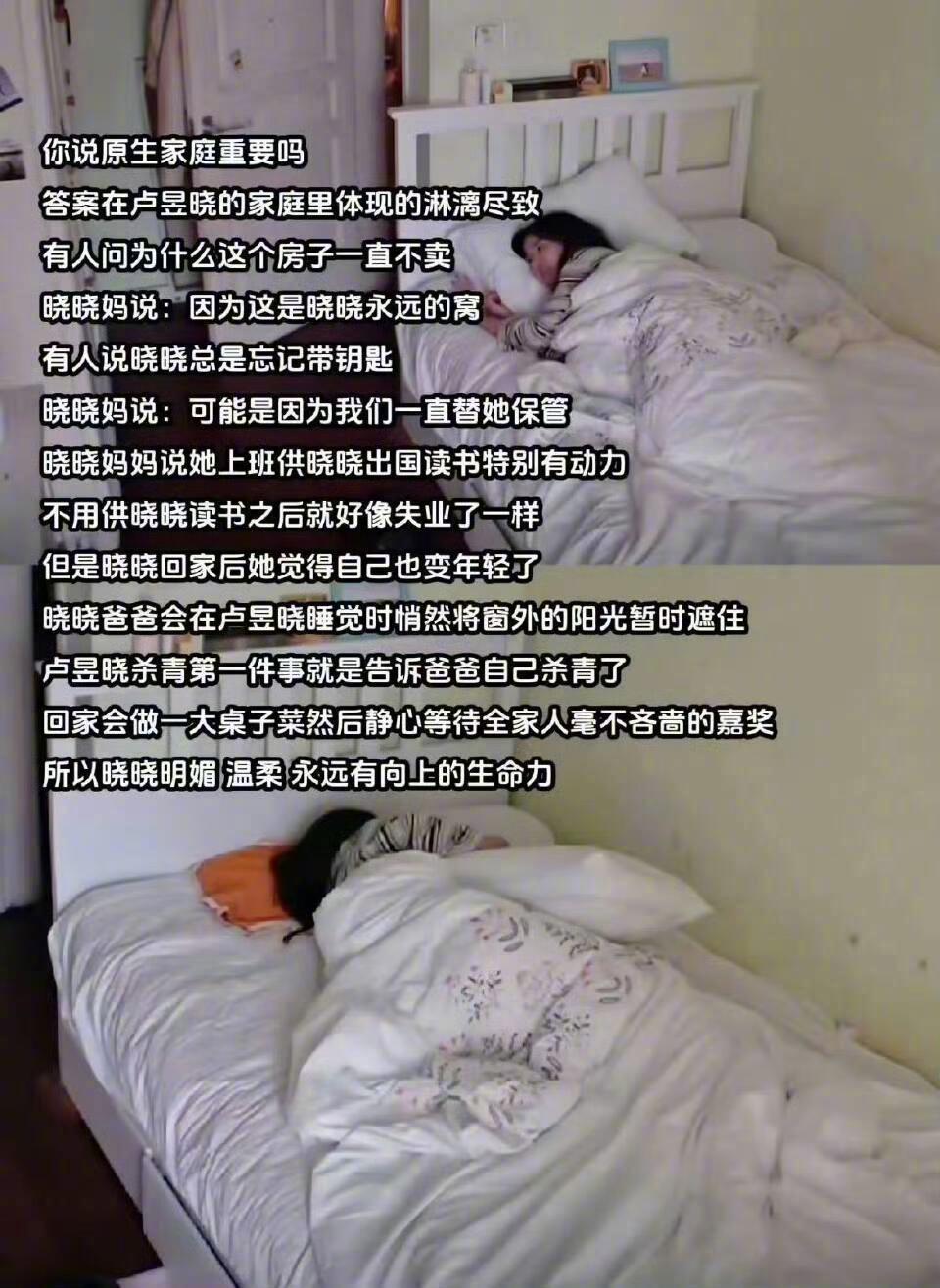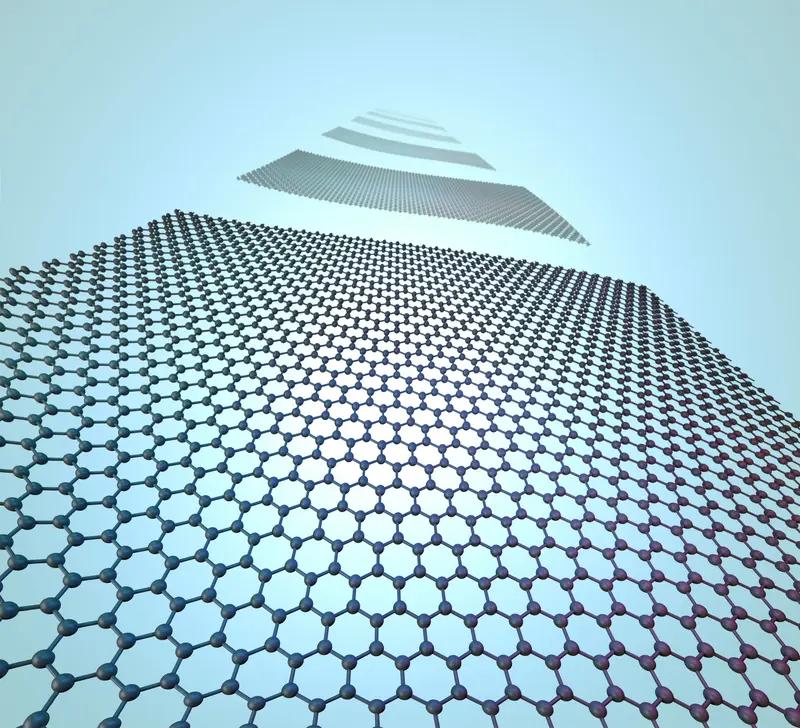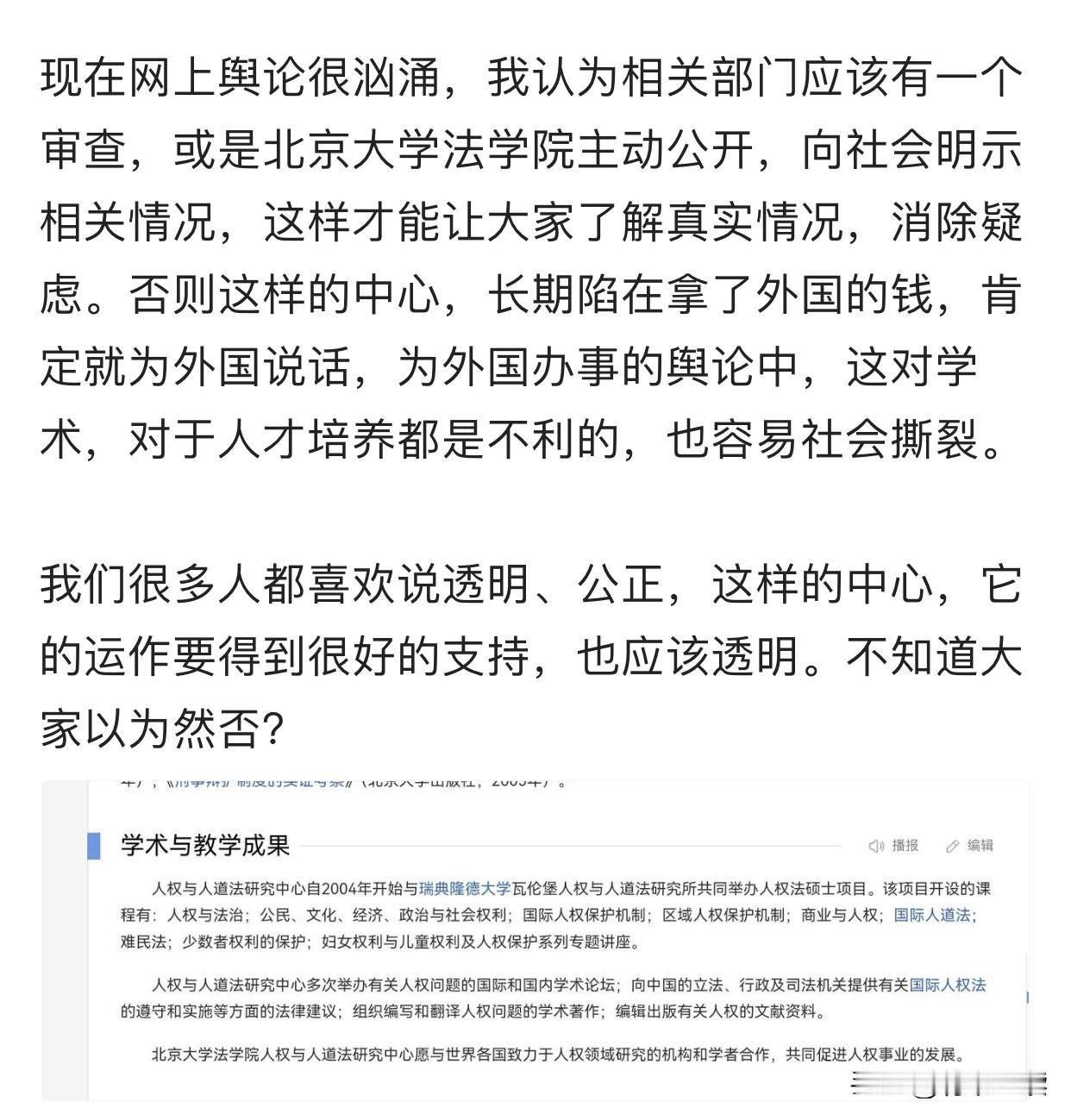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那天中午的北京,柳絮飘得正忙,王承书拎着布包出门时,饭桌上的碗筷还没收。丈夫张文裕以为她只是去实验室赶一份计算稿,谁知等到天黑,等到第二天,等到一周后,她才真正意义上从他们的生活里彻底消失。 实验室的钢笔还斜搁在草稿纸上,墨水瓶敞着口,仿佛主人只是临时被叫去开个会,但这一次,她再也没回来。 那支钢笔就那样静静躺着,墨水慢慢干涸成深蓝色的痂。张文裕在实验室里坐了整整一夜,走廊的灯明明灭灭,他想起去年春天妻子指着窗外说:“你看那些柳絮,看着轻飘飘的,可风往哪儿吹,它们就往哪儿去。”现在想来,这话里藏着另一层意思。 接下来的日子,张文裕像疯了一样四处打听。他去过北大物理系,系主任只是摇摇头;他找过妻子的同事,每个人都欲言又止;他甚至去了派出所,民警登记完信息后说:“张教授,有些事……别找了。”那句话像盆冷水,把他浇了个透心凉。儿子张哲那时才十二岁,夜里总抱着妈妈的枕头睡觉,早晨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 其实王承书就在离北京不远的荒原上。火车载着她和一群沉默的人往西北去,窗外的绿色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漫天的黄沙。没人告诉她要做什么,只说“国家需要你”。她想起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那年,导师劝她留下:“王,你的才华应该属于全世界。”她收拾行李时只说了一句:“我的世界在中国。” 西北的基地建在地平线以下,从外面看就是些普通的厂房。走进去才知道,地下的走廊长得望不到头,墙上刷着“以身许国,默默奉献”的标语。王承书被分配负责铀同位素分离的理论计算,那是制造原子弹最关键的环节之一。组长是个不苟言笑的老军人,见面第一句话是:“从今天起,你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过去,只有现在。” 她确实没有了过去。实验室的灯光永远惨白,桌上的计算尺磨得发亮,算稿堆起来能碰到天花板。有时算到凌晨,她会突然停下笔——儿子的生日是不是快到了?丈夫的胃病好些没有?这些念头刚冒出来,她就狠狠掐自己胳膊,直到清醒为止。有一次基地放电影《上甘岭》,看到战士们在坑道里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黑暗中传来压抑的抽泣声。王承书没哭,她把左手攥成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张文裕那边却渐渐有了猜测。1964年秋天,报纸上登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配着一张蘑菇云的照片。他盯着报纸看了很久,突然冲进书房翻出一本旧相册。有张照片是1956年在回国轮船甲板上拍的,王承书靠着栏杆,背后是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她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小字:“愿以此身,报效祖国。”张文裕把照片贴在胸口,眼泪终于落下来。 儿子张哲长大得特别快。1969年他下乡插队前,把母亲留下的所有东西装进一个铁皮盒子,包括那支干涸的钢笔。火车开动时,他对着北京的方向说:“妈,我也要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不知道,那个夏天他母亲正在西北的地下实验室里,因为长期接触辐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脱落。 重逢来得毫无征兆。1974年冬天,张哲被调回北京工作。某个雪夜他加班回家,看见楼道里站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背驼得很厉害,手里拎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请问……”他刚开口,老太太转过身来。时光在她脸上刻满了沟壑,可那双眼睛还和十二年前一样,温柔又坚定。“小哲,”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妈妈回来了。” 后来张哲才知道,母亲回家的路走了整整三天。从西北基地到兰州,再从兰州转车到北京,她一路上紧紧抱着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她十三年的计算手稿。进门后她没急着说这些年的经历,而是径直走进厨房,系上围裙:“我给你和你爸包顿饺子吧,韭菜鸡蛋馅的。” 那个雪夜,王承书一个人站在窗前看了很久。雪把整个北京城盖住了,就像西北的黄沙盖住他们的基地一样。她想起离开美国那天,有个记者问她为什么放弃优越的条件回国,她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现在她觉得这话应该改改——科学家不但有祖国,有时还得把自己变成祖国土地上的一块砖,埋在最深的地基里,永远看不见阳光,却托起了整座大厦。 张文裕深夜回家时,饺子还在锅里热着。他看见妻子满头白发,什么也没问,只是走过去握住了她的手。两双手都在抖,一双是因为常年打算盘,一双是因为常年握计算尺。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所有的足迹都掩埋了,就像历史掩埋了无数个“王承书”的名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