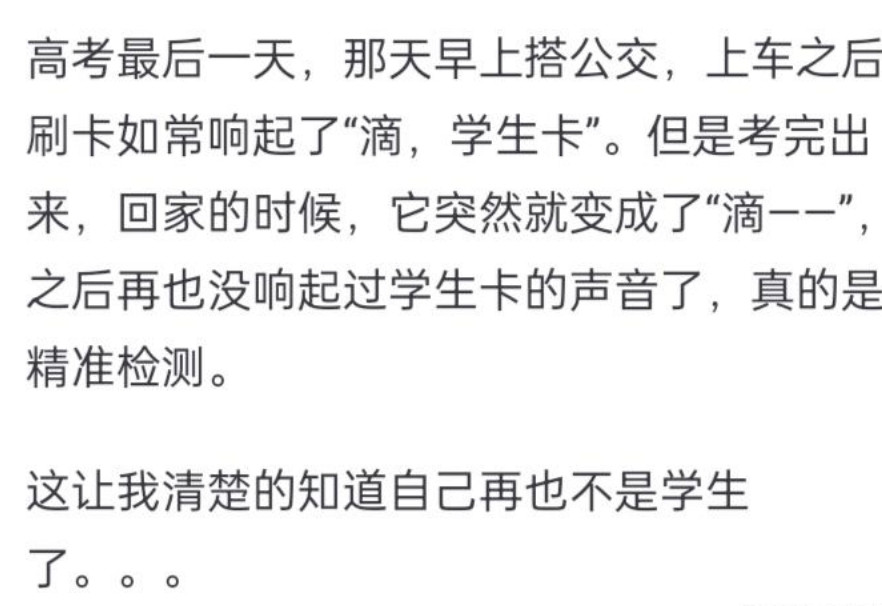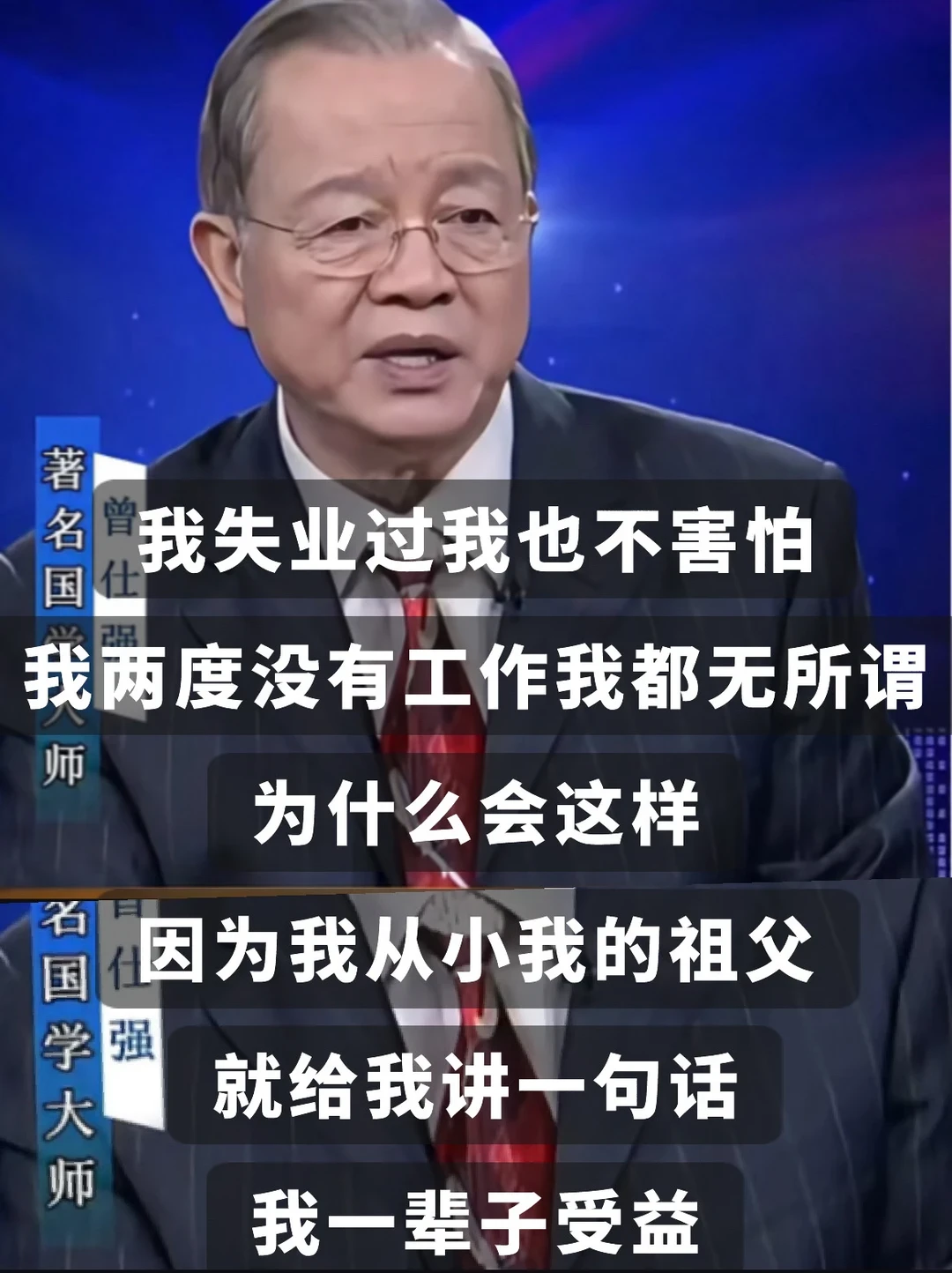1991年1月4日清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清洁工推开妇产科浴厕门时,正撞见作家三毛悬在半空的身影——她用一条咖啡色丝袜绕过淋浴架,双手合十,嘴角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这个画面如同一把锋利的刀,瞬间割裂了人们对"浪漫文豪"的固有想象。 1984年,三毛在一场名为“观落阴”的玄学活动中,声称自己偷看了一眼传说中的生死簿,那上面记载着她这一生注定要写二十三本书。 当时的旁观者或许只当这是一句玩笑,直到七年后,法医在那张死亡鉴定书上签下字,人们清点遗物时才惊觉:已出版的14部作品,加上积压待发的9部手稿,刚好是那个早已被“预言”锁定的数字——23。 那是一个寻常的早晨,台北荣总医院妇科的病房里,当清洁工推门而入,看到的是一个诡异而悲凉的画面。 身高一米六三的三毛,并不是完全悬空的,她在一米六高的点滴铁架上,用一双深咖啡色的丝袜终结了自己的旅程。 法医的报告总是冰冷的,但那一刻的很多细节却耐人寻味:这样一个并不足以完全吊起全身的高度,若非那份去意已决的绝望,求生的本能随时可以让双脚站稳自救。 多年来,人们习惯在琼瑶式的“深海寂寞”里寻找答案,或者在好友徐枫口中的“《滚滚红尘》失利伤了自尊”和“误以为患癌”的恐慌中拼凑真相。 这些世俗的打击固然是重锤,但若将那个被埋藏了17年的秘密挖出来,或许你会发现,死亡对她而言,更像是一场迟到的赴约。 2008年,好友眭澔平在那盏孤灯下,终于公开了一封早已泛黄的信笺,那是三毛去世前最后留下的字迹,藏在送给他的一本书里,信纸被旧时的泪水浸得皱皱巴巴,她不再是那个万众瞩目的作家,只是像个无助的孩子呼唤着密友的昵称“小熊”。 她在信里并没有长篇大论地解释痛苦,只是平静得可怕地通知他:“这一次,我真的要走了。”手术前的那个夜晚,医院的电话线曾传导过她最后的两次求救——或者说是告别,两通拨向眭澔平家的电话,都在无人接听的忙音中沉默了。 其实,这种想“走”的冲动,早已渗入了她生活的每一寸肌理,早在她住在加纳利岛的时候,居住环境就充满了某种黑色的隐喻,那是一片被探险家马中欣形容为“阴森”的男人海滩,触目所及全是黑色的火山岩、黑沙滩,甚至连涌动的海水在那个独特地理位置下都显出一股墨色。 就在那栋被她视为“冥想之地”的宅子里,生与死的界限早就模糊了,为了寻找逝去的爱人荷西,她近乎痴迷地钻研通灵,从东方的“碟仙”到西方的自动书写,她试图把每一个寂静的深夜变成与亡夫重逢的渡口。 这种执念甚至惊扰了现世的安宁。当时住在同岛的好友张福瑞夫妇,硬生生被三毛“吓”得搬了三次家。 原因听起来有些荒诞:三毛坚信自己招来的荷西魂魄,点名要见张家那个深受荷西喜爱的儿子,每一次她信誓旦旦地说把荷西带来了,都让这对夫妇背脊发凉,最终不得不逃离三毛那份沉重到有些畸形的“阴阳交流”。 甚至在徐訏去世时,她也曾试图跨越维度去感知,手指不受控制地写出自己都不通晓的法文,这些在旁人眼里的怪力乱神,在她那里,或许是比现实更真实的寄托。 当二十三本书的预言与现实重叠,当身体的痛楚与精神的空洞合流,那一晚医院卫生间的铁架,只不过是她通往心中那个有星星、有沙漠、有荷西世界的最后一道门槛。 这一跃,不论是林青霞口中的“情绪变化”,还是众人眼中的凄凉,于她而言,或许正如那两通没接通的电话一样,是对这熙攘人间最后的“挂断”。 主要信源:(成都商报——2008-03-26三毛自杀17年后友人首度曝光"遗书" 引发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