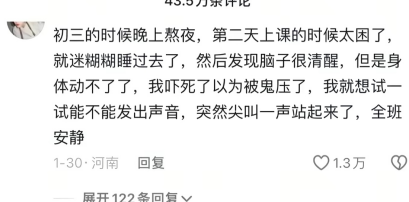我三十岁生日那天,父亲坐在老屋门槛上,阳光像一场迟到的解释,落在他佝偻的右肩。他抬手想揉我的头发,却只摸到我的下巴——我早已比他高出一个头。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十岁那年,我指着他对爷爷说“家里来客人了”。如今,我终于看清了这位“客人”用一生写给我的信,而我,刚刚学会读。 【一】 五岁那年,天刚蒙蒙亮,父亲便要出门坐大巴车去外地,车站尘土飞扬,他蹲下来,用胡茬蹭我的脸,生疼。我哭着喊“爸”,他“嗯”了一声,把眼泪憋进喉咙,转身挤进车门。那一年,我学会了第一个生僻词——“打工”,却不知道它要把父亲抢走好几年。 【二】 十岁那年,腊月二十八,家门口的雪厚得能埋住一条黄狗。我蹲在灶膛前烧火,忽然听见“吱呀”一声,一个黑影顶着风雪进来,肩上的蛇皮口袋比他人还大。我愣了半秒,冲里屋喊:“爷爷,家里来客人了!” 爷爷拄着拐杖出来,一拐杖就敲在我屁股上:“小畜生,连你老子都不认得了!” 父亲站在那里,像一座被雪覆盖的山。他咧嘴笑,眼角挤出沟壑,却不敢上前抱我。我躲到门后,偷偷看他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方便面、掉漆的玩具车,还有一双比我的脚大出两指的运动鞋——那是他记忆里儿子的尺寸,他忘了小孩也会长大。夜里,他蹲在灶口用热水泡脚,脚后跟裂开的口子像一张张渴了的嘴。我假装睡着,却从被缝里看见他往那些血口里贴胶布,每贴一下都倒吸一口冷气——那声音,比爷爷敲我的拐杖还闷、还疼。 【三】 十三岁,我考上镇里的初中,学费像一道跨不过去的河。暑假夜里,父亲背着竹篓,喊我跟他去田埂。月光像撒了一地的碎银,照见他卷起的裤脚,小腿上布满被鳝鱼咬出的血洞。 “篓子放下水,你踩住这头,别吭声。”他低声吩咐,嗓音与蛙鸣混成一片。我踩着,却偷偷回头看:他跪在田里,双手伸进暗黑的淤泥,像把黑夜撕开一道口子,去掏那最滑最腥的月光。 天快亮时,我们逮了十九条黄鳝。父亲把换来的钱用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包好,塞进我书包夹层,笑得像完成一场秘而不宣的祭祀。“好好念,”他说,我:“别让它们咬你。”父亲点头,我却不懂那些鳝鱼其实是他咬紧的命运,一口一口,替他儿子啃出一条路。 【四】 十六岁,我迷上网吧的霓虹,把“高考”当成别人的故事。父亲半夜蹲在网吧后门,手里提着保温桶,里面是母亲炖的鸡汤。他不敢进来,只托网管叫我。我摔键盘:“别来烦我!” 他站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影里,像一截被风吹灭的蜡烛。第二天清晨,我发现书包里多了一本崭新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扉页写着一行歪字——“爸没念过书,不知道这管不管用。” 我撕掉那页,继续钻进虚幻的枪声与喊杀。父亲沉默得像老屋的梁,任我在他胸口钉满钉子,却从不发出一声开裂的响。 【五】 二十五岁,我在省城一家广告公司熬夜做PPT,凌晨三点收到爷爷去世的消息。连夜包车回去,父亲跪在灵堂前,背影像被岁月压弯的一张弓。我走过去,第一次按着他肩膀,喊了声“爸”。他回头,眼里全是血丝,却只说:“回来了?去给你爷爷磕头。” 那一夜,我们并肩跪到天亮。烛火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终于一样高。我第一次发现,他的鬓角已经白成一场无声的雪,而雪下面藏着我童年的全部答案。 【六】 三十岁,父亲在稻田边滑倒,右腿骨折。我赶回去时,他已做完手术,麻药未退,像一截被风吹散的枯木躺在白色病床上。我握住他布满老茧的手,忽然开口: “爸,那年你说‘别让它们咬你’,其实被咬得最狠的是你,对吧?” 他愣住,别过脸去,病房窗户外是一棵掉光叶子的老槐树。半晌,他声音沙哑:“你长大了,爸就放心了。” 那一刻,我再也绷不住,把脸埋进他掌心。泪水渗进他裂开的掌纹,像一场迟到的春雨,终于落进干涸的田垄。父亲用拇指笨拙地蹭我的头发,一如当年车站外,只是这回,他再不用担心眼泪会掉下来。 【尾声】 出院那天,我背着他下楼。他轻得像一捆晒干的稻草,呼吸落在我颈侧,温热而短促。走到医院门口,他忽然说:“放我下来,我自己走。”我弯腰,把他放下,像放下一个时代的债。 阳光很好,我们并肩往停车场走。影子被拉得很长,一长一短,却终于并肩。我伸手想扶他,他甩开,笑骂:“老子还没老到要你架着。” 我缩回手,却在心里牢牢接住——这一次,我不再误解他的倔强。那沉默的背影里,藏着一条从未说出口的河;我三十岁的此刻,终于学会在河水里看见自己的倒影。 风掠过,吹乱他花白的头发。我伸手,轻轻替他理好,像理平一段被岁月揉皱的往事。父亲没回头,却忽然哼起一首我五岁那年他哄我入睡的调子,跑调,却完整。 我跟着哼,两个男声在空气里磕磕绊绊,却终于合成同一首歌。那一刻,我明白:所谓父子,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也是一次迟到的相遇——我们曾在黑暗里彼此恨过、错过,如今又在光里重新认领对方。 而爱,始终在那里,像田埂下的鳝鱼,悄无声息,却滑过最黑的夜,咬出最亮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