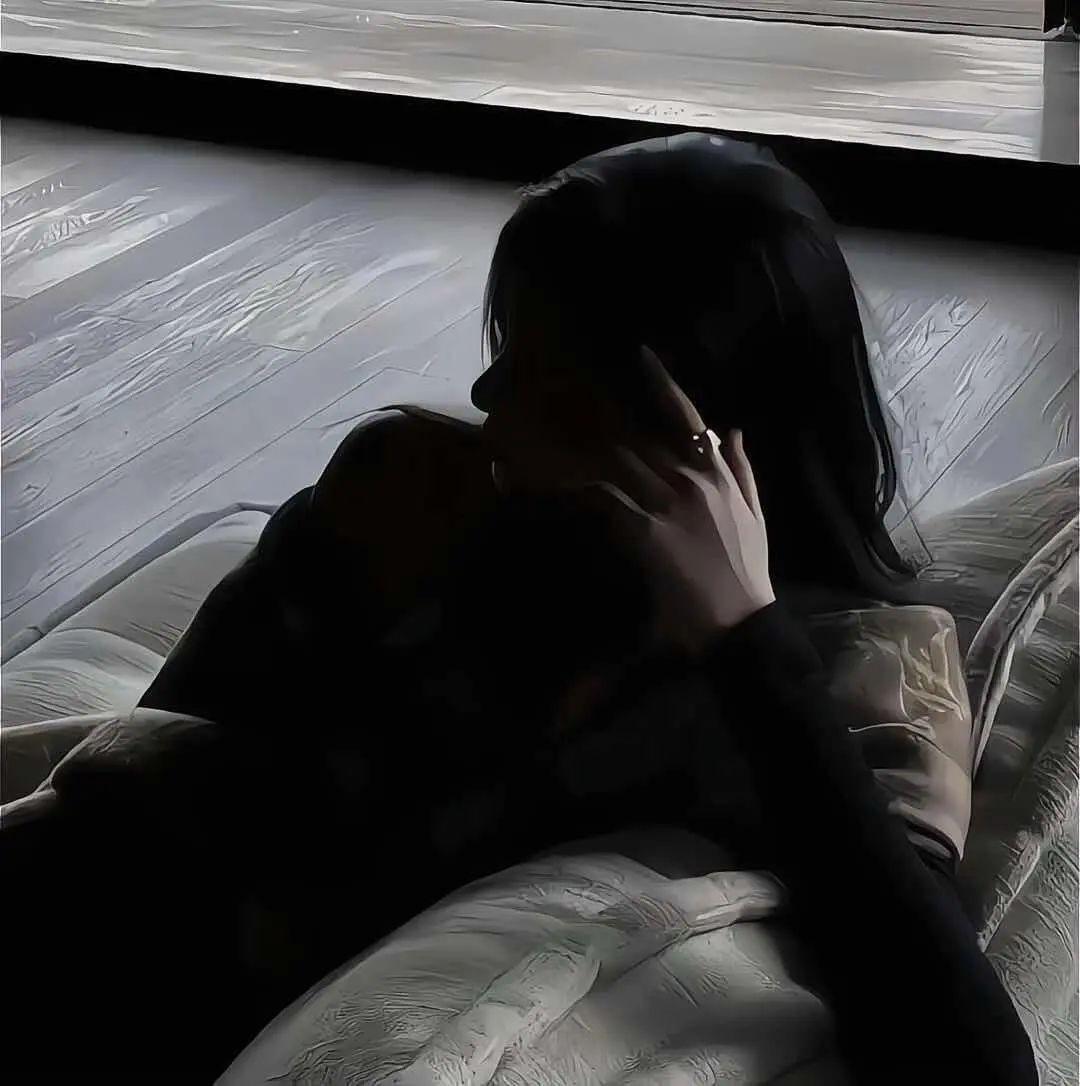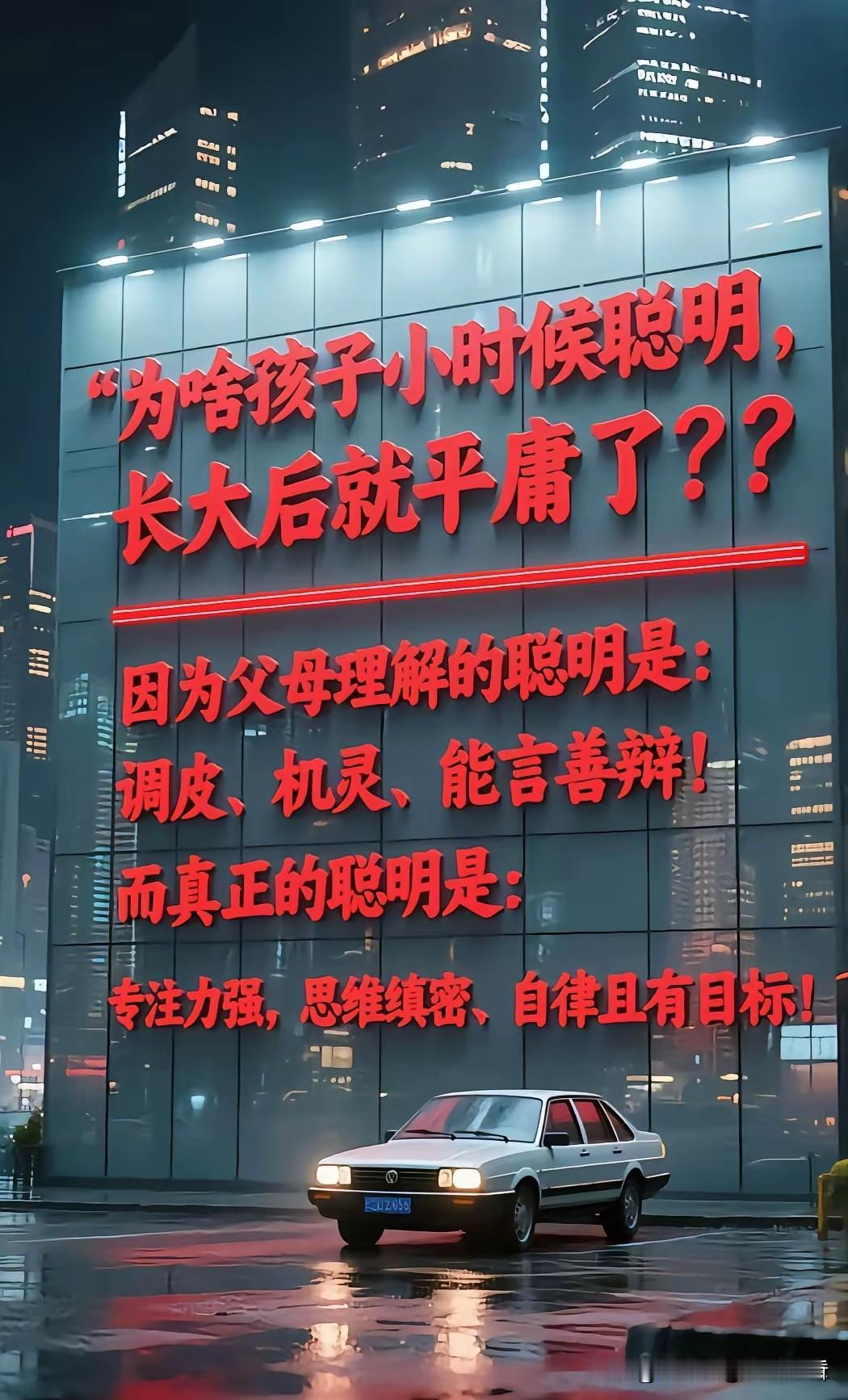想起二十几年前那个清晨,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在W学校宿舍最后一次见她。在此之前,我无数次乘车从公司去她学校找她,那是一段漫长的路程,我去找她,不过是希望她给我一个答案,告诉我为什么那么相爱的两个人,忽然就没有了音讯。有许多次,我在她学校外面的路旁彻夜守候,但她始终不肯见我。 后来她终于开了门,我抓着她的手说了很多话,她望着我,流着泪,没有说一句话。后来她离开宿舍去上课,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然后我才看到书桌上别人写给她的暧昧句子。在那一刻我明白了,她的沉默不过是给我一条路,让我离开。 此后二十多年间,我给她写过几封信,但她没有回信,我们失去了联系。 但我偶尔会梦见她,梦里她总穿一身白衣,还是二十几年前的样子,在熙攘人群里,我总能一眼就认出她,满心欢喜。梦里我不记得我们早已分开,她不说话,而我一刻不停地围着她转,眼睛无法离开她,想要为她做些什么,带她去一些地方看看。 原来,当初她给我一条路,放我走,二十几年来我一直走在那条路上,不过是越走越远,却从没有走开过。 直到那晚我望着北欧上空那轮明月,才明白是时候告诉自己:不纠缠,是最高级的体面。 想明白了这点,再回头看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无论爱情、婚姻、工作、生活、家庭,我从未摆脱过对别人、对自我的纠缠。 唐代高僧寒山与拾得有一段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之乎?”拾得答道:“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西方哲学也有类似观点,萨特强调“存在先于本质” 。这意味着人首先存在,然后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塑造自己的本质。当遇到一些人和一些事时,你拥有选择回应的绝对自由。 你可以选择与之纠缠,也可以选择转身离开,将精力投入到更能定义你人生价值的事情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写道:“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有些情绪、有些感受、有些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是无法彻底厘清的,纠缠其中,往往如同踏入一片沼泽。保持适当的沉默和距离反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尊重和理解,是对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物的守护。 人最终只能自己跟自己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