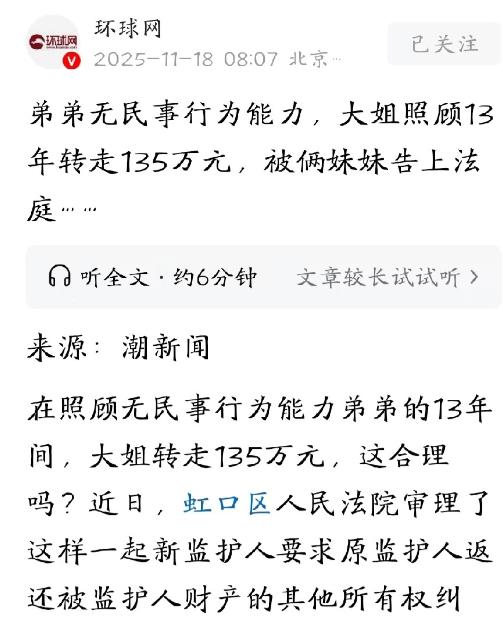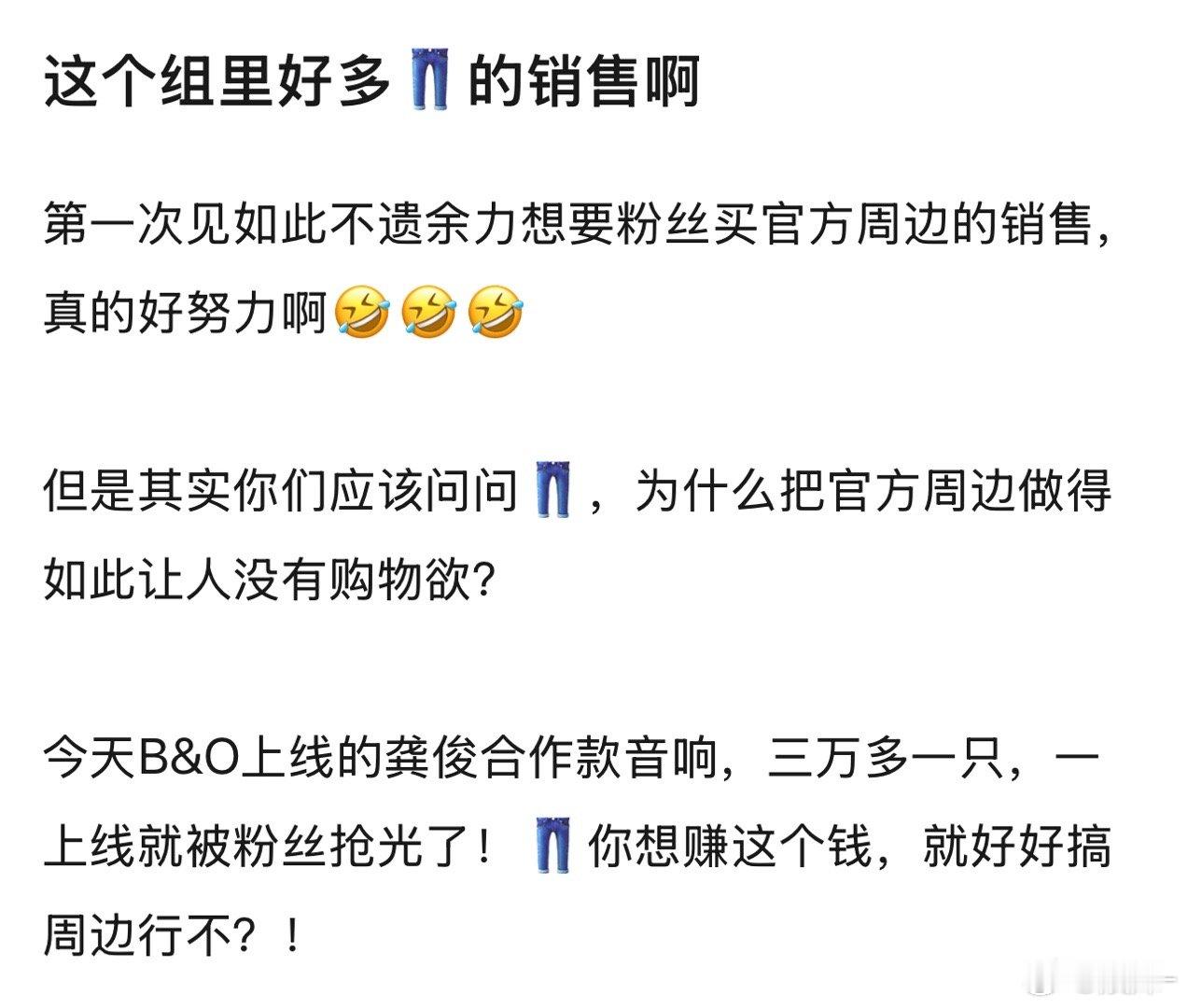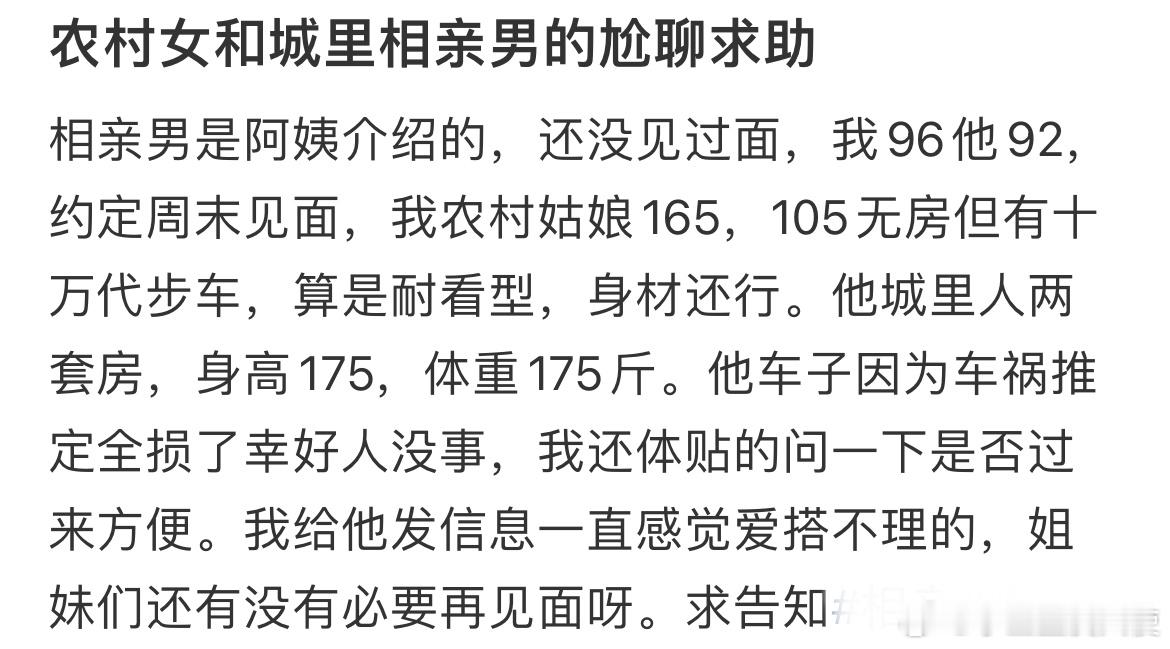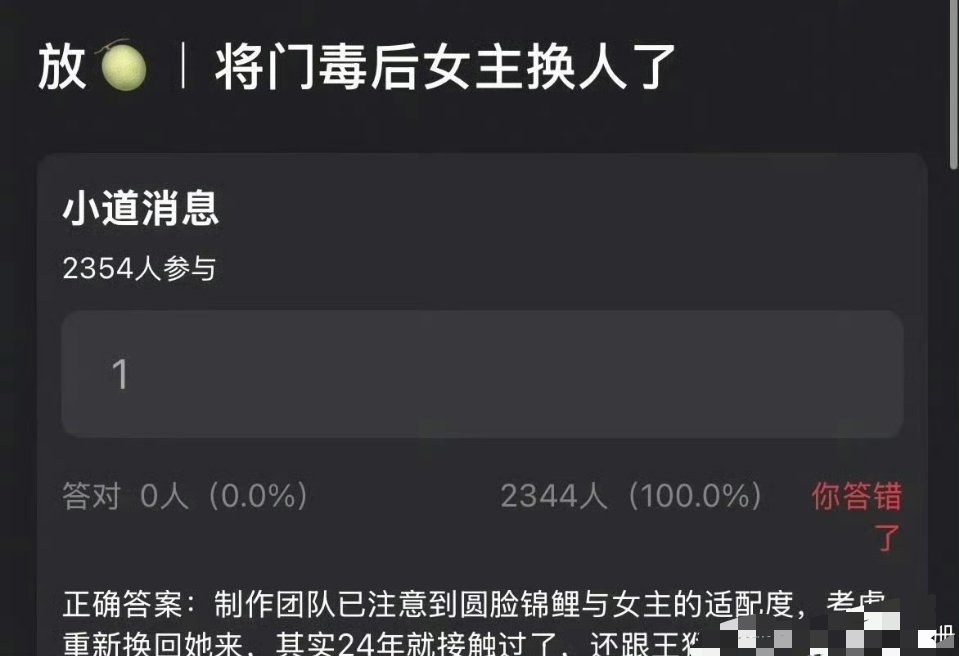上海,男子患精神分裂,未婚未育,退休后被姐姐和两个妹妹送到了疗养院长期居住。他每月退休金五六千,还攒了上百万元,都交给姐姐代为保管。谁知13年后,妹妹竟然发现姐姐悄悄从哥哥卡上转走了135万余元,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花在了哥哥身上,其他的全进了姐姐腰包。于是,两妹妹将姐姐告上法庭,要求立刻还钱。法院经过调查,却发现了更加震惊的真相。 上海的刘先生这辈子过得不容易,年轻时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没结婚也没孩子,父母走得早,身边最亲的人就是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 2010年他退休时,手里攒下了不少钱,加上每月五千多的退休金,还有六百块交通补助、三百块残疾人补助,每个季度再领三百块敬老补贴,日子本该不用愁。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姐妹三个商量后,把他送到了一家精神病疗养院,这里的费用单位还能报销大半,大家都觉得这样安排挺稳妥。 那时候姐妹间的感情还不错,刘先生的三个银行存折和所有证件,都交到了大姐手里保管,大姐还主动说要记账,让两个妹妹放心。 刘先生自己也信任这位最敬重的大姐,把所有积蓄都交了出去,没多想过后果。谁也没想到,这份信任一放就是十三年,最后竟成了亲情破裂的导火索。 亲情的裂痕,源于2023年父母遗留老房的拆迁事宜。 为分割拆迁补偿款,三姐妹多次争执不休,曾经的手足情谊在利益纠葛中荡然无存。 激烈的争吵中,两个妹妹想起了自己哥哥财产的管理。 此前因顾及亲情,她们从未核查过账目,可大姐在拆迁款分配中的强硬态度,让她们不得不怀疑:弟弟的财产是否也遭了算计? 疑虑之下,两个妹妹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首先向法院提出了监护权变更申请。 法院介入调查后发现,大姐多年来频繁从刘先生账户提取现金,个人财产与被监护人财产存在明显混同。 因此,法院最终裁定变更监护权,由两个妹妹担任刘先生的法定监护人。 当她们从大姐手中接过存折与证件,调取银行流水后,眼前的数字让二人脊背发凉,2010至2023年间,累计有135万余元从刘先生账户转出。 刘先生长期在疗养院生活,饮食起居均有专业医护负责,单位报销后个人所需承担的费用极少,135万元的支出显然不合常理。 面对妹妹们的质疑,大姐却显得理直气壮,称自己多年来悉心照料,不仅每月接弟弟外出居住,还专门租房并装修,日常饮食、就医等开销更是由她垫付,这些花费加起来并不少。 但法院调取的证据,却戳穿了这一说法,疗养院记录显示,十三年间刘先生仅被接离院区66次,年均不足六次,其中有三年因病情加重,医生明确禁止其离院。 大姐所说的出租屋,内部采用北欧风格装修,完全贴合其女儿的喜好,实际居住者也是大姐全家。 更令人愤慨的是,刘先生名下另有一套小房产,被大姐私自出租近十年,租金全部归入个人 法院审理过程中,明确《民法典》中的规定,监护人不能把财产用到被监护人以外的地方, 经法官核算,将刘先生十三年间所有合理开销尽数计入,总额不到50万元。 综合考量大姐确有过接送、探视等履职行为,法院最终判决其向刘先生返还70万元。 这起案件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引人深思,最为突出的,便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环节的财产监管盲区。 现实中,不少家庭仅凭亲情维系监护信任,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就给个别监护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 更有甚者,部分监护人对自身职责认知模糊,将“照料”等同于“获利”,擅自将被监护人财产视为己有。 对刘先生而言,70万元的返还固然挽回了经济损失,但十三年间被蒙骗的委屈与破碎的亲情,却再也无法复原。 这起事件也给所有家庭敲响警钟,监护权本质是责任而非特权。 即便是至亲之间,涉及财产保管也应明确边界,定期核对账目,建立必要的监督机制,避免让信任沦为贪婪的温床。 金钱损失尚有弥补可能,而凉透的人心,终究难以回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