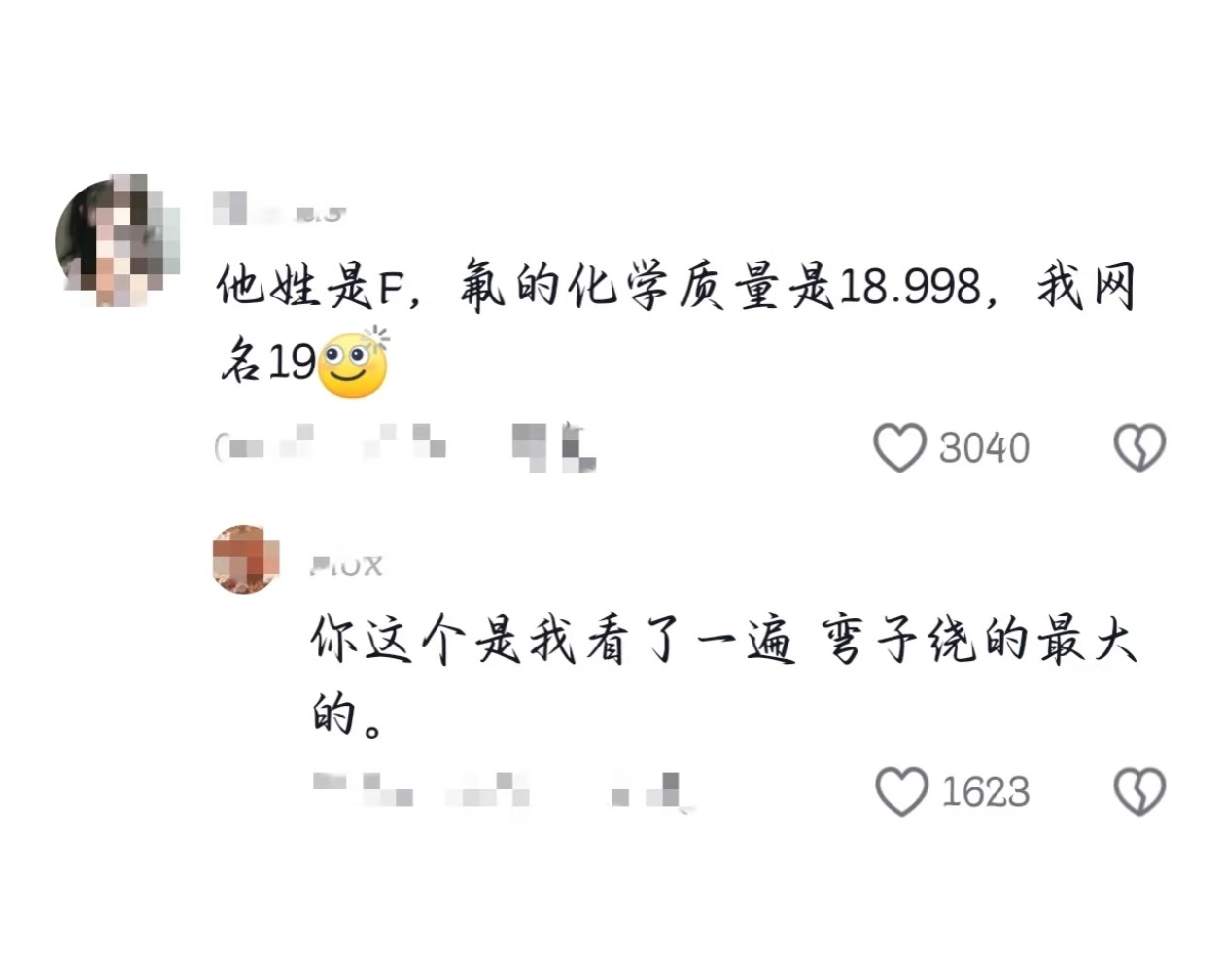美上将再度发问:“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击败中国?”哈佛教授查普曼直言不讳:“美国永远也无法打败中国! 哈佛神学院的大卫·查普曼教授可能说到了点子上,他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完全是那些工厂和技术,而是一种深层的文化。 这股劲儿,是一种有点“拧巴”的劲儿,你得从故事里去感受,晚清那会儿,左宗棠带兵去收复新疆,队伍里头,跟了三千个从天津来的货郎。他们不拿枪,就挑着俩竹篓,在茫茫大漠里硬是走了八千里。 他们的竹篓里,是针线、膏药和年画。那膏药,是给受伤的兵士用的;那年画,是让离家的兵士在帐篷里能瞅一眼,慰藉一下思乡的苦。 他们为什么去?想法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国家有事,我不能光顾自己”,后来仗打完了,很多人没回去,就在新疆扎下根,从挑着担子走,到开铺子坐着卖,慢慢建起了集市,通了商路。 还有东北抗日的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敌人剖开他的肚子,里面全是棉絮、树皮和草根。在零下四十度的绝境里,他想的居然是教战士们认字、吹口琴,用这一点点文明的火种,维系着大家作为“人”的尊严。 这种精神不是孤例,它是一种集体本能。98年洪水滔天,无数人手挽手筑成堤坝,汶川地动山摇,全国的车辆和物资自发地涌向那里。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是邻居之间在互相敲门送菜。 这种关键时刻抱团的习惯,是几千年的灾荒、战乱、迁徙给这个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生存密码。 它的源头在哪?也许藏在最古老的神话里。西方的神话多是神仙之间的恩怨,而我们的神话,主角是“人”。 是那只叫精卫的小鸟,明知不可能,也要衔着树枝去填平大海;是那个叫刑天的巨人,头被砍掉了,身体依然拿着盾牌和斧头在战斗。 这种传承,甚至不是靠课本硬灌的,而是妈妈教你包粽子,爷爷给你讲故事,是孩子们亲手捏一个英雄的泥像,给烈士献上一束花。这些日常的点滴,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管用。 任何外部力量,都很难真正改变中国人对“家”、对“春节”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还有强大的包容性,它不是排他的。就像当初的货郎,能把天津的月饼手艺和新疆的物产结合,变成伊犁的“卢佳月饼”。 “打败中国”是个伪命题。它的力量来自于一个活的、能自我修复的文化系统,这种力量的本质是持续性,而不是爆发速度。只要中国人还记得这些故事,这股劲就断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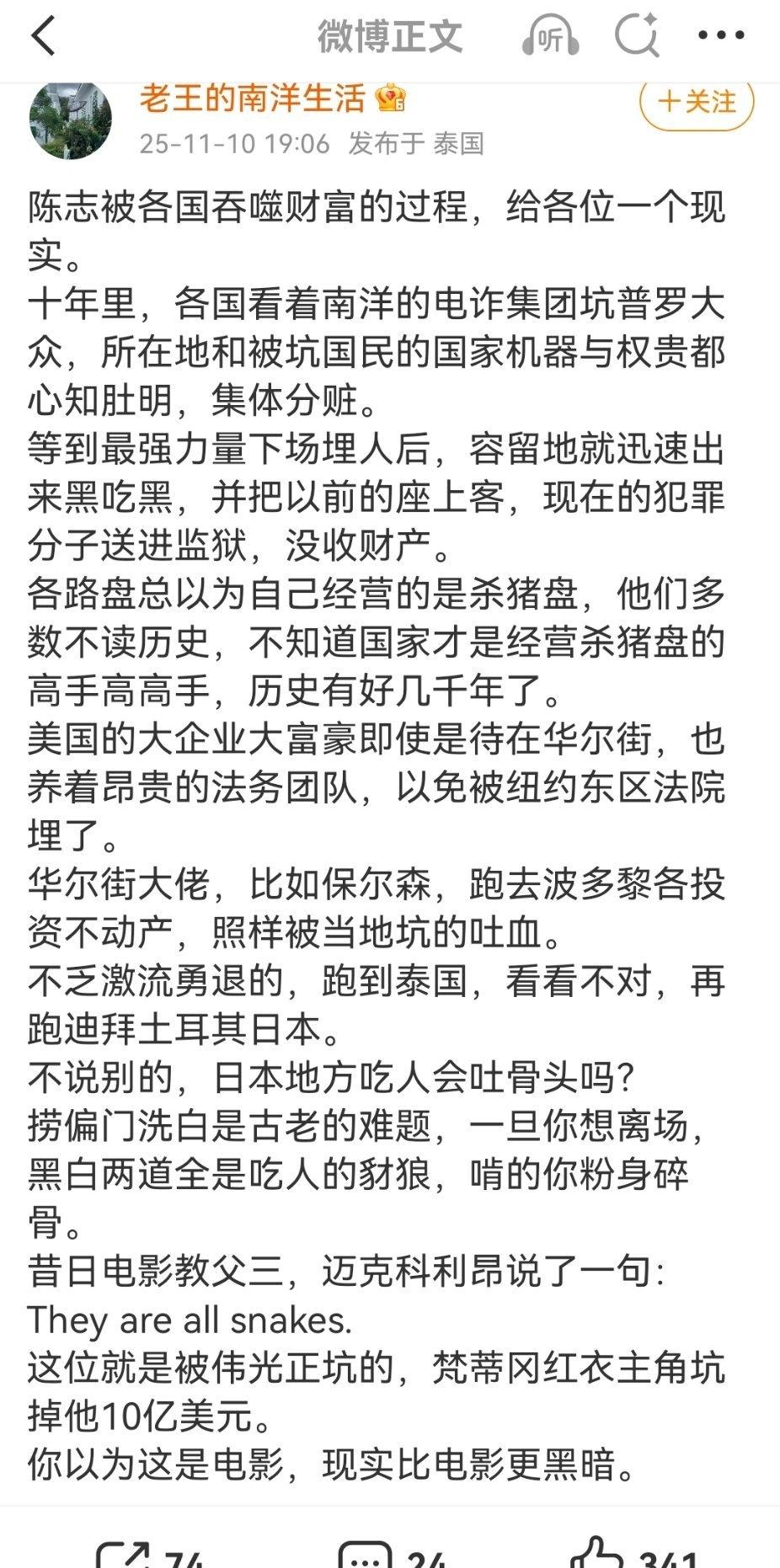

![重大突破![比心]帝国主义要傻眼了?现在,大喜报是一个接一个,前面的还没来得](http://image.uczzd.cn/8451757932031701065.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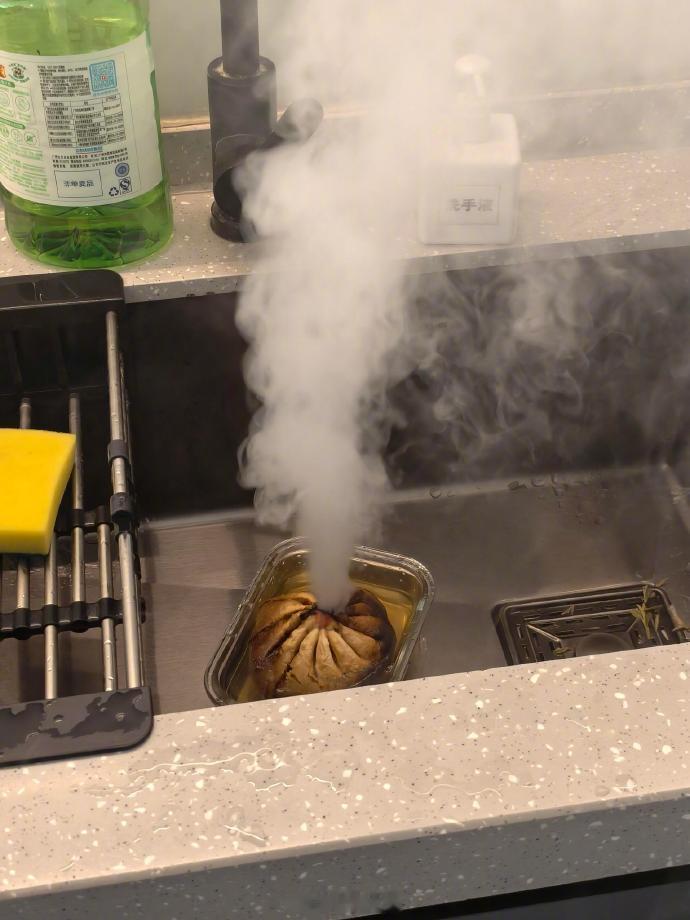

![武器装备赶不上,现在开始吹战术了,下一步是不是准备吹战斗意志?[笑着哭][笑c](http://image.uczzd.cn/13563788687411912063.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