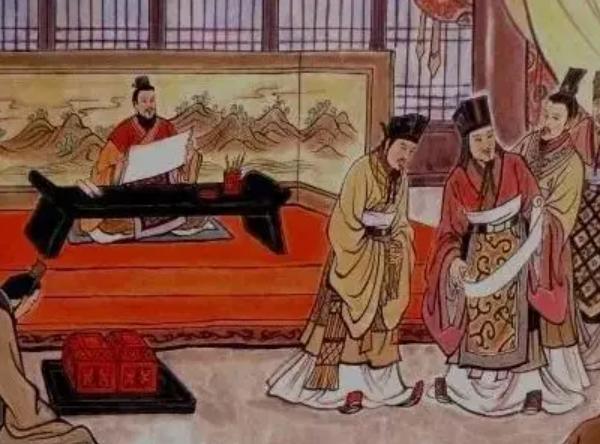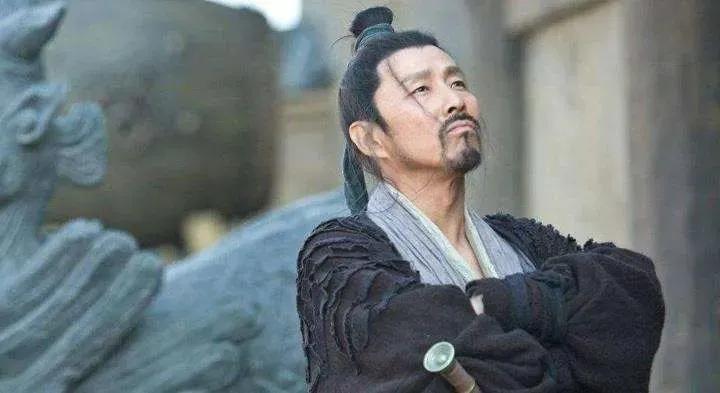公元前196年,皇后吕雉在长乐宫杀死韩信,并灭韩信三族。汉高祖刘邦闻讯显得很高兴,但又悲天悯人地问了一句:“临死之前韩信说了什么?” 公元前196年,长安,长乐宫钟室。 这一年,距离刘邦登基才刚过去六年,天下初定,但杀气未散。 皇后吕雉,这个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趁着丈夫刘邦在外亲征的空当,终于对那个她忌惮已久的男人下手了。 她联手“一知己”萧何,把韩信骗进宫。 一进长乐宫,韩信就发现不对劲,但晚了。 吕后根本没给他辩解的机会,直接将其截杀。 关于他怎么死的,野史传得更狠。据说,刘邦当年曾许诺韩信“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不杀”。 吕后就偏偏要破这个咒。她命人把韩信装进一个大布袋里,吊在钟室的房梁上,四周用布幔遮得严严实实,不见天日。然后,她没有用刀剑,而是让宫女们用削尖的竹签,将这位战无不胜的“兵仙”活活戳死。 一代军神,死法竟如此屈辱。 吕后还不解恨,没等刘邦的圣旨,她“矫诏”下令,火速“夷信三族”。韩信一家老小,血流成河。 几个月后,刘邦平叛归来,凯旋入城。 当他听说韩信的死讯时,史书记载了他当时的反应,四个字:“且喜且怜之。” 喜,是理所当然的。 刘邦心里那块最大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韩信是谁?是那个在刘邦最狼狈的时候,敢在阵前伸手要“假齐王”封号的人。那次要挟,几乎是把刀架在刘邦脖子上。虽然刘邦最后迫于形势,封他为“齐王”,但这根刺,早就扎下了。 后来削他兵权,从“齐王”贬为“楚王”,再从“楚王”贬为“淮阴侯”,软禁在长安。可只要韩信这人还活着,刘邦就睡不安稳。 现在,吕后帮他解决了这个心头大患,他当然高兴。 怜,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大汉江山,韩信至少打下了一半。这样一个旷世奇才,就这么死了,作为“老板”的刘邦,哪怕是装,也得装出一点“怜悯”之心。 可就在刘邦这“又喜又怜”的复杂情绪中,他鬼使神差地,问了吕后一句: “临死之前韩信说了什么?” 吕后倒是老实,她原话转述了: “信言恨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这话一出口,刘邦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刚才的“喜”和“怜”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恐惧。 他顾不上皇后的感受,也顾不上君王的体面,立马咆哮着下了一道命令: “马上把蒯彻抓来,我要亲自烹了他!” 蒯彻,范阳人,汉初最顶级的纵横家、战略忽悠家。 他给韩信出的那个计,就是汉初最大的“阳谋”:“三分天下”。 这事儿,得说回韩信灭齐之后。 当时,刘邦被项羽追着打,而韩信呢“明修栈道”,一路开挂,灭魏、亡赵、降燕、收代,最后连齐国也拿下了。 此时的韩信,手握最精锐的部队,占据着最富庶的地盘。 蒯彻,就是这时候登场的。 他给韩信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老板刘邦和对手项羽,在荥阳一线打得筋疲力尽,谁也吃不掉谁。而你韩信,就是那个决定天平倒向的终极砝码。 接着,蒯彻抛出了他的“灵魂之计”: “将军不如叛汉自立,居于楚汉之间,和他们三分天下!待时机成熟,再一统江山,帝王之业可成!” 为了说服韩信,蒯彻还搞了个玄的。他对韩信说:“我学过看相。” 韩信说:“那先生帮我看看?” 蒯彻说:“看将军的面相,不过封侯而已,而且还伴随着危险。但看将军的“背”相,却显贵无比。” 可韩信是怎么回答的? 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拒绝了。理由很朴素: “汉王待我不薄。他把自己的车给我坐,自己的衣服给我穿,自己的饭给我吃。我不能背叛他。” 这就是韩信的致命弱点。 他是个百分之百的军事天才,但在政治上,他单纯得像个“小白”。 他重情义,却忘了帝王家,最不缺的就是情义,最看重的,只有权力。 蒯彻一看韩信救不活了,叹了口气。他知道,这事儿迟早败露,自己也得玩完。于是,他赶紧装疯卖傻,跑路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长乐宫外,刘邦听到韩信遗言的那一刻。 他为什么怕? 他怕的是,韩信直到临死前,才终于后悔了。 他怕的是,韩信终于承认了,蒯彻的计策是对的。 这等于是在告诉刘邦:你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不是你多厉害,只是我韩信当年一时心软,念了旧情! 刘邦的江山,是韩信“施舍”的。 这比韩信直接造反,还让刘邦难受。 刘邦更怕的是,他意识到,这个叫蒯彻的人,竟然能把天下大势看得如此透彻。他能 怂恿韩信第一次,就能怂恿第二次。 万一,他现在又去怂恿彭越,或者英布呢? 这个“计谋”本身,比十万大军还可怕。 所以,刘邦的反应才是:“马上抓蒯彻来!我要烹了他!” 他要杀的,不只是蒯彻这个人,更是那个“三分天下”的可怕念头。 韩信之死,从他拒绝蒯彻的那一刻,就已注定。 他死于吕后的狠毒,死于萧何的背叛,但归根结底,他死于他那“功高震主”的实力,和他那“不合时宜”的忠诚。 而刘邦,那个“且喜且怜”的皇帝,在听到韩信最后遗言时露出的恐惧,才撕下了“君臣相得”的最后一点温情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