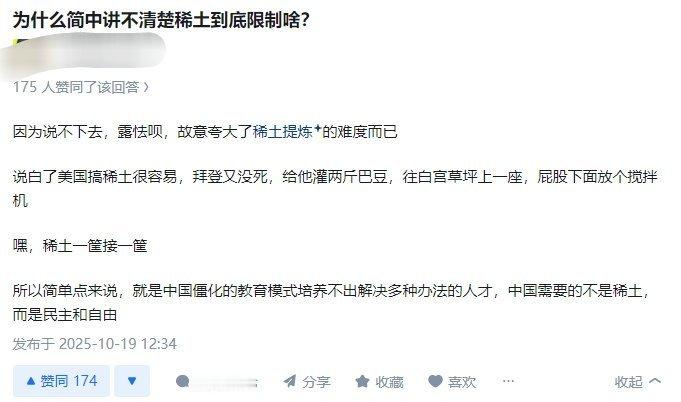不查不知道,原来我国之所以在稀土方面占据如此巨大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名叫徐光宪的大科学家,“从0到1",创造性地开创出了一种全新的“串级萃取法”,这才使得我们开始在稀土产业独占鳌头。 上世纪 70 年代前,咱们国家明明揣着世界 37% 的稀土储量,却连怎么把这些宝贝拆分开都不会。稀土里的 17 种元素化学性质太像了,尤其是镨和钕,简直比孪生兄弟还难分辨,国际上能用上的分离方法就两种:离子交换法和分级结晶法。 可这俩法子又笨又贵,分离周期长得要命,提纯纯度还特别低,轻稀土最多到 98%,重稀土才刚过 90%。 那时候咱们没办法,只能把刚挖出来的稀土原矿低价卖给外国人,一斤卖不了几个钱,转头再花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钱,买人家提纯好的产品。你说这窝囊不窝囊?就像捧着金饭碗要饭,想想都堵得慌。 1972 年国家给徐院士派了紧急任务,要分离镨和钕,这活儿国际上都没人能搞定,可徐院士就认死理:“中国是稀土大国,总卖原料心里不舒服,再难也要上。” 那年徐院士已经年过半百,为了这事儿干脆改了研究方向,一头扎进了实验室。那会儿条件差得很,没有先进设备,他白天就靠 “摇漏斗” 模拟实验,胳膊摇酸了也不停,晚上就趴在桌上算数据,经常一熬就是通宵。 他夫人高小霞院士本来有自己的研究方向,看着丈夫这么拼,干脆放下手头的活儿,陪着他一起干,夫妻俩成了科研路上的 “比翼鸟”。 功夫不负有心人,徐院士还真摸出了门道,他发明了季铵盐 - DTPA “推拉” 萃取体系,一下把镨钕的分离系数从 1.4 提到了 4 以上,这在当时就是世界纪录。 更厉害的是,他发现国外流行的阿尔德斯串级萃取理论根本不适用,干脆自己重新推导公式,硬生生创出了全新的串级萃取理论,这可不是小修小补,是实打实的从 0 到 1 的突破。 1974 年,徐院士带着自己的理论去了包头稀土三厂,跟工人们同吃同住,在满是粉尘的厂房里搞试验。 1975 年第一条工业生产线一投产,整个行业都炸了锅:以前一百天才能出一批货,现在七天就搞定,效率翻了近十四倍;纯度更是从以前的勉强及格冲到了 99.99%,最高能到 99.9989%,比国外最好的技术还高出一大截。 上海跃龙厂是第一个敢试的,以前的生产线又笨重又低效,换了串级萃取工艺后,一排排萃取箱连起来跟流水线似的,原料从这头进去,不同纯度的稀土就从那头自动流出来,生产成本直接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 徐院士从来没把技术藏着掖着,从 1978 年开始办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免费把技术教给全国各地的稀土厂,这一办就办到 1995 年。 他还琢磨出 “一步放大” 技术,不用经过小试、扩试,直接就能用到工业生产上,把复杂的工艺变得跟 “傻瓜操作” 似的,工人只要输几个数据,流水线就能自动运转。 就这么着,全国的稀土厂都用上了这神仙技术,咱们的稀土产业一下就支棱起来了。到 90 年代,全球 90% 以上的高纯稀土都是中国产的,国际上都管这叫 “中国冲击”。 那些以前垄断市场的外国巨头,美国钼公司只能减产,日本的厂子干脆停产,法国罗地亚公司没办法,只能跑来求着跟咱们合作,以前的憋屈劲儿总算彻底出了。 现在更不用说了,咱们的稀土精炼产能占全球 92%,39 所高校培养着世界 70% 的稀土人才,技术早就更新到 “四代半” 了,17 种稀土元素能在流水线上依次剥离,纯度最高能到 99.999996%,相当于在 1 亿吨矿石里只挑得出 1 克杂质。 反观国外,到现在都没追上咱们 1975 年的水平。美国最大的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2024 年折腾了半天,镨钕纯度才 99.1% 到 99.9%,跟咱们的 99.99% 没法比,重稀土更是连分离的门都摸不着。 成本更是差得离谱,咱们每吨分离成本才 3 万元,美国却要 5.6 万美元,这哪儿是生产,简直是用黄金的价钱炼铁,根本没法跟咱们竞争。 就说 F-35 战机的雷达磁体,得用 99.999% 的钕元素,美国纯度不够,磁体良品率直接比咱们低 15%,这就是技术差距带来的硬伤。 徐院士这辈子心里都装着稀土,2008 年拿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时候,穿的还是 30 年前的深蓝色旧西装,领完奖转身就把 500 万奖金全捐给了科研。 后来看到国内企业为了抢生意打价格战,把稀土贱卖出去,他急得两次上书国务院,呼吁保护稀土资源。国家后来出台的稀土保护政策,里面都藏着老院士的心血。 说句实在话,咱们现在能在稀土领域说一不二,真不是靠资源多,核心就是徐光宪院士当年创下的串级萃取法。 这技术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没有它,咱们的稀土到现在可能还在当土卖。徐院士这辈子,把学问和家国情怀拧在了一起,用一辈子的心血给国家铺了条宽路,这样的科学家,才是咱们该记在心里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