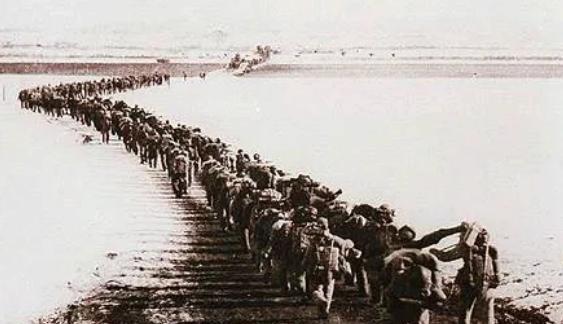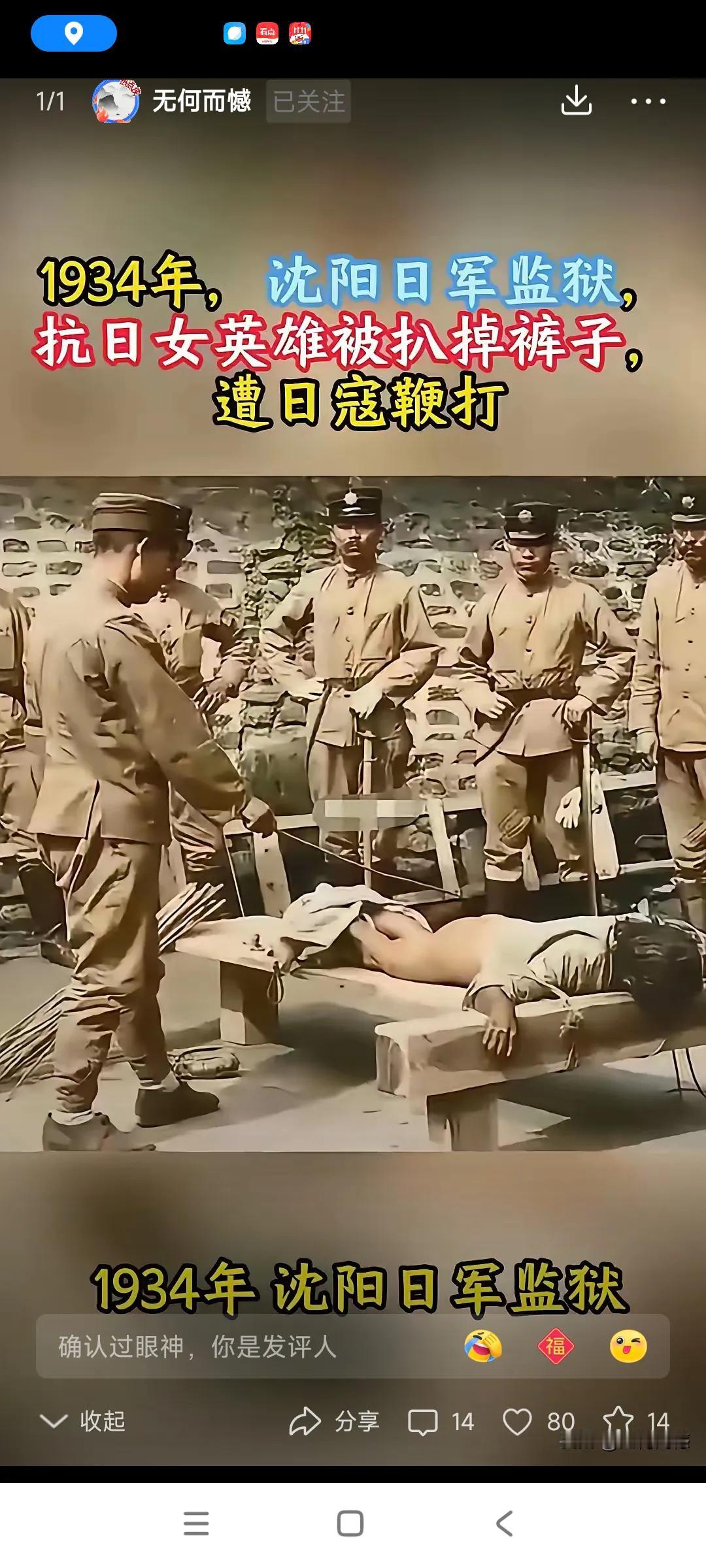1945年,日军被苏联红军被押往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后来,活下来的日军战俘哭着回忆道:“苏联军医用手抓一抓肉,然后肉多肉厚的就要被选去干最苦最累的活……” 1945年8月,那真是个风云突变的月份。美国人两颗原子弹下去,日本本土都懵了。而在咱们中国的东北,斯大林那边也没闲着。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着150多万苏联红军,像一股钢铁洪流,从东、西、北三个方向猛扑过来。盘踞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曾经号称“皇军之花”,结果呢?在这股绝对的力量面前,几乎是摧枯拉朽,几天功夫就散架了。 8月15号,裕仁天皇宣布投降。这一下,散布在亚洲各地的700多万日军,都得放下武器。在东北,苏联人一口气就俘虏了将近60万的日军官兵。这么多张嘴,这么多人,怎么处理?这成了苏联人一个现实的问题。 说实话,当时的苏联,比谁都缺人。一场卫国战争打下来,苏联损失了2700多万人口,绝大部分都是青壮年男性。国家被打得稀巴烂,百废待兴,可到处都缺劳动力。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但就是没人去开发。这下好了,瞌睡送来了枕头,现成的60万精壮劳力送上了门。 于是,斯大林一道命令,从1945年8月23号开始,一列列闷罐火车就把这些日本战俘呜呜地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拉。总共拉走了50多万,剩下那几万老弱病残和伪军,苏联人看不上,就地交给了我们处理。 刚开始,有些日本军官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那些高级军官,投降的时候还带着不少好东西。根据资料记载,第一批被送到坦波夫州的5000名关東軍军官,随身带着轻便的毛垫、枕头、好几身睡衣,甚至还有照相机、画笔和做饭团的调料。他们以为战俘营也得讲点“日内瓦公约”吧? 结果火车一到站,当地的苏联老百姓早就等着了。一位市民后来回忆说:“我们等了好几天,日本人刚下车,我们所有人都扑了上去。”那场面,跟抢东西没两样,瞬间就把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军官们扒得连条像样的裤子都不剩。那一刻,他们才明白,战俘的尊严,一文不值。 到了西伯利亚,真正的考验才开始。第一个就是冷。咱们东北的冬天够冷了吧?西伯利亚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是家常便饭。可战俘们住的是什么呢?据一个叫清水芳夫的战俘回忆,他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又黑又潮,几根原木柱子都被人手摸得油光发亮。这种地方,夏天还好,冬天简直就是个冰窖。每年冬天,都有大批的战俘,在睡梦中就被活活冻死。 第二个是饿。苏联自己战后物资都极度匮乏,哪有那么多粮食给你战俘吃。每天的伙食,基本上就是用饭盒盖子盛的一点稀粥,清汤寡水,饿得人前胸贴后背。 最要命的,是第三个——累。苏联人抓他们来,可不是为了养着玩的,是要他们当牛做马,去干最繁重、最危险的活。开矿、伐木、修铁路、建水坝,这些都是消耗最大、体力要求最高的领域。 说到这,就得提那个让所有幸存日军都毛骨悚然的“选拔”方式了。 每个月,苏联方面都会对战俘进行一次体检。所有人被命令脱光衣服,排成四队,站在西伯利亚的寒风里。即便是冬天,也得光着身子冻得直哆嗦。然后,苏联军医会挨个走过来,不听心跳,不量血压,就一个动作——伸出手,在你大腿或者屁股上,使劲抓一把肉。 军医会根据手感,也就是肉的厚薄,把战俘分成几个等级。那些身上还有点肉,抓起来“肉多肉厚”的,被划为一等。接下来的日子,你将被派去干最苦最累的活。下矿井、扛圆木,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耗体力,哪里就有你的身影。而那些瘦得皮包骨头,一把抓过去只有一层皮的,反而会被分去做一些相对轻松的活。 这是一种极其残酷又“高效”的筛选。它把人彻底当成了工具,用最原始的方式来评估你的“使用价值”。很多战俘后来哭着说,每次体检都希望自己能瘦一点,再瘦一点。因为在西伯利亚,强壮不是资本,而是通往死亡的快车票。 在这种饥寒交迫和超强度的劳役下,死亡率高得惊人。所以,幸存者们都管西伯利亚叫“地狱”。 尸体的处理方式也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冷酷。冬天冻死的战俘,尸体僵硬得像石头。处理尸体的人,根本不会小心翼翼,经常在搬运和埋葬的过程中,把尸体弄得支离破碎。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的命运都一样。苏联人很务实,战俘里要是有工程师、医生或者技术人员,待遇就会好很多。他们会被安排到工厂车间,甚至能领到几百卢布的工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还有些脑子活络的,开始拼命学俄语。因为苏联人缺翻译,只要你会说俄语,就能免除体力劳动,去做采购之类的差事,还能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 绝大部分战俘的苦难,一直持续到1956年。那一年,苏日关系正常化,苏联才开始陆续遣返这些战俘。当他们踏上日本国土时,距离他们被俘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来时浩浩荡荡50多万,回去的只剩下44万多人。那消失的几万人,就永远地埋在了西伯利亚的冻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