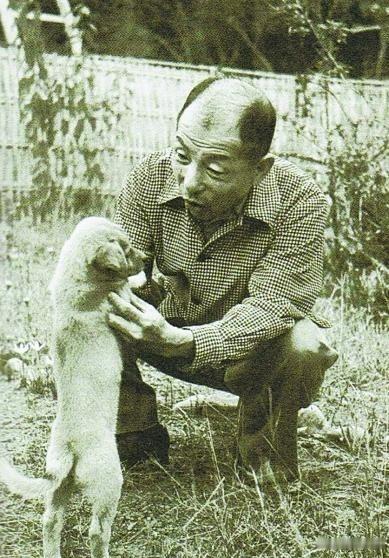1975年那个电闪雷鸣的晚上,张学良听完电话内容,盯着窗外的雨整整愣了一小时。 雨砸在井上温泉疗养所的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声响混着远处的雷声,把夜里的静衬得更沉。他握着听筒的手没松,指节都有点发白,张群在电话那头说的“先生昨夜走了”还在耳边绕——这“先生”,全天下都知道是蒋介石。 屋里没开灯,只有闪电劈下来的瞬间,能看清他脸上的纹路。那是54岁的脸,却比同龄人显老,鬓角的白头发在光里晃得人眼酸。他想起1958年那次见面,在台北士林官邸的书房,蒋介石坐在红木椅子上,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最后只说了句“你头秃了”。他当时还笑了笑,回了句“委员长,你老了”。谁能想到,那竟是两人这辈子最后一次面对面说话。 雷声又滚过来,震得窗玻璃嗡嗡响。张学良慢慢放下听筒,指尖蹭过冰凉的机身,才发觉手心全是汗。这是他被“管束”的第39年了,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南京,他就没真正自由过。先是在大陆的雪窦山、阳明洞,后来跟着到了台湾,最后被安置在这山里的疗养所。说是疗养,其实跟关着没两样——院门外常年站着岗哨,连他给老部下写封贺婚信,都得先经看守检查,有时写了也寄不出去。 有人说他日子过得滋润,有厨师专门做饭,佣人收拾屋子,宋美龄还会让人定期给他空运咖啡和雪茄。可张学良自己清楚,再好的东西,填不满没自由的空。他年轻时是东北军少帅,手里握着几十万兵权,在东北地界上跺跺脚都能震三震。当年为了逼蒋联共抗日,他敢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发动西安事变,可如今呢?他连走出这个院子都要报备,每天只能靠听收音机、翻旧报纸,猜一猜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雨还没停,顺着屋檐往下淌,像一道帘子把院子遮得严严实实。张学良走到窗边,手指隔着玻璃碰了碰外面的雨,冰凉的触感让他打了个激灵。他没去想蒋介石的死会不会改变自己的处境,也没去怨当年的选择——那些念头早在日复一日的等待里磨淡了。他只是想起小时候,父亲张作霖还在时,东北的夏天也常下这样的暴雨,那时他还跟着士兵在操场上练骑马,风刮在脸上都是热的。 天快亮的时候,雨势小了点,远处的山影慢慢显出来。张学良转身走回床边,桌上的搪瓷杯里还剩半杯凉茶,是昨晚睡前倒的。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凉得扎嗓子,却让他清醒了不少。门外传来岗哨换班的脚步声,很轻,却听得清清楚楚——新的一天来了,他的日子,还得照着老样子过。 几天后,他跟着赵一荻去国父纪念馆吊唁。穿着深色的中山装,站在蒋介石的灵前,他没说话,只是对着棺椁鞠了三个躬。后来侍从递来纸笔,他提笔写了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分,宛如仇雠”。十六个字,把他和蒋介石几十年的纠葛,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从当面交锋到隔空相望,全装进去了。 吊唁回来的路上,车开得很慢,窗外的稻田绿油油的。赵一荻靠在他肩上,轻声问“心里还好吗”,他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望着窗外掠过的树影。他知道,蒋介石走了,可困住他的那道无形的墙,还没倒。往后的日子,还得在这山里,听着雨声,等着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自由。 后来有人问过他,那天晚上愣在窗前的一小时,到底在想什么。他想了想,笑着说“忘了,早记不清了”。可那笑容里的涩,只有经历过几十年等待的人,才能品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