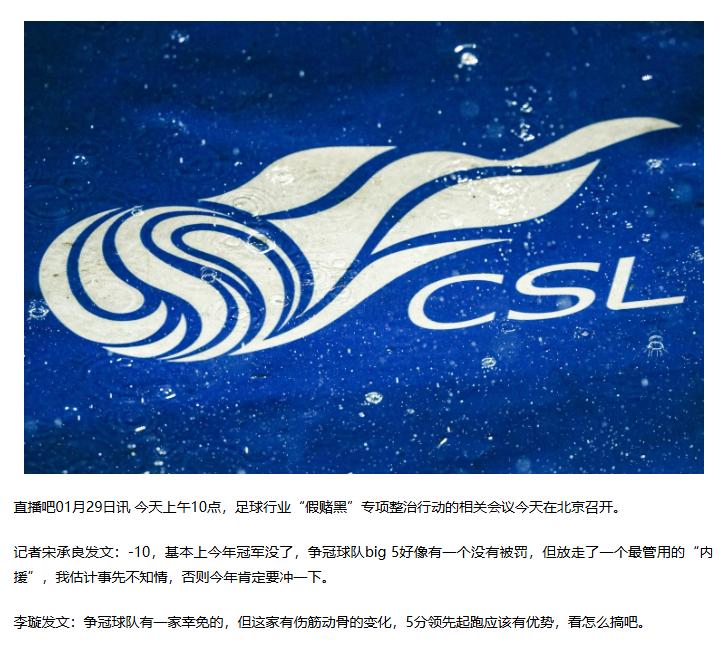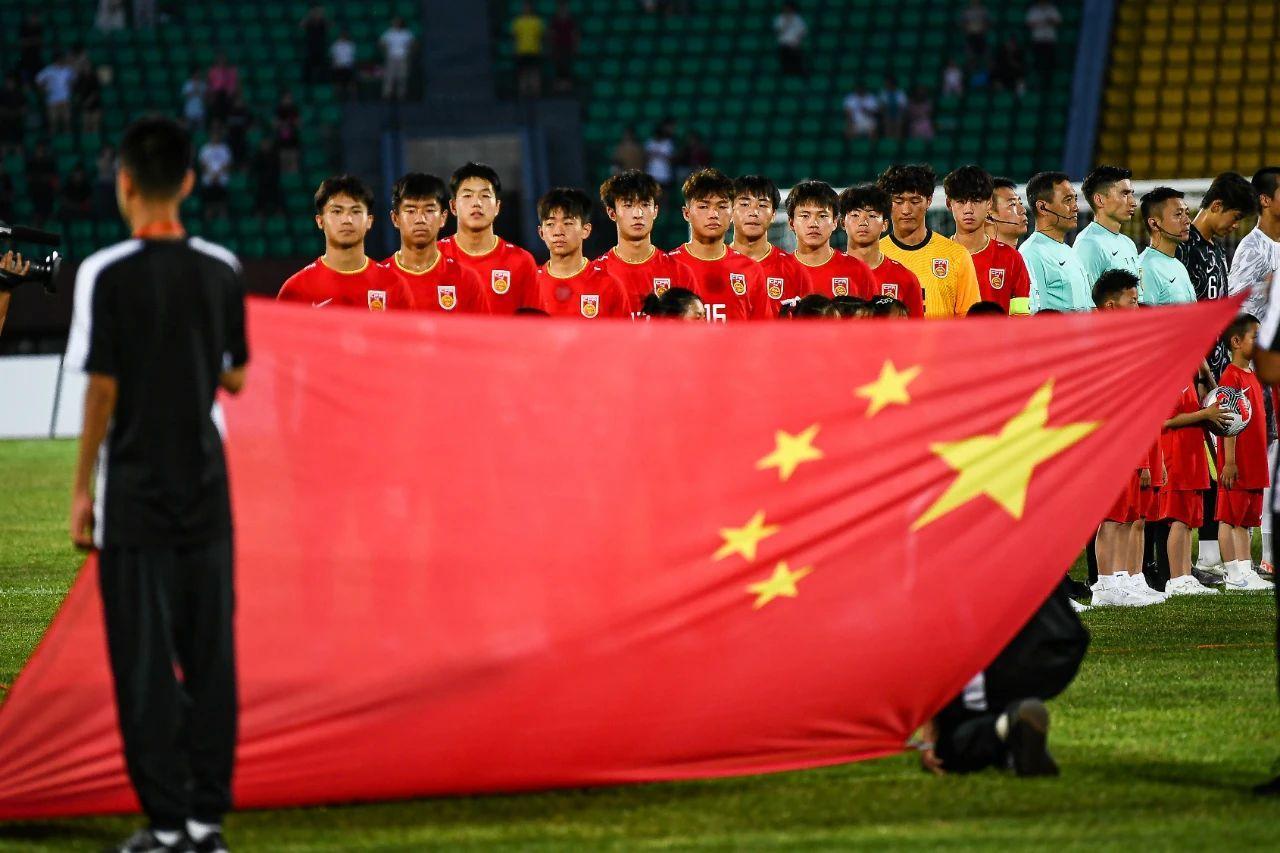1995年11月的成都,麻辣鲜香的烟火气与足球赛场的热血激情交织涌动。中国足球史上这段极具冲击力的篇章,被当时《足球》报总编严俊君定义为“保卫成都”,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保卫成都”并非单场赛事,而是一系列牵动人心的保级大战,其中川青对决、川军交锋两役尤为惊心动魄。杨为健,这个离开青岛后鲜为人知的球员,险些因一粒进球成为成都这座城市的“公敌”。 多年后,他与姚夏在青岛重逢,姚夏半开玩笑地回忆:“当初要是我没把那个球追回来,你恐怕真没法安全离开成都。”八年后的同一日,成都加州酒店大堂里,杨为健感慨万千:“没想到我在成都还这么有知名度,可那年我们球队终究还是降级了。” 八一队造访成都参赛时,入住的是军区附近的一家招待所,远眺便能望见珠峰宾馆的轮廓。时光回溯到1995年最后一战的前夜,曾有成都球迷怀揣一捆人民币直奔八一队驻地,哼着《智取威虎山》中“自己的队伍来到了面前”的唱段,想用这份特殊的“诚意”争取对手手下留情。 保级之夜,无数球迷涌向珠峰宾馆,整夜不停呼喊着“谢谢解放军”。而到了2003年川军再度对阵八一队的当晚,八一队即将整体撤编的消息传来,招待所内瞬间陷入一片死寂,往昔喧嚣荡然无存。 为了一张比赛门票,球迷们在成体中心外搭起棚子,整整排队三天三夜,始终秩序井然。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手持话筒爬上桌子,向现场球迷郑重承诺:“球迷同志们,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满足大家的愿望,让每一个人都能进场看球。” 川军那场关键之战,能容纳四万多人的体育场硬生生挤进了六万名观众。在当时的成都,无需排队就能弄到一张球票,俨然成了“有门路、吃得开”的象征。然而六年后的春天,杨肇基在全兴队的转让协议上签下名字,走出全兴大厦时,看着徐明等人的车辆远去,他转身面向记者,语气中满是近乎绝望的恳求:“别再责怪我了。” 与八一队的比赛中场休息时,我昔日的记者同仁许勇,悄悄将一块此前被裁判要求翟飚取下的玉佩,重新递到了他手中。比赛仅剩最后十分钟,魏群高声呐喊:“时间不多了!”话音刚落,翟飚便顶进了职业生涯中最具纪念意义的一粒头球。他紧攥着玉佩冲向许勇,激动得语无伦次:“勇哥!勇哥!”同样是六年后,许勇将四川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职位,移交到了一位名叫曲庆才的大连人手中。 1995年的成都,正是被这样一群人用热血与执念守护着。这段往事,几乎成了中国足球联赛史上的一段传奇。 成都本是座极致休闲的城市,却因足球被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万众瞩目的“战场”。多年后,成都的街头巷尾、新闻版面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献忠屠城、文革时期的武斗,再到1995年的成都保卫战,堪称这座城市走向极端化的三大节点。而在这之后,成都才渐渐回归往日的恬静与闲适。成体中心所在的后子门,曾是文革时期被炸毁后修建“万岁展览馆”的后门,默默见证了这一切的变迁。 成都终究被“保卫”下来,其金牌赛场之名传遍全国。但这场保卫战,也成为后来“球迷集体无原则支持”的开端。为了宣泄心中纯粹的情感,成都球迷可以容忍裁判的争议判罚,看着吉林队被气得消极比赛数十分钟,对“6比0”的耻辱比分毫无波澜,反倒视作荣耀;可以在甲B联赛出现11比2的悬殊比分时一笑而过,觉得理所当然;也可以痛骂彭晓方一脚将当年的“恩人”八一队踢入降级深渊,让少数人“心太软”的歌声淹没在漫天的鼓噪之中。 在西方,足球是产业工人的运动,遵循着标准化的齿轮式管理模式;而在成都,足球更像是闲适人群的一种消费,追求的是随心所欲、合乎心意的情感宣泄。当年保级战中的城市英雄们后来各奔东西,四川足球尚未登上顶峰便从1995年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也正是这种无原则的狂热追捧,纵容了日后联赛中近在眼前的“黑幕”与“假球”。当球迷们因联赛的种种乱象心寒不已,纷纷远离成体中心时,成都终究没能守住人们心中那份纯粹的足球热爱。11月26日,城市各处的人们依旧沉浸在日常的玩乐之中,后子门外,一小撮球迷围着徐弘欢呼雀跃,用当年最为热烈的方式庆祝所谓“第二次成都保卫战的胜利”,但这份热闹,早已不及1995年那般万众一心的盛况。——2003年12月25日《竞赛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