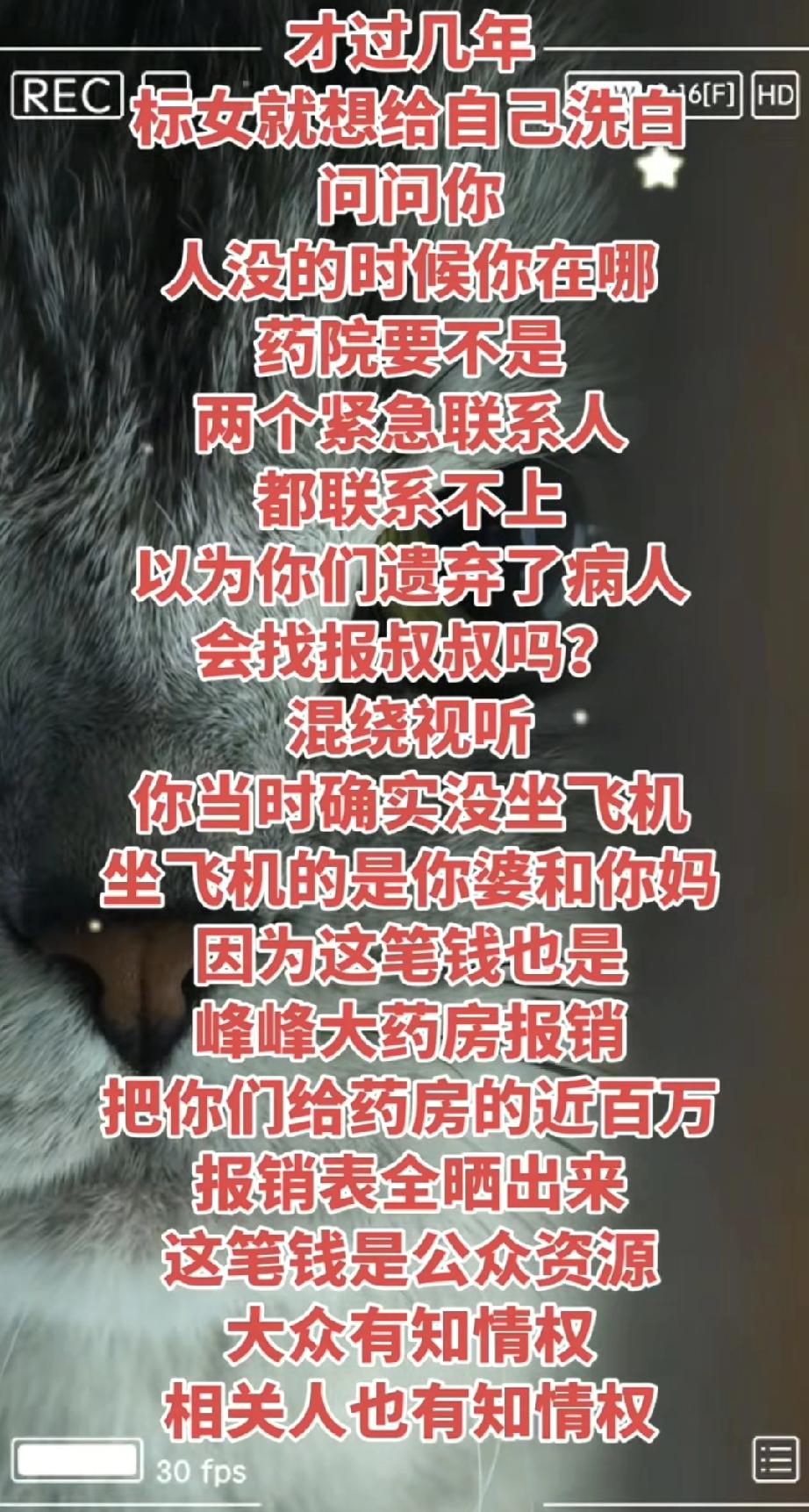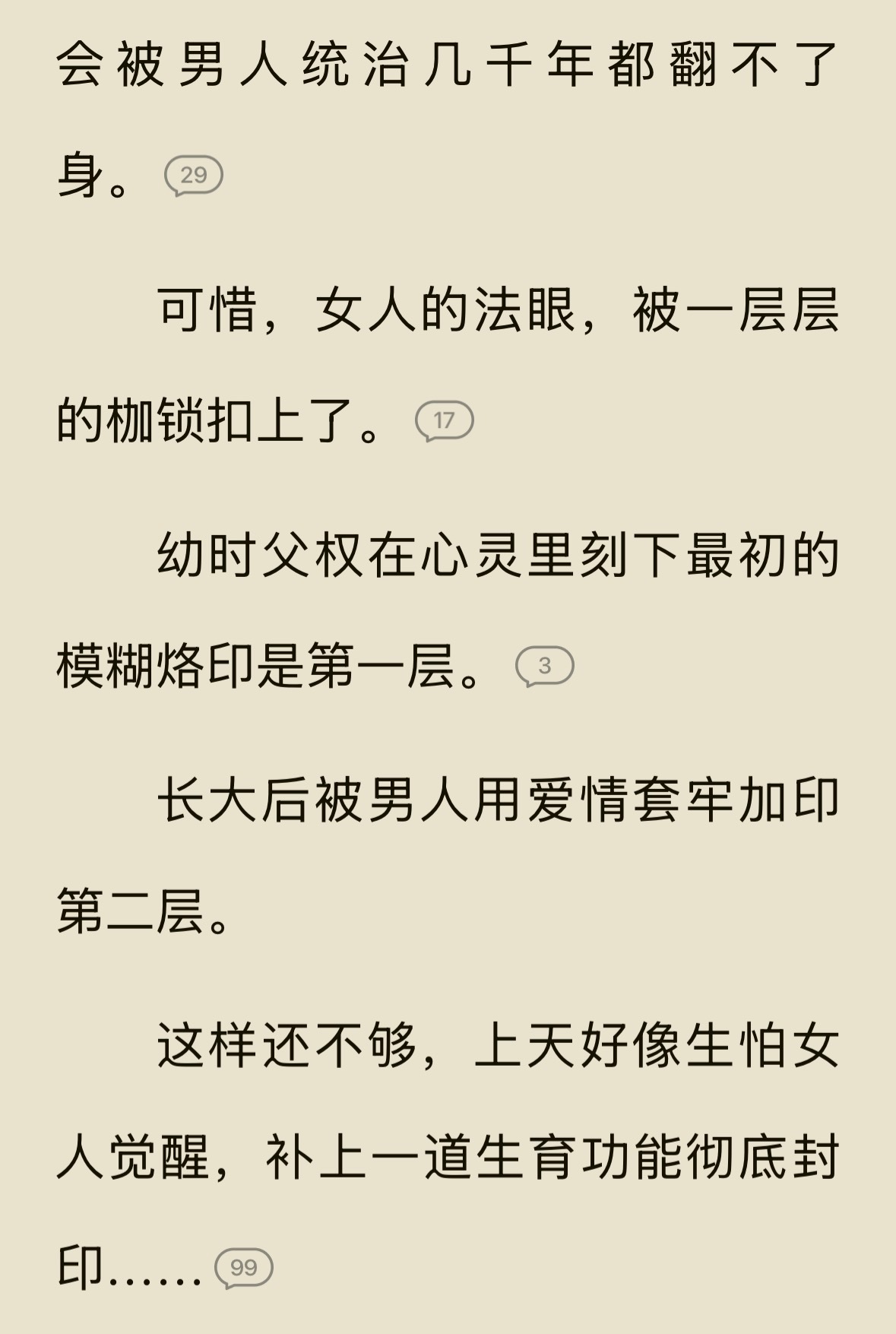1973年,宁夏一对年轻的夫妻,天没亮就出门赶集,走在前方的丈夫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慌忙转身查看,发现妻子竟消失不见了,而一根长得犹如松塔一般的圆柱形器物,就此重见天日。 此刻,如果你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前,隔着玻璃凝视那块黑色的“松塔”,很难把它和五十多年前宁夏固原那个带着土腥味的清晨联系起来。 现在的它是国宝,是东汉文明的切片,但在1973年,它差点就被当成一块烧火的废料,或者压咸菜的烂石头。 把时针拨回1973年的秋天,宁夏固原的清晨,风硬得像刀子。 王建国和媳妇李秀英起得比鸡还早,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背篓里的这点山货和蔬菜,是一家子在这个冬天能不能吃上油盐的指望。 王建国是个急性子,埋头赶路,脚步踩在碎石路上咔咔响。 这条路他们走过无数次,熟得闭着眼都能摸回家。 可概率论偏偏在这个早晨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身后突然传来“啊”的一声短促惨叫,紧接着是重物落地的闷响。 王建国猛一回头,身后空荡荡的,刚才还跟在后面的大活人,就像被这黄土高原一口吞了。 荒草在风里哗哗作响,王建国疯了一样往回跑,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应。 直到在一片被枯草遮掩的地面上,他发现了一个黑黢黢的窟窿。 这是西北常见的“地眼”,其实就是地下空洞塌陷形成的陷坑。 李秀英就在坑底,万幸坑不算太深,人除了崴了脚、吓掉了魂,没什么大碍。 就在王建国解裤腰带、找树藤准备救人的时候,坑底发生了一件极具戏剧性的事。 李秀英想撑着地站起来,手心却被什么东西狠狠硌了一下。 出于庄稼人“走过路过不空手”的本能,她没把那东西扔了,而是捡了起来。 借着洞口漏下来的微光,她看清了手里的物件。 这是个黑疙瘩,冰凉,梆硬,形状像个没张开的松塔,又像个手雷。最邪门的是,在这阴冷潮湿的土坑里,这东西竟然隐隐透着一股香气。 这股味道不是土腥气,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药香,混着松脂味。 李秀英也没多想,顺手把它揣进了棉袄兜里,这东西沉甸甸的,给家里的娃当个玩具倒是不错,要是实在没用,回家当引火煤烧了也行。 到了县城集市,这块后来震惊考古界的“松塔墨”,就那么随随便便地被扔在一堆萝卜白菜旁边。 一上午过去,山货卖得差不多了,唯独这个黑疙瘩无人问津。 路过的人扫一眼就走,没人愿意为一块“长得怪的黑石头”掏哪怕一分钱。 就在两口子准备收摊回家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卡上了。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路过,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又像是被什么磁场吸住了一样,倒退了回来。 他蹲下身,捡起那个黑疙瘩,手指在上面那一圈圈精细的螺纹上摩挲。 那一刻,专家的直觉战胜了理智。 “大哥,这东西你们可别乱卖。”年轻人说话的时候,声音都不太稳。 当天下午,在县文化站的办公室里,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 当刷子扫去那层浮土,露出乌黑油亮的本体时,鉴定专家的瞳孔瞬间放大。 他猛地站起身,第一反应竟然是去关门窗,生怕这消息长了翅膀飞出去。 经过反复比对,结论那是相当炸裂:这是一块东汉时期的“松塔墨”,距今已经一千八百多年。 这东西在当年就是妥妥的“黑科技”,你看它的造型,不做成方块,而是做成带螺纹的圆柱体,这叫“手捉墨”。 东汉的文人不需要带着沉重的砚台到处跑,只要握着这个墨块,利用螺纹防滑,直接在简单的石板上就能研磨,这是1800年前的人体工学设计。 更让专家背脊发凉的,是它对抗时间的“不朽之身”。 你得知道,普通的墨是用动物胶粘合的,皮胶也好,骨胶也罢,过个百八十年,胶质老化,墨块早就该干裂、酥碎成渣了。 但这块墨,在西北潮湿的地下墓室里躺了近两千年,出土时竟然黑亮如漆,连一道细微的裂纹都没有。 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东汉的工匠,掌握了一种我们至今都没完全参透的防腐配方。 可能是松烟与麝香的黄金配比,也可能像后来实验室推测的那样,混入了蜂蜡来隔绝水汽。 顺着王建国两口子的指引,考古队火速赶到了那个“吃人”的土坑。 一铲子下去,历史的真相彻底揭开:李秀英踩塌的哪是什么土坑,而是一座东汉贵族墓葬的盗洞。 虽然墓室早年被盗过,但清理出的金银玉器依然让人眼花缭乱。 可要论学术价值,谁都比不上李秀英兜里揣回来的那块墨。 它是孤品,是把《汉官仪》里关于“手捉墨”的文字记载变成实物的铁证。 当初为了表彰这两口子的贡献,政府颁发了一面锦旗,外加50元奖金。 别嫌少,在1973年,50元是一笔巨款,抵得上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足够这户农家过个肥得流油的新年。 但对于历史来说,这笔交易简直是血赚。 如今,当你再看着它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柔光里,别忘了,它曾属于泥土,属于那个寒冷的清晨,属于一对只想换点油盐钱的年轻夫妻。 信息来源: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