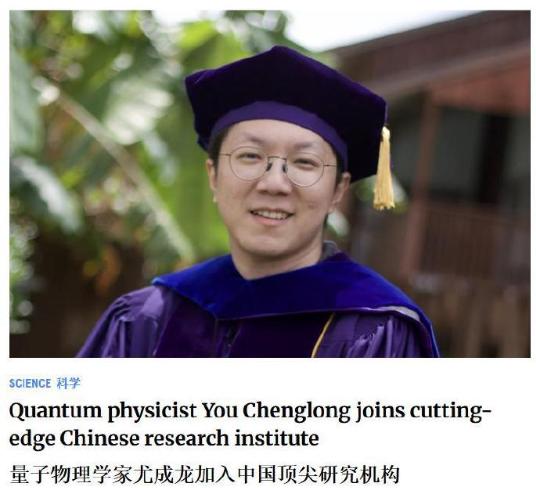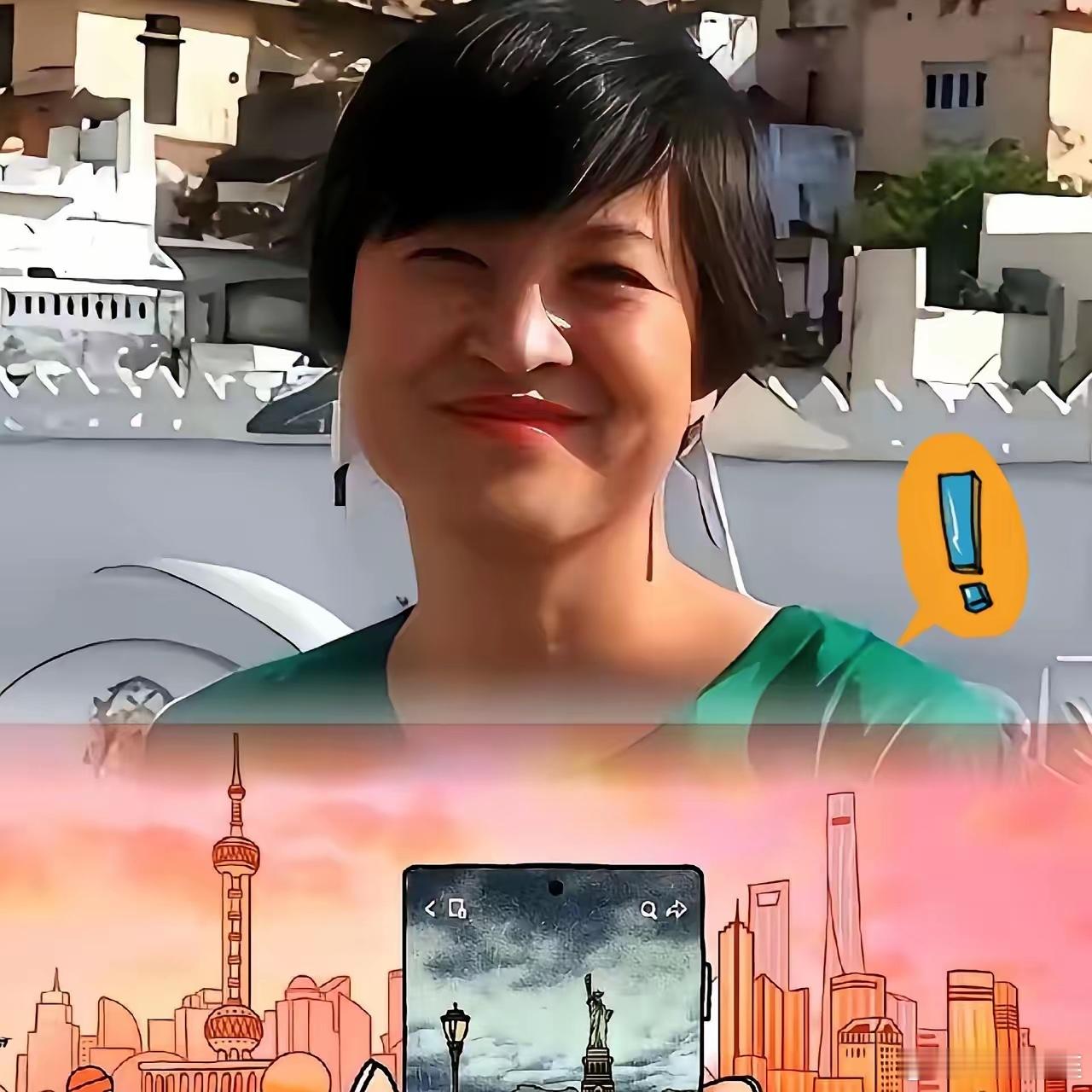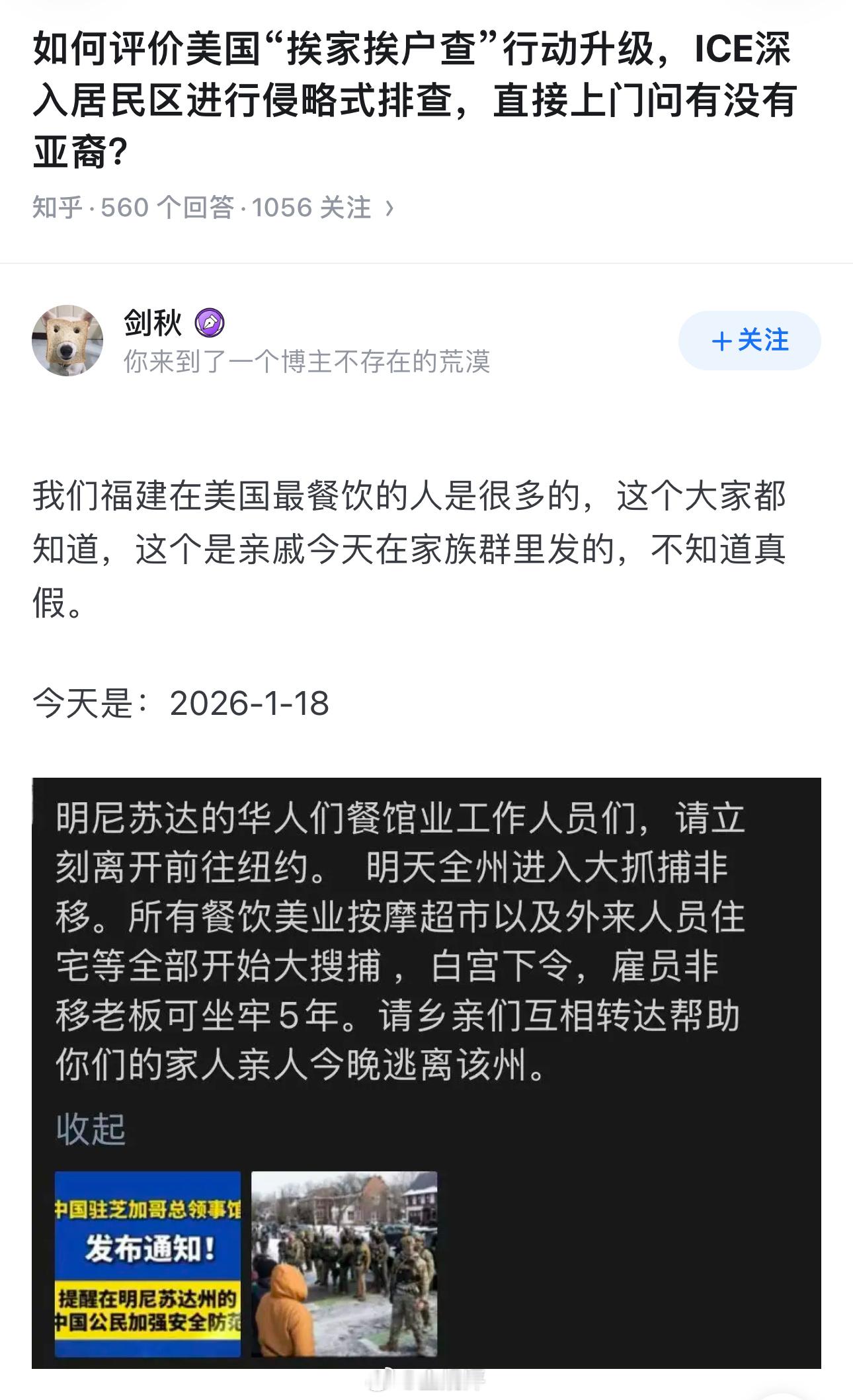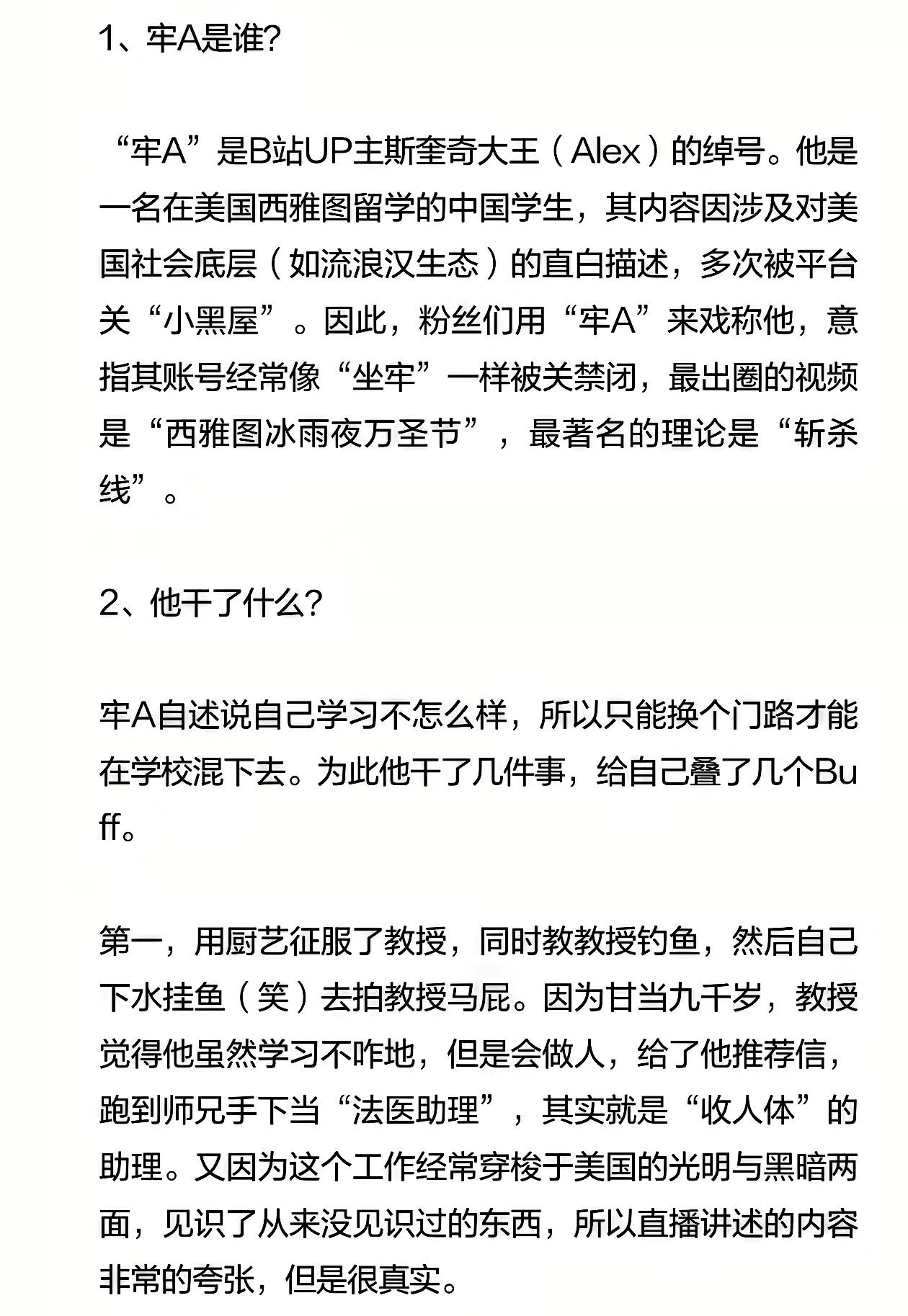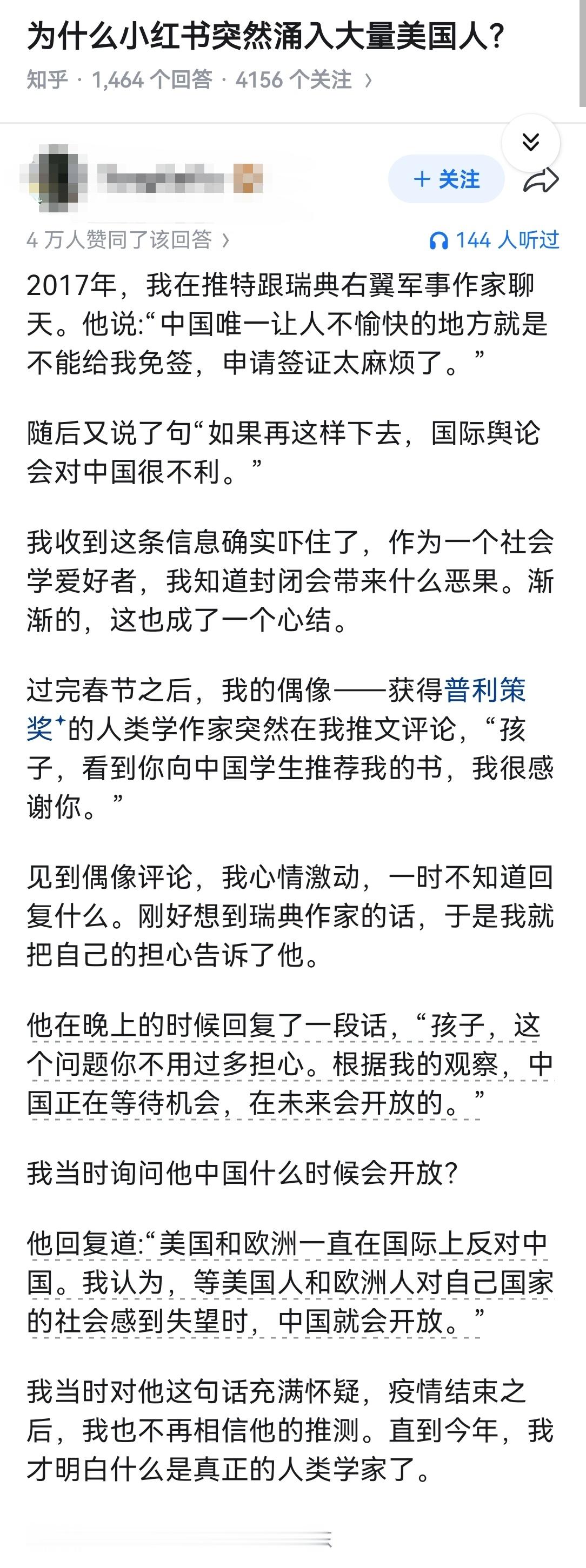“遮羞布被扯掉了!”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直言:中国的数学水平比美国落后了80多年,甚至和美国上世纪40年代差不多。让人意外的是,这位数学家自1980年回国后,竟然已经在中国待了四十年。 1980年代他第一次回国时,国内高校数学系连基本的微分几何教材都难找,如今他创办的七个研究院里,光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就聚集了百位科研人员——这不是退步,而是从“零基础追赶”到“结构性短板”的阶段性问题。 美国1940年代是什么概念?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刚迎来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正在奠定博弈论基础,数学与物理的交叉研究如火如荼。 而同期的中国,连华罗庚都还在西南联大的茅草屋里推导《堆垒素数论》。丘成桐算的是“积累账”: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系统引进欧洲数学家,到1940年代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生态,光哈佛数学系就有12位未来的菲尔兹奖得主在读。 中国真正大规模投入基础数学,是2000年以后的事,满打满算不过二十多年。就像他在清华求真书院强调的:“我们建大楼很快,但培养能提出原创问题的学者,需要三代人的沉淀。” 第二个痛点藏在人才结构里。2025年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的数据显示,获奖学者中三分之一来自国内,但细看研究方向,70%集中在应用数学领域,纯粹数学的突破依然罕见。 丘成桐创办的少年班项目里,12岁的孩子能大胆质疑教授,但到了高中,90%的学生因刷题失去提问勇气——这正是1940年代美国数学教育的反面。 当时的美国中学已普及数学讨论班,学生可以直接参与教授的课题,而中国至今有85%的重点中学把数学竞赛当升学工具。 他在自传里提到,自己当年敢拒绝陈省身指派的黎曼猜想,选择卡拉比猜想,这种学术自主权,正是当下国内博士生最稀缺的。 更关键的是学术生态的“代际断层”。丘成桐团队统计过,国内45岁以下的数学博导中,73%有海外留学经历,但真正在国际顶尖期刊担任编委的不足5%。 这就导致一个怪圈:引进的海外人才忙着发论文,本土培养的学生忙着“接轨国际”,没人敢碰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问题。 上海研究院的连文豪教授回忆,丘成桐要求学生每周读1940年代的经典论文,“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太习惯用计算机验证猜想,却忘了当年纳什用草稿纸就能证明嵌入定理的那种纯粹”。 这种从问题驱动到工具依赖的转变,恰恰是美国1940年代数学黄金时代的核心精神。 当然,追赶的速度也在改写账本。2024年清华数学中心的论文统计显示,本土培养的博士在《数学年刊》发文量同比增长40%,丘成桐少年班的学生已开始在国际奥赛中崭露头角。 但他看得更透:“1940年代的美国数学,不是靠论文数量堆出来的,而是出了一批定义学科方向的学者。”就像他坚持在研究院设置文史哲必修课,要求学生读《庄子》写旧体诗——因为当年的冯·诺依曼正是从《浮士德》中获得博弈论灵感。 这种人文土壤的培育,比建实验室更难,也更需要时间。 最值得注意的是丘成桐的行动逻辑。他一边说落后80年,一边把哈佛的退休时间定在2022年,全职回国组建团队;一边批评刷题教育,一边在39所中学开设少年班,专门保护12岁孩子的好奇心。 这就像他证明卡拉比猜想的过程:先承认问题的困难,再一步步搭建解决框架。2025年上海研究院的“无界学术周”,让代数几何与人工智能团队每天碰撞,这种跨学科生态,正是1940年代普林斯顿的翻版。 说到底,丘成桐的“刺耳”背后,是对中国数学从“跟随”到“引领”的急切。他算的不是简单的时间差,而是创新生态的成熟度。 当国内学生能像1940年代的美国同行那样,不为评奖只为好奇去研究一个数学问题,当导师能像陈省身允许他转向卡拉比猜想那样,包容学生的“离经叛道”,中国数学自然会跨过那80年的鸿沟。 这不是悲观的断言,而是一位学者的清醒认知:只有直面差距,才能踩准追赶的节奏。